愛因斯坦自由的人類良心起源于對道德宗教的信仰,在宇宙宗教上帝的信仰中實現人類良心的高度,這也是對個人自由的追求從而達到良心自由的境界。愛因斯坦自由的人類良心具有促進人類社會和諧發展、合乎邏輯地導向社會主義、促進國家法律改革和完善、實現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有機統一等積極意義。愛因斯坦自由的人類良心也存在著在殘暴專制的國家權力面前不堪一擊、離開優裕的物質生活條件滋養難以形成和存在,以及具有任性或隨意性因素等局限性。
[關鍵詞]:愛因斯坦,自由的人類良心,積極意義,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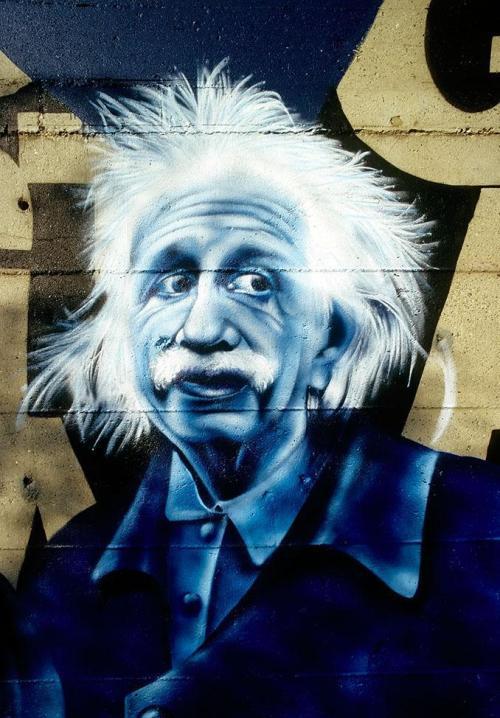
一、 良心及學術界對愛因斯坦良心的研究
無論是在中國文化上還是在西方文化中,“良心”都是人們渴望保有的一種美德,也是人們推崇的一個道德概念,它對于人和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中國文化中,“良心”概念的含義是“善良的心”,它源于《孟子·告子上》“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中的“良心”一詞[1](1417) ,意指人的天性中所包含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2](259)。在西方文化中,“良心”的含義是“一個人對道德真理的意識”[3] ,它是從拉丁文“conscientia”一詞而來的,意指人與人之間“默契的知識”。這里的人與人之間“默契的知識”,除了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般知識外,它“更是一種基于道德知識的,針對具體事情和境遇的實踐性判斷和行為”[4] 。因此,總的說來,所謂良心,我們可以將其定義為人所具有的、能夠調節和維護人與人之間合理關系的、促進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最核心的道德觀念。人的良心作為人的內在素質,它是通過人的言論和行為表現出來的,因而人的良心是蘊含在人的言論和行為中的道德觀念,通過對人的言論和行為的考察,就可以揭示出這個人究竟有沒有或具有什么樣的良心。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良心”被看成是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內容而受到排斥,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良心’一詞曾變成階級斗爭的活靶子”[5]。如果有人講“良心”或者說自己“憑良心干活”,會被認為是沒有覺悟或覺悟較低的表現,因而“良心”從道德本體的位置,降低為不值得人們信任的一種東西。如果有人因為受到誤會而用“良心”起誓,不僅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反而會遭到人們的鄙視,受到“你的良心值多少錢一斤?”的譏諷。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之下,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較高道德價值的“良心”,逐漸被“黨性”、“人格”或“對領袖的忠誠”所取代。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良心”作為人的“本份”的代名詞,重又回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有一位縣委書記在民主生活會上主動承認自己存在白吃、白喝、白吸(煙)、白拿等情況,并采取具體措施,切實解決了這些問題,就被中央領導同志稱為“一個有良心的縣委書記”[6]。按說,不貪、不占是國家公職人員的“本份”,守住或回歸了這個“本份”,就成了這個人“有良心”的體現。同樣,商人的“本份”在于誠信經營,誠信經營就成了商人的“良心”[7];記者的“本份”是不受任何干擾地如實報道新聞,不搞歪門邪道和實話實說就成了“記者的良心”[8],如此等等。于是,“良心”成了人們一顆守住自己“本份”的平常之心。
人們之所以把這種能夠守住做人的“本份”,保持一顆平常之心的道德觀念和行為稱為“良心”,是因為在經歷了極“左”思潮嚴重摧殘的當代中國社會中,它已經成為一種稀缺的社會資源。關于這一點,只要看看目前中國城市居民住宅防護的嚴密程度,以及媒體不斷曝出中國游客在國外旅游期間高聲喧嘩、隨地吐痰、亂扔垃圾的新聞報道,“說假話”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以致黨政官員很難聽到下屬的真話[9],而更多的人對此見怪不怪,就可以知道當今國人的良心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況了。
但是,這種作為做人“本份”的平常之心,與孟子所要求的那種在他人遇到危難時伸出援手所表現的“惻隱之心”,對自己或別人所做的壞事和惡習感到羞恥厭惡的“羞惡之心”,對高尚的人和事心存敬仰的“恭敬之心”,以及在為人處事中應當具有公平和正義感的“是非之心”,還是有相當明顯的差距的,只能說是一種最低檔次的良心。
盡管學術界對“良心”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是,在對愛因斯坦道德和倫理思想的研究中,似乎還沒有人對愛因斯坦的良心進行過較為系統的研究。在筆者所能見到的文獻中,即筆者以“良心”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的“期刊”欄目中,只搜索到李醒民的“論科學家的科學良心:愛因斯坦的啟示”一篇文章[10]。在李醒民的文章中,作為愛因斯坦“科學良心”具體內容的“科學探索的動機:力圖勾畫世界圖像,渴望看到先定和諧”、“科學追求的目的:發現真理,為科學而科學”、“維護科學自主:自覺抗爭,保持相對獨立”、“捍衛學術自由:爭取外在自由,永葆內心自由”、“科學活動的行為:道德高于才智,美德不可忽缺”、“對研究后果的意識:制止科學異化,杜絕技術濫用”和“對科學榮譽的態度:實事求是,寬厚謙遜”,不過是愛因斯坦科學良心的一些具體表現,而不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對愛因斯坦良心概念的系統論述。因而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愛因斯坦良心概念的研究,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
愛因斯坦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思想家,懷著推進社會發展和人類幸福的真摯感情,以他的強大理性和敏銳直覺,在對宇宙、社會和人生的思考中,形成了他自己一系列獨到的認識和理解,其中包括他極為深刻的道德和倫理觀念[11][12],而“良心”則是愛因斯坦道德和倫理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盡管愛因斯坦沒有系統地論述“良心”概念,他關于“良心”的言論也不是很多,但是在筆者看來,在愛因斯坦的“人類良心”和“良心的自由”等概念中,[13](14,279) 包含著極為深刻的道德和倫理內容,通過對愛因斯坦良心的研究,可以加深我們對良心概念的認識和理解。
二、 愛因斯坦自由的人類良心形成和發展過程
愛因斯坦認為,一個人從來到這個世界起,就自然地繼承了兩個方面的道德和倫理因素的遺傳。一方面是通過生物性的遺傳,繼承了群居動物中的個體對群體依賴的特性。這種特性在人類社會中,就像螞蟻和蜜蜂那樣,表現為個人對社會的依賴。他指出,這種不會變化的“人的生物學本性”,在原始部落的社會群體生活中,表現為“有節制的、合作的生活方式”[13](315,300)。雖然愛因斯坦的這種觀點,在當時只是一種想像力的自由聯想,但是,最新的科學研究已經發現,動物也有類似于人類的“道德觀”[14]。另據新華社報道,瑞士蘇黎世大學的研究人員,在人腦中發現有個“公平中心”[15]。這個“公平中心”,顯然是通過生物學遺傳得到的。這就意味著,愛因斯坦關于在原始部落社會群體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所表現出來的有節制的、合作的生活方式的行為,是通過生物學的遺傳,從群居動物中繼承的一種道德和倫理因素的預言,已經被當代的科學研究所證實。
另一方面,人在獲得生物學意義上的道德和倫理遺傳的基礎上,又在社會生活中,得到一種文化上的遺傳,即得到一種文化上的素質,把外在世界展示給我們的不清楚的現象之間的關系,解釋為是必然的、完全服從因果性規律的這種需要,愛因斯坦認為,這“無疑是在文化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理性經驗的產物”[16](345)。
比如,在原始人那里,他們根據同自己意志活動的類比,把他們在生存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對饑餓、野獸、疾病和死亡的恐懼,都歸因于某種看不見的精靈的意志的表現,從而想象出各種具有人性的鬼神,并且賦予它們各種超凡的本領,同時創造出一套代代相傳的傳統,通過一些動作和祭獻,以求得它們的恩寵,對人產生某種好感,愛因斯坦把這稱為“恐懼宗教”[16](403)。在愛因斯坦看來,恐懼宗教的意義在于,它根據人的力圖避開痛苦和死亡,而尋求安樂的原始本能,以那些使人具有巨大敬畏感的鬼神的名義,向人們提出一些適合當時人類生存需要的道德要求,以在當時的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建立起一種和諧共存的關系。
在人類社會和人的社會性的進一步發展中,人們在恐懼宗教的各種鬼神的基礎上,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一個能夠保護、支配、獎勵和懲罰人的“社會的或者道德的上帝概念”,愛因斯坦把在對這種上帝的敬畏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宗教,稱為“道德宗教”[16](404)。道德宗教是把各種恐懼宗教所提出的各不相同的道德要求,加工整理為統一的道德原則,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建立起只要“遵循這些原則”,就能得到“最大可能的安全和滿足”和“最小可能的痛苦”的信念[13](184)。當人們接受并信奉這些道德原則,就是把它們內化為自己的道德意識或道德觀念,構成各個人的良心。
愛因斯坦在晚年談到自己的思想歷程時說,早在少年時代,他就已經深切地意識到,大多數人終生無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無價值的。為了從這種毫無價值的人生追求中解脫出來,做一個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他通過學校的和社會的宗教教育,深深地信仰當時社會中流行的道德宗教。盡管他在12歲那年,由于讀了通俗的科學書籍,對《圣經》里的許多故事產生了懷疑,認為它們不可能是真實的,從而導致他突然中止了對神學宗教的信仰,失去了他的“少年時代的宗教天堂”,轉向從思想上掌握那個在個人以外的實在的外在世界,并且把這確立為他的人生的“最高目標”,但是,他把他對當時社會中流行的道德宗教信仰的經歷,看成是他“從‘僅僅作為個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第一個嘗試”,以及在對國家所制造的謊言的懷疑中,獲得了“一種真正狂熱的自由思想”[16](2),從而形成他最初的道德和倫理觀念,成為他的良心的基本內容。
如果僅從愛因斯坦在少年時代,通過對道德宗教的信仰而形成的道德和倫理觀念來看,由他在這一經歷中所體現的道德和倫理觀念,是一般信教群眾都會有的。比如,束星北的女兒束美新在談到她的母親時說,她的母親9歲在教會學校上學,從“嬤嬤們的奉獻精神”中,“學會了愛,學會了寬容大度”[17]。當這種以“奉獻精神”或“利他觀念”為核心的道德和倫理觀念,內化為通過“愛”和“寬容”等形式表現出來的個人素質,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社會良心”。凡是具有這種素質的人,都具有社會良心。
隨著愛因斯坦在追求知識和真理的道路上一步步地前進,以及他對宇宙本質和規律的理解的一步步加深,他深刻地認識到,盡管各種類型的道德宗教教義中的上帝觀念,是對人類精神進化的幼年時期所幻想出來的各種神的概念的升華,但是,正是它們上帝概念的擬人化特征,導致了科學與宗教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為了把科學與宗教協調起來,愛因斯坦用自己的科學精神和科學邏輯,通過對道德宗教的批判,使他的信仰達到人類宗教經驗的第三個階段,愛因斯坦把這種宗教稱為“宇宙宗教”,他說自己的哲學就是“宇宙的宗教”[16](569—570),他信仰的就是“那個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諧中顯示出來的上帝”[16](365)。愛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是用科學凈化了道德宗教的擬人化的上帝概念,從而提高了道德宗教的“境界”,使之成為“真正的宗教”[13](219)。這種真正的宗教一方面作為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最強有力、最高尚的動機,給予科學家們以強大的道德力量,使他們不顧無盡的挫折而堅定不移地忠誠于他們的志向;另一方面,被科學凈化并提高了境界的道德宗教,留下的是它屬于純粹人性的一面,愛因斯坦將其表述為:“個人的自由而有責任心的發展,使他得以在為全人類的服務中自由地、愉快地貢獻出他的力量。”[13](208) 至此,愛因斯坦在對宇宙宗教上帝的信仰中,達到了“人類良心”的高度,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世界公民”。[18](94)
在這里,愛因斯坦的人類良心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作為科學家,由宇宙宗教的因果必然性的上帝決定的愛因斯坦的“科學良心”[16](P531),要求他在廣義相對論創立以后,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對統一場論的研究之中。與此同時,愛因斯坦從他的科學良心出發,與量子力學的創立者們展開了一場意義深遠的論戰。愛因斯坦在經歷了初期從他的哲學觀點出發對量子力學理論真理性的攻擊失敗以后,雖然承認量子力學是一個成功的科學理論,但是對量子力學的創立者們把統計性作為“處理物理學基礎在本質上已是最后方式的這種信仰”,表達了他強烈的“反感”[16](652)。愛因斯坦在與量子力學創立者們的論戰,以及在對量子力學的評論中所說的他自己的“物理學本能”和“科學本能”[16](604,507),實質上是他的科學良心的不同表達形式。
〔參考文獻〕
[1] 廣東,廣西,湖南,河南辭源修訂組,商務印書館編輯部.辭源(合訂本)[Z].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 楊伯峻.孟子譯注(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 張秋梅.當代西方天主教自然法學派的良心觀[J].宗教學研究,2006,(1):202-205.
推薦閱讀:《宗教學研究》核心期刊論文發表
《宗教學研究》雜志是宗教學專業學術性雜志。內容以中國道教研究為主,兼及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中國民族民間宗教及其他宗教的研究。本刊主要讀者對象為哲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學、考古學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師生。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