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佛教文明的交流性是佛教思想文化的一個(gè)本質(zhì)性特征,是佛教文化成為全球性文化的一個(gè)重要的內(nèi)在基礎(chǔ)。但是對(duì)于佛教思想交流性本質(zhì)的發(fā)掘與論證,還需要系統(tǒng)地學(xué)術(shù)探索與建構(gòu)。以釋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的交流性問(wèn)題為核心議題,分別從以生命為本位問(wèn)題的佛陀哲學(xué)觀,以慈悲、無(wú)常、無(wú)我為主軸的佛陀真理觀,以“四大教法”為思想原則的佛陀詮釋觀,以“國(guó)土相應(yīng)法” 為特色的佛陀弘法觀等四個(gè)方面,對(duì)于釋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中交流互動(dòng)的特質(zhì),給予系統(tǒng)深入地整理和論證。對(duì)于原始佛教思想中交流性問(wèn)題的發(fā)掘,是基于“一帶一路”研究視域?qū)τ诜鸾趟枷氡举|(zhì)的一種闡釋?zhuān)矠榻窈笕妗⑸钊肜斫夥鸾涛拿鞯慕涣骰?dòng)問(wèn)題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ch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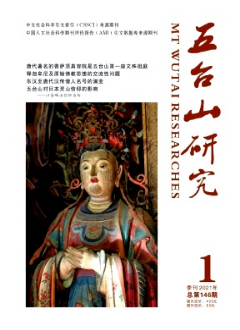
本文源自五臺(tái)山研究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3-17《五臺(tái)山研究》雜志,于1985年經(jīng)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zhǔn)正式創(chuàng)刊,CN:14-1080/B,本刊在國(guó)內(nèi)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shí)效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其中主要欄目有:文殊研究、五臺(tái)山學(xué)專(zhuān)論、生態(tài)環(huán)保等。
關(guān)鍵詞:釋迦牟尼;原始佛教;交流性;“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當(dāng)前我國(guó)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的研究領(lǐng)域,也為我們目前研究佛教史、佛教思想史提供了一種富有創(chuàng)新可能的學(xué)術(shù)空間。“一帶一路”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理解及解釋的范式,側(cè)重觀察和評(píng)述“一帶一路”地區(qū)及國(guó)家歷史及現(xiàn)實(shí)中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及宗教的互動(dòng)性、交流性,而“一帶一路”研究視域所觀照的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史,尤其能夠彰顯佛教文明交流互動(dòng)的特質(zhì)問(wèn)題。
法蘭克福學(xué)派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把人的社會(huì)行為區(qū)分為目的行為、規(guī)范調(diào)節(jié)行為、戲劇行為和交往行為四種形式,[2]83-84 這一交往行為理論為當(dāng)下“一帶一路”文明交流互鑒問(wèn)題的研究,提供了很合適的社會(huì)學(xué)理論基礎(chǔ)。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重視以理性為基礎(chǔ)的人類(lèi)交往活動(dòng)(即交流活動(dòng)),我們從這一理論受到啟發(fā),借鑒哈貝馬斯的理論,把交流性理解為佛教文明最本質(zhì)的內(nèi)在特質(zhì)之一。這里所謂的“交流性”,是指佛教在其思想教義、宣傳傳播、價(jià)值理念、制度建構(gòu)、思維方式中特別具有的排斥獨(dú)斷性,摒棄偏頗性,以尊重包容、平等多元、交流互動(dòng)等價(jià)值作為重要價(jià)值的佛教思想信仰的品質(zhì)。佛教文明的交流性是佛教思想文化的一個(gè)本質(zhì)性的特征,是佛教文化成為全球性文化的一個(gè)重要的內(nèi)在基礎(chǔ)。
迄今為止,學(xué)界較多關(guān)注宗教文化及佛教文化交流史實(shí)方面的探討,[3]1 而對(duì)佛教思想交流性本質(zhì)問(wèn)題的研究,則基本上尚稱(chēng)闕如。已故原中國(guó)佛教協(xié)會(huì)會(huì)長(zhǎng)趙樸初先生曾提出佛教先輩“弘揚(yáng)佛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的議題,認(rèn)為“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弘法”,“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弘法”及“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弘法”,是“佛教創(chuàng)立 2500 多年來(lái)”的三大“優(yōu)良傳統(tǒng)”[4]1401-1404,這一分析高屋建瓴,首次從全局性的層次和文化傳統(tǒng)的高度凸顯了交流互動(dòng)精神特質(zhì)之于佛教文明的本質(zhì)意義。而如何從學(xué)理上深入開(kāi)展對(duì)于佛教文明交流性本質(zhì)問(wèn)題的理解,則是我們今后需要認(rèn)真繼續(xù)發(fā)掘的課題。本文主要對(duì)釋迦牟尼及原始佛教思想重視交流性的品質(zhì)這一方面展開(kāi)相關(guān)的討論。對(duì)于原始佛教思想交流性本質(zhì)的發(fā)掘是基于“一帶一路”研究視域?qū)τ诜鸾趟枷氡举|(zhì)的一種闡釋?zhuān)矠榻窈罄^續(xù)深入探討佛教文明的交流互動(dòng)本質(zhì)奠定了初步的理論基礎(chǔ)。
一、以生命本身問(wèn)題為本位的佛陀哲學(xué)觀
釋迦牟尼思想中最令人醒目的一點(diǎn),是他以生命本身及其解脫問(wèn)題為本位,拒絕討論種種形而上學(xué)觀點(diǎn)的特別的哲學(xué)態(tài)度。對(duì)于佛陀這一哲學(xué)態(tài)度最形象的揭示,可以舉出《中阿含經(jīng)》中《箭喻經(jīng)》的記錄。[5]804a21 佛陀提出這樣的譬喻來(lái)啟發(fā)學(xué)生:好比一個(gè)身中毒箭,遭受極重痛苦的世人,親族們憐憫他,為他找來(lái)了醫(yī)生,此時(shí)此刻這位病人是先研究醫(yī)生的身份背景、身上所中毒箭的顏色、形狀、制作的地區(qū)、制作人的種種情況,以致在這個(gè)無(wú)窮無(wú)盡、漫長(zhǎng)的探求過(guò)程中生命趨于消失呢,還是先要請(qǐng)醫(yī)生斬釘截鐵地拔出毒箭,以保全其性命呢?答案顯然不言而喻:一個(gè)身中毒箭、生命垂危者,首要的事情,當(dāng)然是先要拔出毒箭,保全生命。同樣的道理,一個(gè)佛陀的學(xué)生,追隨佛陀學(xué)習(xí)佛法,他是應(yīng)該先探尋世界有邊、無(wú)邊一類(lèi)的問(wèn)題,在這個(gè)漫長(zhǎng)的求索過(guò)程中讓生命白白消失呢,還是應(yīng)該直接關(guān)注他自己生命本身的問(wèn)題?在佛陀看來(lái)這個(gè)問(wèn)題的答案同樣不言而喻。
漢譯《雜阿含經(jīng)》卷 34 的論題,與《箭喻經(jīng)》的相關(guān)論題,也是一致的。這篇經(jīng)中說(shuō),有一天,佛陀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有個(gè) Vaccha 種姓的漫游者(漢譯:“婆蹉種出家”)來(lái)到佛陀住處,與佛陀發(fā)生了一場(chǎng)對(duì)話。這位漫游者先詢問(wèn)佛陀是否秉持“世間常”的真理,遭到佛陀明確的否定回答。接下去漫游者一一詢問(wèn):佛陀是否秉持世間無(wú)常、世間既恒常又無(wú)常、世間非常非無(wú)常、世間有邊、世間無(wú)邊、世間既有邊又無(wú)邊、世間非有邊非無(wú)邊、生命與身體同一、生命與身體不同一、如來(lái)死后存在、如來(lái)死后不存在、如來(lái)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如來(lái)死后非存在非不存在的真理,佛陀同樣也一一作出明確的否定性的回答。
這篇經(jīng)文中漫游者提出的“世間常”等十四個(gè)論題,與《箭喻經(jīng)》中所提出的論題一致,就是后來(lái)佛教的教義學(xué)所概括的“十四無(wú)記”——十四個(gè)佛陀不予以回答的問(wèn)題。而佛陀樂(lè)于回答的問(wèn)題,則是關(guān)于生命窘迫的現(xiàn)狀(苦圣諦)、導(dǎo)致窘迫現(xiàn)狀的原因(苦集圣諦)、生命的自由自在境界(苦滅圣諦)、導(dǎo)致生命終極境界的方法(苦滅道跡圣諦)這樣的四組問(wèn)題。佛陀不予回答的十四個(gè)問(wèn)題,是釋迦牟尼時(shí)代及原始佛教對(duì)于印度哲學(xué)界帶有形而上學(xué)意味的典型哲學(xué)問(wèn)題的集中概括;而后四組問(wèn)題,則是佛陀所側(cè)重并啟示的新型的哲學(xué)問(wèn)題:人人應(yīng)當(dāng)關(guān)注的自己生命本身及其可能性的問(wèn)題。
經(jīng)文中提出:佛陀為什么對(duì)于那些有哲學(xué)意味的問(wèn)題,不像一般哲學(xué)家那樣看、那樣說(shuō)呢?這是因?yàn)榉鹜诱J(rèn)為通常這些形而上學(xué)的觀念,及其探索的過(guò)程,并不能改變生命不自由、不自在的現(xiàn)狀,而且經(jīng)常還是導(dǎo)致生命不自由、不自在狀態(tài)的原因之一。佛陀引導(dǎo)弟子們,或?qū)ζ浣谭ㄓ信d趣的人們,直接關(guān)注生命本身,關(guān)注生命的解脫。這種問(wèn)題關(guān)懷及其思考方式,使得他所倡導(dǎo)的佛法自一開(kāi)始就規(guī)避陷入種種形而上學(xué)的窠臼中,也使得佛教在后來(lái)的發(fā)展中始終堅(jiān)持避免成為一種抽象思辨的哲學(xué),或純粹知識(shí)的哲學(xué)。
對(duì)于佛陀這種思想氣質(zhì),一種流行的解讀是,認(rèn)為佛陀對(duì)于哲學(xué)懷有某種厭棄,這樣的解讀其實(shí)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的學(xué)界。如 20 世紀(jì)初中國(guó)現(xiàn)代著名佛學(xué)家歐陽(yáng)竟無(wú)(1871-1943),即曾提出“佛法非哲學(xué)”的著名觀點(diǎn),力陳哲學(xué)之種種過(guò)謬及佛法之種種殊勝,將“佛法”與 “哲學(xué)”幾乎完全對(duì)立起來(lái)。[7]493 其實(shí)這種解讀是不準(zhǔn)確的。佛陀的覺(jué)悟并不是反對(duì)哲學(xué),他所反對(duì)的其實(shí)是脫離生命本身,不以生命問(wèn)題為第一位問(wèn)題的哲學(xué)。佛陀啟發(fā)了一種關(guān)注生命本身的哲學(xué)模式,這種哲學(xué)模式教導(dǎo)人們突破任何獨(dú)斷論、知識(shí)論體系的迷霧及其糾結(jié),建設(shè)智慧的人生,覺(jué)悟的人生。重視生命問(wèn)題本身的哲學(xué)可以避免任何獨(dú)斷論哲學(xué)、知識(shí)論哲學(xué)的封閉性、強(qiáng)制性、非義性,讓哲學(xué)省思始終從生命出發(fā),圍繞生命,并為了生命。釋迦牟尼以生命問(wèn)題為軸心的哲學(xué)方向本身就寓涵佛法智慧活動(dòng)的生命性和交流性。
二、以慈悲、無(wú)常、無(wú)我為主軸的佛陀真理觀
任何哲學(xué)和宗教,無(wú)非從事真理之探究,所以一定的真理觀是一定的哲學(xué)或宗教的理論基礎(chǔ)。作為一個(gè)覺(jué)者的佛陀,他本人究竟持有怎樣的真理觀,他闡述了怎樣的真理理念呢?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通過(guò)《雜阿含經(jīng)》的如下表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婆羅門(mén)出家白佛言:“瞿曇!我等眾多婆羅門(mén)出家集于此坐,作如是論:‘如是婆羅門(mén)真諦,如是婆羅門(mén)真諦。”佛告婆羅門(mén)出家:“有三種婆羅門(mén)真實(shí),我自覺(jué)悟成等正覺(jué),而復(fù)為人演說(shuō)。汝婆羅門(mén)出家作如是說(shuō):‘不害一切眾生,是婆羅門(mén)真諦,非為虛妄。’彼于彼言我勝、言相似、言我卑,若于彼真諦不系著,于一切世間作慈心色像,是名第一婆羅門(mén)真諦,我自覺(jué)悟成等正覺(jué),為人演說(shuō)。復(fù)次,婆羅門(mén)作如是說(shuō):‘所有集法皆是滅法,此是真諦,非為虛妄。’乃至于彼真諦不計(jì)著,于一切世間觀察生滅,是名第二婆羅門(mén)真諦。復(fù)次,婆羅門(mén)作如是說(shuō):‘無(wú)我處所及事都無(wú)所有,無(wú)我處所及事都無(wú)所有,此則真諦,非為虛妄。’如前說(shuō),乃至于彼無(wú)所系著,一切世間無(wú)我像類(lèi),是名第三婆羅門(mén)真諦,我自覺(jué)悟成等正覺(jué)而為人說(shuō)。”
這篇經(jīng)文所記錄的,是佛陀與一些婆羅門(mén)宗教師(漢譯:“婆羅門(mén)出家”)對(duì)談?wù)胬碛^問(wèn)題。可以看出,佛陀這里向這些婆羅門(mén)宗教師宣講的真理(真諦),一共有三種:其一是“不害一切眾生”,其二是“所有集法皆是滅法”,其三是“無(wú)我處所及事都無(wú)所有”。第一個(gè)真理的核心要素是慈悲心,第二個(gè)真理的核心要素是無(wú)常觀,第三個(gè)真理的核心要素是無(wú)我的理念。
參考南傳佛教增支部經(jīng)典,這部漢譯經(jīng)典對(duì)應(yīng)的經(jīng)典在此處說(shuō)到四種真理:一是“不殺害一切生命”,二是“一切諸欲無(wú)常”,三是“一切諸有無(wú)常”,四是“無(wú)我無(wú)我所”。[8]553漢傳(北傳)與南傳兩種經(jīng)典傳承相比,漢譯此處所傳的第二條真理,可以看作是南傳此處第二、第三兩條真理的融合。所以南北傳佛教這里傳述的原始佛教的佛陀真理觀是一致的,慈悲的理念、無(wú)常的理念及無(wú)我的理念構(gòu)成佛陀所講述的基本真理。可以看出,此處經(jīng)文佛陀所宣講的三條真理,與后來(lái)原始佛教及部派佛教所總結(jié)的“三法印”說(shuō),無(wú)論是與南傳佛教的三法印(諸法無(wú)我、諸性無(wú)常、一切行苦)相比,或是與北傳佛教的三法印(諸行無(wú)常、諸法無(wú)我、涅槃寂靜)相比,[9]49-74 都可以看出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有一定的不同,顯示從佛陀所講述的真理到后來(lái)僧團(tuán)的教義學(xué)定型的過(guò)程中,存在某種演進(jìn)的痕跡和微妙的差異。
我們看到:慈悲的真理成為佛陀這里所宣講三條真理中的第一條真理,顯示佛陀對(duì)慈悲的真理理念的高度重視。慈悲心是對(duì)待人類(lèi)同胞及動(dòng)物親近、愛(ài)護(hù)的情懷,這是佛陀的根本思想之一,是佛教思想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也可以說(shuō)是佛教真理的基石。慈悲這一真理所傳達(dá)的人類(lèi)倫理及動(dòng)物倫理的思想,充滿了平等的精神,關(guān)愛(ài)的情懷,推己及人的態(tài)度,決定了佛教文明在人類(lèi)倫理及動(dòng)物倫理層面所彰顯尊重一切生命、推動(dòng)生命的交流互動(dòng)的基本價(jià)值。后世大乘佛教正是基于這一認(rèn)識(shí),將慈悲心的價(jià)值進(jìn)一步予以提升,“謂菩提心依於大悲為根本”[10]456a19,也就是將慈悲心視為菩提心的核心要素。
佛陀這里所講的第二條真理,無(wú)常的真理,說(shuō)明無(wú)論是我們對(duì)于外部世界的主觀性的欲望,還是在欲望的推動(dòng)下所形成的我們的現(xiàn)實(shí)生活,都是變動(dòng)不居的。這一真理的實(shí)質(zhì)是啟示人們破除對(duì)于世界及人生種種幻象的迷戀,關(guān)注生命本身的真實(shí)現(xiàn)狀及其改變的可能性、主動(dòng)性。所以這一條真理與佛陀以生命本身為佛法智慧本位的哲學(xué)觀是一致的,其實(shí)質(zhì)并非如很多人所錯(cuò)誤以為的“悲觀主義”。
而佛陀所宣講的第三條真理,無(wú)我的真理,強(qiáng)調(diào)我們所習(xí)以為常見(jiàn)到的自我,其實(shí)是并不存在的,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于自我中心的排除。無(wú)我的真理觀使得佛教自始至終都有一種排斥個(gè)人中心主義的自然趨勢(shì),而對(duì)于個(gè)人中心主義的排除可以培養(yǎng)一種包容的氣質(zhì),這正是突破個(gè)人中心主義及人類(lèi)中心主義,使得基于平等、多元及尊重、交流的普世倫理能夠確立的哲學(xué)基礎(chǔ),也正是佛教之交流性所以可能的一種內(nèi)在條件。
三、以“四大教法”為原則的嚴(yán)謹(jǐn)而開(kāi)放的佛陀詮釋觀
任何哲學(xué)或宗教都有其經(jīng)典,都有其思想、教義,因而也都有其經(jīng)典、教義的詮釋原則。在組成教團(tuán)成為一種宗教團(tuán)體之后,同人類(lèi)歷史上的任何其他宗教團(tuán)體一樣,佛教的教團(tuán)也必然有其經(jīng)典和教義,也必然有其詮釋的原則。具有獨(dú)斷氣質(zhì)的宗教傾向從經(jīng)典、教義詮釋的層面封閉交流開(kāi)放的可能,而具有開(kāi)放氣質(zhì)的宗教則往往保持詮釋層面不斷開(kāi)放、意義層面不斷更新的空間和可能。從經(jīng)典教義詮釋的角度觀察,佛教可以說(shuō)是人類(lèi)宗教中最具開(kāi)放詮釋空間的宗教體系之一,而佛教思想文化這種特質(zhì)的形成同樣導(dǎo)源于它的創(chuàng)立人釋迦牟尼。
在漢譯《長(zhǎng)阿含經(jīng)》中,收錄有一部《遊行經(jīng)》,與巴利三藏長(zhǎng)部經(jīng)中所收《大涅槃經(jīng)》(Mahqparinibbqnasuttam), 乃是同源經(jīng)。這部經(jīng)典記錄佛陀晚年最后一次出行、試圖返回故鄉(xiāng),在中途患病并涅槃的事跡,是原始佛教文獻(xiàn)中實(shí)錄性質(zhì)非常強(qiáng)的一部經(jīng)典,被很多學(xué)者接受為反映佛陀晚年最后一段時(shí)間生活的信史。在這部經(jīng)典提出“四大教法”的理念,因?yàn)楹苡锌赡艹鲎苑鹜佑H自的訓(xùn)誡,所以在研究佛陀個(gè)人的佛法思想時(shí)具有高度的信實(shí)性。所謂“四大教法”,巴利文是:Catumahqpadesa,其中的 qpadesa,既是“教法”的意思,也是“理由”、“根據(jù)”的意思,所以“四大教法”的理念,既是指佛陀晚年垂示的四個(gè)教法,也是晚年佛陀所指示未來(lái)佛教經(jīng)典教義詮釋的四條基本的詮釋原則。“四大教法”的理念,可以代表佛陀的教法詮釋思想。
其中,關(guān)于第一大教法原則,經(jīng)中這樣記錄:
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諸賢!我于彼村、彼城、彼國(guó),躬從佛聞,躬受是教。”從其聞?wù)撸粦?yīng)不信,亦不應(yīng)毀,當(dāng)于諸經(jīng)推其虛實(shí),依律、依法究其本末。若其所言非經(jīng)、非律、非法,當(dāng)語(yǔ)彼言:“佛不說(shuō)此,汝謬受耶!所以然者?我依諸經(jīng)、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違。賢士!汝莫受持,莫為人說(shuō),當(dāng)捐舍之。”若其所言依經(jīng)、依律、依法者,當(dāng)語(yǔ)彼言:“汝所言是真佛所說(shuō),所以然者?我依諸經(jīng)、依律、依法,汝先所言,與法相應(yīng)。賢士!汝當(dāng)受持,廣為人說(shuō),慎勿捐舍。” 此為第一大教法也。
可見(jiàn)“第一大教法”的意義是:不以是否“躬從佛聞”作為判斷所說(shuō)正確與否的標(biāo)準(zhǔn),而是要依據(jù)既有的經(jīng)、律、論加以鑒別,凡是符合經(jīng)、律、論的,則應(yīng)接受為“佛所說(shuō)”;凡是不符合經(jīng)、律、論的,則應(yīng)加以舍棄。
同樣的道理,不能以是否從“耆舊”所聞、從“眾多比丘”所聞、從“一比丘”所聞,作為正確與否的標(biāo)準(zhǔn),而是要訴諸經(jīng)、律、論的檢驗(yàn),以為接受或舍棄的判定。這些規(guī)定分別是第二、第三、第四三大教法的意義。
可以看出四大教法理念的核心,是不能以一個(gè)人在僧團(tuán)中的地位來(lái)決定他所傳誦佛學(xué)思想的價(jià)值,而是要以是否符合經(jīng)、律、論來(lái)作為嚴(yán)格檢驗(yàn)的標(biāo)準(zhǔn)。即使是佛陀本人,如果所說(shuō)不符合佛法的真理,那么傳自他的說(shuō)法也不可以被認(rèn)為是“佛所說(shuō)”的佛法,何況出自其他人的傳說(shuō)。這樣的教法原則就是后來(lái)僧團(tuán)進(jìn)一步概括的“依法不依人”的教法詮釋原則。這一教法詮釋原則確保了佛教經(jīng)典、義理詮釋的客觀性、嚴(yán)謹(jǐn)性,避免了隨意性和散漫性,使得佛教的思想教義具有其權(quán)威性與一致性。但是通常人們的理解和解釋?zhuān)鲆暳诉@一教法詮釋原則的另外一層意義:任何一個(gè)人,不要看他的身份,如果他所覺(jué)、所傳、所言,符合基本的教法原則,那么經(jīng)過(guò)一定的檢驗(yàn)程序之后,他之所傳所言也就應(yīng)該被接受為“佛所說(shuō)”的佛法。所以“依法不依人”的教法詮釋原則,從本質(zhì)而言,包涵了嚴(yán)謹(jǐn)性與開(kāi)放性的兩個(gè)方面。正是這兩個(gè)方面的辯證統(tǒng)一,一方面確保佛教思想詮釋的嚴(yán)肅與純潔,一方面也使得佛教的思想的理解始終有開(kāi)放詮釋、創(chuàng)新詮釋的可能。
在原始佛教經(jīng)典《中阿含經(jīng)》中,有一部《大品阿梨咤經(jīng)》,是反映原始佛教佛法詮釋理念的一部重要經(jīng)典。這部經(jīng)針對(duì)一個(gè)名為阿梨吒的比丘對(duì)于佛陀說(shuō)法的錯(cuò)誤理解的問(wèn)題,提出:“若我所說(shuō)法盡具解義者,當(dāng)如是受持。若我所說(shuō)法不盡具解義者,便當(dāng)問(wèn)我及諸智梵行者。所以者何?或有癡人,顛倒受解義及文也,彼因自顛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謂正經(jīng)、歌詠、記說(shuō)、偈他、因緣、撰錄、本起、此說(shuō)、生處、廣解、未曾有法及說(shuō)義,彼諍知此義,不受解脫知此義,彼所為知此法,不得此義,但受極苦,唐自疲勞。所以者何?彼以顛倒受解法故。”[5]764a10-18 這里強(qiáng)調(diào)了完整、準(zhǔn)確地理解經(jīng)典意義的重要性,指出如果“顛倒”地理解三藏經(jīng)典,則不得佛法之義,白白消耗生命。那么要如何準(zhǔn)確地理解、把握佛法的真義呢?這部經(jīng)典中也提出著名的“筏喻”的理念:“我為汝等長(zhǎng)夜說(shuō)筏喻法,欲令棄舍,不欲令受。若汝等知我長(zhǎng)夜說(shuō)筏喻法者,當(dāng)以舍是法,況非法耶?”[5]764c12-14 經(jīng)中提出佛陀所說(shuō)的法,就如同 “筏”一樣,法的作用是幫助人們渡過(guò)生死洪流,而不是讓人們?nèi)グ淹婊驁?zhí)著,所以法是應(yīng)當(dāng)被舍棄的,更何況非法的東西呢。《中阿含經(jīng)》強(qiáng)調(diào)完整、準(zhǔn)確的理解的重要性,揭橥佛法如筏的教法性質(zhì),同樣既重視佛法詮釋的嚴(yán)謹(jǐn)性、嚴(yán)肅性,又反對(duì)將佛法教條化、獨(dú)斷化,這種詮釋思想與釋迦牟尼“四大教法”說(shuō)中體現(xiàn)的詮釋精神如出一轍。
正是由于釋迦牟尼教法詮釋智慧的積極影響,后世佛教進(jìn)而發(fā)展出所謂“佛法有五種人說(shuō)”[12]66b4-6 的理念,對(duì)于所謂 “佛說(shuō)”的傳承人資格問(wèn)題,給出進(jìn)一步的思考和厘定,確證并不是只有佛陀一個(gè)人的說(shuō)法,才有資格稱(chēng)為 “佛說(shuō)”,其他人如佛陀的弟子、仙人、諸天、化人,他們基于真理體悟的正確的說(shuō)法,也都有資格稱(chēng)為“佛說(shuō)”,對(duì)于佛法傳承人資格的這一審察標(biāo)準(zhǔn)可以視為釋迦牟尼及原始佛教詮釋智慧的合理延續(xù)。初期大乘佛教對(duì)于作為佛陀說(shuō)法立教的內(nèi)在原則、作為佛菩薩圣者重要的內(nèi)在品德之一、作為佛菩薩圣賢與一般眾生交流互動(dòng)內(nèi)在依據(jù)的“善巧方便”概念思想,進(jìn)行了深入細(xì)致的研究、發(fā)揮和總結(jié),[13] 也正是釋迦牟尼及原始佛教詮釋思想、原則的進(jìn)一步深化及提升。
四、以“國(guó)土相應(yīng)法”為特色的佛陀弘法觀
“國(guó)土相應(yīng)法”,是漢傳原始佛教經(jīng)典《毗尼母經(jīng)》(Vinayamātrkā)中所闡釋佛教的弘法策略思想。這一思想要求考慮到不同地方、不同國(guó)土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的實(shí)際情況及不同需要,采取靈活機(jī)動(dòng)的弘法策略,調(diào)整佛教的制度建構(gòu),適應(yīng)地方文化的實(shí)際需求,以便更好地弘揚(yáng)佛法,發(fā)揮佛教的教化功能。關(guān)于這個(gè)問(wèn)題,《毗尼母經(jīng)》卷 8 中有如下的記載:
國(guó)土相應(yīng)法者,阿盤(pán)提國(guó)通律師五人得受具足,阿犯干提熱得數(shù)數(shù)洗,亦聽(tīng)兩三重皮作革屣著。爾時(shí)諸比丘雪山中夏安居,身體剝壞,來(lái)到佛所。佛聞已,如此國(guó)土聽(tīng)著富羅復(fù)衣。有二比丘,一名烏嗟羅、二名三摩跎,來(lái)到佛所白言: “諸比丘有種種性、種種國(guó)土人出家,用不正音壞佛經(jīng)義,愿世尊聽(tīng)我用闡提之論正佛經(jīng)義。” 佛言:“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yǔ),雖質(zhì)樸不失其義,令人受解為要。’爾時(shí)世尊在毗舍離,世儉谷貴,乞食難得,諸比丘乘神通力至豈伽國(guó)乞食。彼國(guó)人惡賤道人,持食著地,不過(guò)手中。有諸比丘往白世尊。佛言:“雖非手受,施心已竟,可取食之。” 是名國(guó)土相應(yīng)法。
同一經(jīng)典卷 4,有與這一段經(jīng)文內(nèi)容意義相近而語(yǔ)言更為詳盡的表述。[14]821c18 綜合兩處的表述,可知“國(guó)土相應(yīng)法”包涵的基本內(nèi)容如下:允許在不同的地方說(shuō)戒,而不是僅僅在中心地區(qū)說(shuō)戒;允許在邊遠(yuǎn)的地方有五位律師就可以接受具足戒;允許在國(guó)土很熱的地方,僧人每天洗澡;允許在荊棘多的地方,僧人可以著皮革;在寒冷的國(guó)土中,允許僧人著複衣;考慮不同地區(qū)的不同語(yǔ)言,允許用不同的語(yǔ)言宣講佛法;可以接受一些并非親手施與或放置于地上的食物。這些原則,就叫做“國(guó)土相應(yīng)法”,或“隨國(guó)應(yīng)作”。所以根據(jù)不同地區(qū)、不同國(guó)家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huì)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來(lái)對(duì)佛法的制度、生活作出適當(dāng)?shù)恼{(diào)整,以更好地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需要,融攝地方文化,應(yīng)當(dāng)是佛陀以“國(guó)土相應(yīng)法” 為基本內(nèi)涵的弘法政策的基調(diào)。
漢傳佛教所譯《十誦律》中,也有一段文獻(xiàn)說(shuō)到:“國(guó)土凈法者,得神通諸比丘,至惡賤國(guó)土乞食,是比丘先從惡賤人受食噉,此人心悔:‘我等墮不凈數(shù)。’便不復(fù)乞。是人持食于比丘前棄地而去,諸比丘不知云何?佛言:‘從今日至惡穢國(guó)土,棄食著地得自取食,隨國(guó)土法故。如邊地持律,第五得受具足戒;阿葉波伽阿盤(pán)提國(guó)土,聽(tīng)著一重革屣、常洗浴、皮褥覆;如寒雪國(guó)土中,聽(tīng)畜俗人靴具。’是名國(guó)土凈法。”[15]414b27-c6 可以看出此律所說(shuō)“國(guó)土凈法” 的內(nèi)容,與《毗尼母經(jīng)》的“國(guó)土相應(yīng)法”或“隨國(guó)應(yīng)作”,是一致的。此外,《中阿含經(jīng)》中還有“隨國(guó)俗法,莫是莫非”[5]701c6 的誨示,其間的精神,應(yīng)該也是相通的。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原始佛教中的這一弘法思想及弘法政策,應(yīng)當(dāng)是直接起源于佛陀。這一弘法思想的主旨是增強(qiáng)佛教的適應(yīng)性,避免佛教與各種不同文化之間不必要的沖突,推動(dòng)佛教的發(fā)展和影響,而在這一弘法政策的背后,則是祛除“文化中心”的驕慢,平等尊重其他地方包括邊遠(yuǎn)地區(qū)文化價(jià)值的態(tài)度。我們?cè)谶@一弘法策略中不難再次體會(huì)佛陀教法理論及弘法實(shí)踐確實(shí)深深浸透著平等、交流、多元、去中心的精神。
這其中特別是佛陀弘法的語(yǔ)言政策問(wèn)題尤其值得提出。如果一種宗教在傳播的過(guò)程中,有其權(quán)威語(yǔ)言或者有具有權(quán)威性的比較固定的語(yǔ)言,那么這種宗教的交流性應(yīng)當(dāng)是有所減弱的;相反,如果一種宗教并不規(guī)定其權(quán)威語(yǔ)言,則這樣的宗教在其傳播過(guò)程中,在語(yǔ)言方面具有靈活性,當(dāng)然也就更加具有多元文化的交流性。我們?cè)卺屽饶材岬恼Z(yǔ)言政策中,可以看到他所推動(dòng)弘揚(yáng)的佛教,正是這樣一種并不建立權(quán)威語(yǔ)言的宗教。在上述《毗尼母經(jīng)》的兩處譯文中,我們都看到佛陀關(guān)于佛教語(yǔ)言政策的明確的指示。從這兩處的指示可以看出,佛陀的語(yǔ)言政策有三個(gè)要點(diǎn):第一個(gè)要點(diǎn)是:在語(yǔ)言與義理二者當(dāng)中,認(rèn)為主旨是義理,凡是能表達(dá)義理的就是合適的語(yǔ)言,這一原則在后來(lái)的僧團(tuán)中將被概括為“依義不依語(yǔ)”的詮釋原則;第二個(gè)要點(diǎn)是:究竟采取什么樣的語(yǔ)言來(lái)弘揚(yáng)佛法,是要根據(jù)眾生的需要,眾生使用的語(yǔ)言是什么,就應(yīng)當(dāng)用什么樣的語(yǔ)言來(lái)弘法。第三個(gè)要點(diǎn)是:一些出身婆羅門(mén)的信徒,如前經(jīng)中提到過(guò)的烏嗟呵、散摩陀,向佛陀建議根據(jù)“闡陀論”來(lái)整理佛教的經(jīng)典,這種闡陀(Chanda)論是梵語(yǔ)的音律學(xué),它與式叉論的聲調(diào)學(xué),毗伽羅論的文法學(xué),尼羅多論的吠陀難句釋一起,構(gòu)成當(dāng)時(shí)的梵語(yǔ)學(xué)。[16]12 但是將佛教經(jīng)典闡陀化的要求遭到了佛陀的嚴(yán)厲拒絕。
這里所謂原始佛教“語(yǔ)言政策”的概念,我們參考了季羨林先生的研究和提法。季先生曾研究南傳佛教《律藏》小品(Cullavagga)V.33.1 中的一段說(shuō)法,[17] 這一段說(shuō)法與我們上文所研究漢傳《毗尼母經(jīng)》的相關(guān)說(shuō)法,精神是一致的。
關(guān)于佛陀這一語(yǔ)言政策的實(shí)質(zhì)及其作用,季先生認(rèn)為:原始佛教一方面不允許利用婆羅門(mén)教的語(yǔ)言梵文;另一方面,也不把佛所利用的語(yǔ)言摩揭陀語(yǔ)神圣化,使他升為經(jīng)堂語(yǔ)而定于一尊。他允許比丘們利用自己的方言俗語(yǔ)來(lái)學(xué)習(xí)、宣傳佛教教義。這對(duì)于接近群眾,深入群眾有很大的好處。因此,“佛教初起時(shí)之所以能在人民群眾中有那樣大的力量,能傳播得那樣快,是與它的語(yǔ)言政策分不開(kāi)的;另一方面,后來(lái)佛經(jīng)異本很多,語(yǔ)言很雜,不像婆羅門(mén)教那樣能基本上保持圣典的統(tǒng)一和純潔,這也是與放任的語(yǔ)言政策分不開(kāi)的。”[28]15 季先生認(rèn)為原始佛教采用“方言俗語(yǔ)”是由于當(dāng)時(shí)傳教的實(shí)際需要,而這種語(yǔ)言政策的功能作用從整個(gè)佛教史的角度看則是有利有弊,具有兩面性。
我們的理解則是:佛陀之反對(duì)梵語(yǔ)雅文,選擇使用“方國(guó)言音”作為弘法的語(yǔ)言,不能僅僅從語(yǔ)言策略的角度來(lái)理解,佛陀這一語(yǔ)言策略是他整個(gè)弘法思想及弘法策略的一個(gè)組成部分,更廣義而言,其語(yǔ)言政策、弘法思想又是他所覺(jué)悟和開(kāi)創(chuàng)的佛教文明的有機(jī)組成部分。因此只有在佛陀智慧覺(jué)解及其弘法思想的整體脈絡(luò)中,才能夠更好地理解原始佛教“語(yǔ)言政策” 的實(shí)質(zhì)與意義。佛陀之反對(duì)梵語(yǔ),其根本的理由是他反對(duì)這種宗教建立及維護(hù)權(quán)威語(yǔ)言的歷史傳統(tǒng)和習(xí)慣做法。這與佛陀哲學(xué)思想、智慧覺(jué)解中追求平等性、尊重多元性、關(guān)切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差異性的價(jià)值取向,是完全一致的。無(wú)論是以“國(guó)土相應(yīng)法”作為原則的佛陀整體的弘法政策,還是“隨國(guó)俗言”的語(yǔ)言政策,都彰顯了他對(duì)于不同地方文化、語(yǔ)言所抱有的平等和尊重的價(jià)值考量,凸顯了佛教弘法理論及實(shí)踐的高度的交流性。
綜上所述,從以生命問(wèn)題為本位的哲學(xué)觀,可見(jiàn)釋迦牟尼智慧悟解以生命本身作為核心關(guān)懷的哲學(xué)方向,這一哲學(xué)方向開(kāi)啟了人類(lèi)一條歷久彌新的哲學(xué)進(jìn)路,也決定了原始佛教規(guī)避玄想、思辨,重視當(dāng)下生命及生命間互動(dòng)交流的智慧學(xué)底質(zhì);以慈悲、無(wú)常、無(wú)我為核心的真理觀,不僅與釋迦牟尼佛教的哲學(xué)關(guān)懷一致,也彰顯其宗教具有普世主義的倫理情懷,突破自我中心及人類(lèi)中心的價(jià)值訴求,具有倫理層面高度重視交流性的價(jià)值旨趣;以“四大教法” 為主軸的佛陀詮釋理念及詮釋原則,彰顯原始佛教思想教義詮釋上嚴(yán)謹(jǐn)性與開(kāi)放性的統(tǒng)一,啟示了佛教文本詮釋、意義開(kāi)展層面的交流性;以適應(yīng)國(guó)土、地方文化為特征的佛陀的弘法傳教思想,則彰顯了佛陀“去中心主義”的尊重包容的文化觀,展示了佛教處理與地方文化關(guān)系時(shí)重視適應(yīng)和交流的思想模式。趙樸初先生在分析佛教先輩“弘揚(yáng)佛法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問(wèn)題時(shí),曾提出在 2500 年佛教文明的開(kāi)展過(guò)程中都表現(xiàn)出重視交流互動(dòng)的特殊宗教文化精神。我們這里則特別指出:佛陀個(gè)人的佛法思想具備深刻的交流性,這一點(diǎn)在相當(dāng)程度上決定了后世佛教文明始終秉持和拓展的交流互動(dòng)的發(fā)展方向。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