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紀中晚期,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上先后建立起明朝與朝鮮王朝。兩國之間的封貢關系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到16世紀時迎來新的發展局面,并為“壬辰倭亂”(1592—1598年)時雙方得以順利建立緊密的政治、軍事同盟奠定了基礎。兩國間的封貢關系如何在16世紀的和平年代里得以深入發展呢?這與雙方間頻繁的政治互動,尤其與朝鮮采取合適的外交舉動緊密相關。而朝鮮做到及時獲悉明廷的政治動向并采取合適的外交舉動離不開情報搜集活動。在16世紀前,朝鮮已經通過外交活動、軍事秘密活動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備的對明情報搜集體系。1同時兩國的邊疆地區——遼東與平安道地區也在情報傳遞上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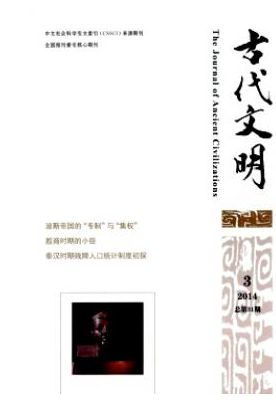
本文源自古代文明2021年1期反映和推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增進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提供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信息。刊發關于古代文獻的文本研究、個案實證研究、區域文明和全球文明關系研究、歷史文化解釋性研究,以及關于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和重大理論問題的闡述、評論、綜述與爭鳴等學術文章。
關鍵詞:信息流通;情報搜集;朝鮮使臣;朝鮮王朝;明鮮關系
從15世紀晚期開始,全國性的市場網絡逐漸在明朝形成,信息流通的速度進一步加快。所謂的“朝報”(也稱“邸報”“通報”)在明朝士紳社會廣泛傳播,并成為官員、士大夫以及識字民眾了解政局變化的重要讀物。它作為明廷政務公開和議政公開的渠道,能提供可信度極高的政治情報。3明朝的朝報主要依賴手抄流傳,后來也出現了雕版刊刻與活字印刷的朝報。4總之,獲見朝報并非難事,朝報可以說是士紳社會最常見的政治讀物之一。
臺灣學者王鴻泰認為,朝報的傳播功能構成一個“虛擬舞臺”,讀物與讀者之間構成了一個臺上與臺下、看與被看的關系。不同地區的讀者聚集在此舞臺前,他們是觀眾,但不是被舞臺隔絕的沉默觀眾。知識分子閱讀朝報,往往會對具體事務展開討論,這種討論就是一種參與。在朝報的傳播作用下,朝報的讀者們共同思考國家的運作。1這樣的看法的確很有道理,但僅把目光局限于明朝一國,是遠遠不夠的。實際上,整個東亞世界都是這樣一個由信息發布、流通和互動構成的舞臺。如果把朝鮮等朝貢國都納入考慮范圍的話,這個舞臺的性質和信息互動的機制,其實遠比明朝自身要復雜,也始終在影響明朝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可以預見,明朝的信息流通情況很可能對朝鮮的情報搜集活動產生影響。國內外學界已然注意到朝鮮對明情報搜集活動,并將研究重點放在兩國關系的變化,朝鮮對“土木之變”、“大禮議”、《大明會典》修撰等事件的情報搜集與外交回應上,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2不過既有研究較少關注朝鮮情報搜集活動本身的變化,朝鮮君臣如何看待各類情報來源等問題。朝報等明朝文書流入朝鮮,究竟給朝鮮帶去了怎樣的信息,又對朝鮮的外交回應乃至兩國關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仍待進一步研究。因此,本文將以朝鮮君臣對各類情報來源的認識為線索,通過若干案例探討朝鮮在16世紀和平時期如何根據搜集到的明朝情報做出外交應對,并分析兩國之間的信息流通情況。
一、正德帝駕崩與朝鮮的情報判斷
在封貢關系中,明朝是東亞這個更大的信息流動空間里的中心、源頭和主導者,也是話語權更重的一方,所以信息往往是由明朝傳至朝鮮,并對朝鮮政局產生影響。而信息傳播的渠道本身又相當復雜,常有失實或滯后的問題。這樣一來,朝報的優勢就漸漸顯現出來。
老皇帝駕崩與新皇登極無疑是明廷最重要的政治變動,也是朝鮮最為關心的事項。15世紀以來,隨著儒教化的不斷深入,朝鮮朝廷編定了一系列禮學書籍,如《國朝五禮儀》《五禮儀注》等,以供禮儀之需。按《五禮儀注》規定,“初聞皇帝喪即變服,第四日成服”。3問題是從何處“初聞皇帝喪”可以被視作可靠的消息來源。永樂帝駕崩時,朝鮮在接到明朝詔書前已通過使臣樸得年在遼東抄到的皇太子令諭獲知消息。國王世宗隨即舉哀并派進香使崔迤等人赴明。崔迤等人在遼東湯站附近遇到正趕赴朝鮮頒詔的明使,遭到“詔書未到前,以私通消息入朝可乎”的斥責。于是世宗命令崔迤等人在邊境待命,等明使完成頒詔任務后再赴北京。4到第二年洪熙帝去世時,朝鮮吸取了教訓,在明朝詔書到達后才舉哀并派出慰問使。5可見朝鮮并不想觸犯明朝的禁令,落得“私通消息”的罪名。在明朝看來,朝鮮可以通過明廷發出的詔書﹑敕書等正式文書獲取消息,但私自打探情報則有觸犯禁令的嫌疑。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正德帝崩于豹房。6他在駕崩前的二月中旬曾派太監金義、陳浩等人赴朝鮮頒敕。1四月十三日,明朝敕使團的副使陳浩在到達良策館(今平安北道龍川)時偷偷告訴朝鮮通事安訓:“俺等到廣寧,聞皇帝兇訃。朝廷捉囚江彬,皇太后定策立弘治親弟,頒詔天下云。”陳浩稱自己本是朝鮮人,擔心朝鮮不能應付敕外征索之事,所以特意提前通知此事,并讓安訓轉告遠接使安潤德。同時,正使金義也暗將訃音告知朝鮮通事李和宗。2安潤德接到消息后,立刻讓通事們向明朝敕使團中的相熟人士進一步打探情況,得到“到遼東,哀書至,乃知皇帝去三月十六日已崩。但頒敕前,兩使秘而不發,慎勿喧說”的答復。3安潤德隨即將該情報以狀啟的形式上告朝廷。
這封狀啟立刻引發軒然大波。朝鮮君臣針對該消息是否屬實,是否該即刻舉哀展開討論。領議政金詮等人認為既然消息來自明使,那應該不是謊言,但明使不愿將此消息廣而告之,實在讓人難以理解。于是他們提議向遼東派出押解官,打探遼東是否舉哀,這樣即可確認消息的真假。所謂押解,表面上是把貢馬或漂流民送至遼東,實際上可借押解的名義,進入明朝境內打探情報。司諫院認為既是明使親口告知的訃音,定然不假,應該立刻派人向金義等人追問正德帝死因。若訃音屬實,朝鮮在迎敕前必須舉哀。國王中宗否決了這一建議,理由是公然追問訃音,可能惹怒明使。中宗表示:“我國之計,惟待中朝之命而已。”4
中宗的擔心自有原因。在正德帝駕崩前幾年,曾出現過諸如正德帝被蒙古人俘虜、明朝對皇太后去世之事秘不發喪等虛假流言傳到朝鮮等情況。5對于正德帝駕崩這種大事,朝鮮若僅憑明使私下的傳話就貿然舉哀,萬一消息不實,不僅會被世人嘲笑,更有可能惹怒明朝。此外,中宗不愿即刻舉哀還有對日交鄰層面的考慮。當時日本使節正停留漢陽,他早已決定要在四月十七日于正殿接見日本使節并舉行宴會。如果舉哀,勢必要停止這些禮儀活動。朝鮮不便以明使私下告知的皇帝訃音為由,突然決定不接見日本使節。6實際上,明使告知朝鮮的消息的確存在一些問題。如正德帝駕崩的日期不是十六日而是十四日,以及新皇帝非弘治帝親弟,而是弘治帝之侄朱厚熜。
領議政金詮等人支持中宗的決定。在他們看來,“帝崩之言非公文頒布事,天使之語通事又是秘密,不令下人知之,則不可以此而舉哀也”。可見在當時朝鮮官員看來,最可靠的消息來源當是明廷頒布的公文。大司憲洪淑等人向中宗建議派人直接向明使發問,但遭到否決。中宗表示,此前曾多次聽說正德帝駕崩,最后都被證明是明朝人怨恨皇帝無道而捏造的假消息。這次明朝敕使團中有人說是在廣寧聽到訃音,有人說是在遼東聽到訃音。同屬一個使團,竟然出現消息來源各異的情況,這難免讓人起疑。但為保險起見,中宗勉強同意派人赴遼東。眾臣亦贊同此舉:“既送人遼東,命探問朝報,姑待此人之還,至為便當。”中宗最后決定:“三月十六日皇帝崩逝云,則公文必近日當到,往遼東人亦不久而還。姑待近日,可也。”7該對話是朝鮮史料首次明確提及明朝朝報的存在。8從朝鮮君臣的反應來看,在這之前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朝報的可信度。通過該次討論,朝鮮內部就等待可靠消息到達后再為正德帝舉哀達成了一致。
盡管中宗在口頭上一再表示不能立刻為正德帝舉哀,但在實際行動上已為新皇即位做好了準備。四月二十三日,他任命李惟清與韓亨允分別擔任賀登極正使、副使。9這樣一來,一旦確認新皇即位,朝鮮就可以盡快派出使節。二十六日,通事金亨錫傳回了從明朝人鄭臧等人處聽到的消息。鄭臧等人稱:“聞皇帝過飲冷酒,二月十四日吐血而崩。”針對新皇帝是誰的提問,鄭臧等人回答:“成化之子興王已死,其子襲封為興王,年甫十三。”1雖然朝鮮搜集到的情報存在細節上的差異,但所有情報均指向正德帝已經駕崩。于是中宗召大臣共商謝恩表文文辭與舉哀諸事,然而改動謝恩表文一事非常棘手。中宗認為:“時無明降,謝恩文書改之為難。若中朝以為‘朝鮮何以先知乎,則將何以答之?”考慮到“我國不見公文而但聞傳言即舉哀,亦所未安不小”,因此中宗決定待派往遼東的通事回國后再商議此事。2可見中宗非常擔心明朝可能察覺朝鮮的情報搜集能力,出現不必要的麻煩。此時舉哀問題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接待日本使節的典禮已經完成,為明朝皇帝舉哀是僅在朝鮮國內舉行的儀式,既然多個情報源都稱皇帝駕崩,那朝鮮只需確認消息即可。所以當平安道觀察使呈上狀啟,稱押解官魯繼孫等人在遼東湯站探問朝報,獲得張千戶與湯站指揮對皇帝駕崩一事的肯定答復后,中宗隨即下令當日舉哀。湯站指揮稱:“皇帝去三月十七日崩逝,哀書已到,皆著衰服矣。”3雖然史料未提張千戶與湯站指揮的消息源是朝報,但此時朝鮮君臣認為明朝朝報是可信的消息來源應無疑義。
六月初,賀登極使李惟清啟程赴北京。4他發回的狀啟于九月中旬到達朝鮮。按狀啟所錄,李惟清在北京“看得奇別一本”,內容是明朝即將派唐皋為首的詔使團赴朝鮮宣詔,并將嘉靖帝的賞賜帶去朝鮮。中宗隨即下令迅速做好接待明使的預備工作。5“奇別”在朝鮮語中有兩層意思,一是泛指“消息”;二是特指“朝報”,朝鮮亦以“奇別”稱呼本國的朝報。李惟清所稱的“奇別一本”顯然指的是明朝朝報。明朝令唐皋等人赴朝鮮頒詔的日期是八月二十六日,6考慮到從北京到漢陽至少需花費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可知李惟清是在讀到朝報后就派人快馬加鞭將消息送至本國。
朝鮮使臣重視明朝朝報是因為在使行途中或歸國之后,必須以聞見事件或狀啟的形式將見聞報告國王。歷年的聞見事件會被朝廷整理為《聞見事件謄錄》,作為了解明朝動向的參考。7朝鮮成宗二十四年(1493年),成宗以聞見事件里多有誤處為由,令司憲府審問千秋使書狀官房玉精。8這就要求使臣在撰寫報告時不得不對情報的來源多加留意。為避免事后被追責,朝鮮使臣自然傾向搜集可信度較高的情報。于是明朝朝報作為可信的情報源之一開始出現在使臣的報告中,并成為朝鮮國王制定應對策略的重要參考。
通過以上事例可知,明朝的消息在傳向朝鮮的過程中時常出現真假摻雜的情況,這給朝鮮君臣做出判斷造成了較大干擾。朝鮮在制定對明外交決策時,最相信的當然是明廷發出的公文,但在無法及時獲得公文的情況下,也會主動利用各種渠道搜集朝報等文書。可見16世紀初的朝鮮朝廷公認朝報是可信的明朝消息源。
二、嘉靖“大禮議”與朝鮮的情報搜集
朝鮮使臣對明朝朝報的著力搜集,客觀上讓朝報的流通超越了國界,并將朝鮮帶到明朝的政治舞臺前。朝鮮君臣通過閱讀朝報,可以像明朝士大夫一樣,經由解讀具體事務來建立自身與明廷的聯系。但與境內讀者不同的是,朝鮮君臣的明朝朝報閱讀行為帶有極強的風險預防與自保目的,即為應對與明朝交涉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朝鮮有了解明廷的政治﹑軍事情況的迫切需要。同時,通過外交應對舉措,朝鮮也可直接參與明廷政治舞臺的表演,主動建設和調整與明朝的關系。
嘉靖帝推動的一系列對親生父母的追尊之舉,給朝鮮高度參與明廷的政治表演創造了機會。在即位不久就引發“大禮議”的嘉靖帝需要朝鮮的政治協作來展示自身的合法性,而朝鮮中宗依靠勛舊大臣發動“丙寅政變”(1506年),將燕山君廢位才得以登上王位,也迫切需要明朝的政治承認與支持。尤其是“己卯士禍”(1519年)后,中宗面臨勛舊勢力與士林勢力長期對立的局面,需要在連續不斷的政治漩渦中強化王權。相互的政治合作需要成為兩國關系不斷深化的基礎。1朝鮮在這一時期存在強化對明情報搜集,進而做出合適回應的強烈動機。
嘉靖帝繼位后,楊廷和等人建議尊孝宗弘治帝為“皇考”,尊嘉靖帝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嘉靖帝不從,堅持要給親生父母上皇帝與太后的尊號。這便是“大禮議”的開端。朝鮮使臣對“大禮議”情報的搜集,大致通過三種途徑:一是由通事直接與明人交流;二是搜集明朝各種朝報、題本等政府文件;三是搜訪明朝公布的“大禮議”文獻。2第一種方式很可能因口頭傳話造成情報謬誤,而第三種方式有時間上的滯后,即等到“大禮議”文獻頒布后,朝鮮可能錯過采取外交行動的最佳時機。所以綜合來看,朝報、題本等文書更可能為朝鮮及時做出外交回應提供參考。
朝鮮中宗十九年(1524年)六月二十二日,謝恩使申鏛派遣的先來通事回到朝鮮,告知朝廷:“皇帝加上昭圣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圣康惠皇太后,興獻帝尊號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加上興國太后尊號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中宗不確定是否應該派遣進賀使。承文院提調建議:“加上尊號之例于《謄錄》不載。然臣等意以為前者上尊號時既已進賀,今亦進賀為宜。”于是中宗傳下教旨:“今承文院提調以為宜進賀,不必更議也。”3
幾天后承文院提調又否定了之前的看法。他指出本次進賀與此前遣使進賀皇太后上徽號只是類似而并不相同,中宗因而讓眾臣商議此事。領議政南袞、左議政李惟清等人表示雖然派遣進賀使會給朝鮮造成一定的經濟負擔,但“事大之禮,不可以私廢”,所以還是遣使為妥。但就該如何書寫進賀表文中的尊號,朝鮮君臣仍有疑慮。4在多次討論未果的情況下,承文院提調認為在進賀表文內書寫“本生”等字樣沒有先例,建議派押解官赴遼東探問。該建議獲得中宗的許可。5一個多月后,押解官裵瑊從遼東帶回了“令我國進賀之咨”。6然而遼東咨文并沒有明示朝鮮的表文該不該去掉“本生”二字。又過了近一個月,圣節使方輪派遣的先來通事回到朝鮮,該通事帶回的狀啟中提到大量明朝官員反對去“本生”二字而被嘉靖帝嚴厲處罰的情況。7方輪寫道:“中國去‘本生二字,朝廷方爭論。我國于進賀表去‘本生二字則似聞見而不書。”議政府三議政讀完方輪的狀啟與帶回的明朝朝報后認為,進賀表文中去掉“本生”二字沒有問題,問題在于表文中若是明寫“因申鏛來,得聞而不書‘本生字”,明廷可能認為朝鮮是擅自行事,所以建議把表文改成“因遼東咨文得聞”。隨后朝鮮派出了以許淳為首的進賀使團赴北京。8雖然給朝鮮帶去確切情報的是使臣狀啟與明朝朝報,但這樣的情況不便讓明廷知道,遼東咨文等文書仍是朝鮮獲得明朝情報的合規途徑。換言之,朝鮮非常清楚明朝僅許可朝鮮接觸其樂意公開的部分情報,而朝報上含有大量明廷未必樂意向外國公開的信息。對朝鮮來說,這恰是朝報最具吸引力的部分。通過朝報,朝鮮得以細致了解明朝政局的最新動向,從而采取合適行動滿足明朝皇帝的期待,并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國利益。
從嘉靖帝的立場來看,在未獲國內廣泛支持的情況下,若能得到來自有“禮儀之國”之稱的朝鮮的支持,顯然可以為自己的行為增加合法性。朝鮮的表文不書“本生”二字,更是符合嘉靖帝的期待,所以他對朝鮮大加賞賜。1在朝鮮時代,如果國王獲得明朝皇帝的優賞,根據優賞的具體情況,首都或地方的文武百官要向國王進賀。這是國王向全體臣民夸示王權的政治儀禮,也是國王積極采取符合明朝皇帝期待的外交行動的動機來源之一。2
然而朝鮮的進賀之舉也在內部引發了“我國以海外之邦先為進賀,則無乃助成其邪論”的擔憂。盡管中宗列出“中原之事,非我朝所得以是非之也”等理由為自己辯護,3但內心深處仍有不安。該年底的一次經筵中,中宗提及自己讀到明朝朝報,其中有嘉靖帝將生父稱為皇考的內容,但他不確定嘉靖帝是否會把生父升祔太廟。在他看來,“若以祔于太廟,則昭穆之制舛矣”。經筵檢討官趙仁奎認為嘉靖帝把興獻帝稱為皇考,肯定是為祔廟做準備,這是不顧大義的行為。中宗贊同這一判斷,但又表示:“中原事,固不可是非也。但于外國之見,亦未安矣。”4朝鮮君臣明知嘉靖帝的行為不符合程朱理學的“禮”,但出于鞏固兩國關系的考慮,仍采取了迎合嘉靖帝的行動。這也印證,16世紀作為朝鮮儒教化加深的時期,程朱理學的價值判斷雖不一定會反映在實際對明交涉中,但日益影響朝鮮君臣的思考方式。5同時,明朝朝報傳到朝鮮,也為朝鮮君臣提供了與聞明朝政治的機會。他們通過閱讀朝報,得以了解明朝的政治運作并為參與明朝政治博弈做出準備。
朝鮮君臣就明朝朝報展開討論的習慣亦被后世繼承。朝鮮明宗十一年(1556年)十一月,領經筵事尹溉向明宗提到自己讀到明朝朝報,其中有“中原地震地坼,平地山出”的內容。尹漑認為萬一明朝出現變亂,與明朝接壤的平安道會首先遭到沖擊,因而建議強化平安道的防備。明宗接受了建議,并強調:“大國無事,然后小國可安。”6朝鮮對明朝的動向一直抱有極大的關注,這不僅是因為地理上的鄰近,更因為在國家規模﹑軍事實力等方面與明朝相比,朝鮮始終處在一種非對稱的位置上。7這種非對稱關系的一大特點是,與關系中勢力較強的一方相比,較弱的一方更容易受到影響。這是因為雙邊互動對弱國的影響遠甚于強國,弱國面臨著更大的風險和利益。8朝鮮與明朝的關系正是如此,所以朝鮮君臣始終注視著明朝的動向,擔心局勢變化會對朝鮮產生影響。為應對兩國交涉中可能發生的問題,朝鮮需要了解相關信息。也就是說,朝鮮可以用對明朝的了解來消解非對稱關系可能對其不利的一面。9而朝報恰是可以滿足這樣需求的信息媒介。朝鮮君臣通過閱讀朝報,了解所需信息,可以及時做出準備。
此外,明朝朝報上登載的關于朝鮮的內容,也為明朝人了解朝鮮提供了信息參考。嘉靖十六年(1537年)九月初,戶科給事中吳希孟的家人吳天定等人來到朝鮮使臣的住所——玉河館,將吳希孟連上兩道題本夸獎朝鮮的消息告知朝鮮通事車允成等人,此前一年吳希孟曾赴朝鮮頒詔。車允成等人回答:“近日到京師,求見通報,知老爹奏意,使臣以下不勝感激。”10吳希孟在題本中稱朝鮮“素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并建議朝廷“自今凡詔告敕諭,事關禮制者宜使之一體知悉”。11車允成等人見到的朝報很可能出自玉河館。當時玉河館中有供提督主事等官員閱讀的朝報,朝鮮人通過賄賂即可得見。12按朝鮮中宗三十四年(1539年)進賀使李芑的報告,正是由于吳希孟等明使“以我國知禮義之意達之于皇帝前,故中朝之人,前稱我國人必曰‘夷人,今則稱為‘使臣也”。1借由朝報的流通作用,朝鮮的“禮儀之國”形象在明朝社會擴散,并對明朝人的朝鮮認識產生了積極影響。
總之,明朝朝報在給朝鮮提供可靠信息的同時,將朝鮮與明廷、乃至明朝的民眾更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以朝報為媒介,兩國間形成一個“共享”的信息世界。在這樣的信息流通過程中,朝鮮不僅是明朝政治舞臺的觀眾,也可以是通過事大禮儀介入明廷政治博弈的參與者。
三、“壬寅宮變”與朝鮮的情報回應
朝鮮君臣從16世紀起逐步將明廷的朝報、題本等官方文書視為重要的情報來源,但這并不意味著朝鮮在做出局勢判斷時完全依賴它們。這些文書有官方背景,在刊登負面情況或宮闈之事時常有隱諱,這就要求朝鮮必須綜合考慮各種情報的可信度。與“大禮議”不同,朝報不便大張旗鼓地刊登“壬寅宮變”這種可能暴露皇帝無道的宮闈之事。但恰是這種不便明說的宮闈之事,可為我們提供探究朝鮮如何獲得宮闈消息并做出回應的線索。
除史料價值之外,這些明朝朝報對趙憲這類關注社會現實、希望改革弊政的朝鮮士人產生的影響亦值得進一步關注。2實際上,趙憲使行過程中已多次目睹明朝吏治的腐敗情形,并多有批判,但他在歸國后上交宣祖的改革方案——《先上八條疏》中卻把明朝描繪成一個值得朝鮮學習的“烏托邦”。按夫馬進的解釋,趙憲為批判朝鮮的現狀,最有效的方法是將明朝作為一個完整的烏托邦提出。當時朝鮮正在推行鄉約,如果介紹說明朝讓愚蠢糊涂的人擔任約正與副正,那么就無法進一步展開議論。3宣祖以兩國風俗不同不必操之過急為由拒絕了《先上八條疏》,4所以趙憲不便再遞交后來的《擬上十六條疏》,但《擬上十六條疏》的價值仍不可忽視。趙憲在該文中多次引用明朝朝報,以朝報刊登的明朝政治運營事項來強調改革的必要性。這為我們探究朝鮮士人如何閱讀并利用明朝朝報提供了線索。
首先,趙憲在第一條疏——《格天之誠》中建議宣祖:“臣伏愿殿下先盡修省之道,以為格天感人之本。”為說明此主張的合理性,趙憲以萬歷帝的行為作為依據。趙憲寫道:“皇上憫念畿內亢旱,筑壇宮中,竭誠露禱;通行諸司,一體省戒。中外人心無不感悅云。”5這段引文來自《中朝通報》八月十四日條,即江西巡按御史凌云翼報告洪水肆虐并請求朝廷賑災的奏疏。凌云翼為說明災情的嚴重與賑災的緊迫性時,提到了此前畿內干旱時萬歷帝曾在宮中筑壇祈雨的先例。6
其次,趙憲在第七條疏——《聽言之道》中建議宣祖多納諫言,聽取朝廷公論。趙憲描述道:“臣于皇上納諫之事,雖未詳聞,而伏見通報,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撫按御史日有奏疏,例下該部,使之詳議。該部覆奏則詢于閣老,無不施行。是則天下之事,一付于朝廷之公論,而帝不敢以一毫私意容于其間,且不為近習之言所遷惑也。”7不過趙憲所謂的官員奏疏均由朝廷公論決定的情況并不符合事實。1574年正是張居正手握大權的時節,比起皇帝的私意與朝廷的公論,顯然是張居正的政治意圖更多反映在政治運營中。趙憲對此也并非一無所知,但他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仍把朝報記載的情況視為朝鮮應該學習的榜樣。趙憲對明朝朝報的論述,與其說是如實說明,毋寧說是將政治憧憬與朝報內容混合在一起而做出的偏向性分析。趙憲在奏疏中大段引用明朝朝報來強調論據的可信度與主張的合理性,這首先表明朝報作為可信度較高的明朝政治參考資料,在朝鮮政界已獲得普遍認可。
再次,趙憲的事例也反映出這一時期朝鮮使臣對明朝朝報的有意識閱讀與記錄,不僅是為了滿足情報搜集與復命之需,也是他們積極參與本國政治實踐的重要手段。朝鮮建國后的百余年間,儒教理念逐漸在朝鮮社會生根發芽,培養出一大批對儒教理念深信不疑的士林派人士。但在士林派看來,16世紀的社會現實與他們所憧憬的儒教理念間存在巨大鴻溝,即朝鮮社會并不是那么“儒教”。這就促使士林派人士采取各種措施,努力把儒教理念落實到國家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把朝鮮建設成一個名實相副的儒教國家,可以說是士林派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之一。宣祖即位后,為因“己卯士禍”遭遇不幸的士林派平反,士林派從此大舉登上政治舞臺。趙憲作為士林派西人黨的一員,尋求各種政治資源來支撐改革主張自是情理之中。在當時朝鮮君臣看來,朝鮮王朝的立國之本在于兩方面:一是通過對明事大緊隨中華秩序;二是積極接受以明朝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儒教理念。1這兩點其實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也是朝鮮政壇上無需多言的政治正確。通過學習明朝來改造朝鮮不夠“儒教”的地方,可以說是將朝鮮盡快儒教化的捷徑,也是朝鮮大量引入明朝禮儀、制度、文化的動機所在。盡管趙憲在使行途中目睹了明朝腐敗叢生的景象,與他憧憬的儒教國家相距甚遠,但他不得不考慮的是,在當時朝鮮人的認知里,明朝仍是儒教文明國家的最佳代表。如果說作為儒教發源地的明朝都沒能落實儒教理念,那朝鮮學習明朝豈不是失去了意義?考慮到兩國之間的封貢關系與朝鮮人將明朝視為“君父之國”的心態,就算有人覺得明朝不夠“儒教”,此時也不太會有另起爐灶,否定明朝而自封本國為中華正統的強烈動機。趙憲正是利用了朝鮮國內這種將明朝視為名正言順的改革榜樣的心理。雖然明朝的腐敗現實不能給他的改革主張提供依據,但代表明廷官方立場且被朝鮮政界普遍認可的朝報可以為他的觀點增加說服力。
最后,通過趙憲的記錄與取舍選擇,明朝朝報的部分內容得以在朝鮮士人中流傳,并進入后世朝鮮社會的政治談論中,與朝鮮的政治改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趙憲去世后,他的文集——《重峰集》由同屬西人陣營的安邦俊于朝鮮光海君十四年(1622年)整理刊行。包括《中朝通報》在內的使行日記、《先上八條疏》《擬上十六條疏》等各種文稿均被收入《重峰集》。朝鮮仁祖元年(1623年),西人政權上臺執政。他們不滿此前北人政權主導編纂的《宣祖實錄》而另修《宣祖修正實錄》。趙憲的《先上八條疏》與《擬上十六條疏》也被添入這部改修實錄中。2可見實錄修纂官讀過《重峰集》,并認為這些文稿是應該補入實錄的內容。朝鮮仁祖八年(1630年),兵曹判書李貴向國王仁祖解釋朝鮮官員向明朝官員詢問禮儀原有前例,并舉趙憲之例“宣祖朝趙憲以質正官奉使天朝,與中朝士人輩互相問答,兼采中朝典禮十八條,枚舉疏陳。”3顯然李貴曾讀過趙憲的奏疏。朝鮮英祖二十四年(1748年),國王英祖為表彰趙憲的功績,下令校書館以活字重刊《重峰集》。《中朝通報》通過《重峰集》的刊行與流通,得以進入朝鮮士人的閱讀范圍,成為后世朝鮮士人了解當時明朝政治運營與朝鮮自身改革情況的重要資料。
趙憲使行結束后沒幾年,漢陽城中的“識字游食之人”開始模仿明朝以活字印行朝報的習慣,開刻活字印刷本國的朝報賣以資生。宣祖偶然見到了這樣的朝報,震怒道:“刊行朝報與私設史局何異?若流傳他國,則是暴揚國惡也。”印刷朝報之人因此被處以極刑,4活字印刷的朝鮮朝報也從此銷聲匿跡。朝鮮的朝報由奇別書吏每日在承政院抄錄而成,再通過他們送給相關衙門與官員。但通過奇別書吏抄錄并傳播的朝報數量并不大,難以滿足識字階層對國家政事的了解渴望。朝鮮人會生出仿照明朝以活字印刷朝報的念頭,暗示了這一時期已有不少明朝朝報流入朝鮮,并為“識字游食之人”所知。而宣祖對本國朝報流至外國的擔憂,很有可能也是有鑒于明朝朝報流入朝鮮的情況。朝鮮君臣雖然通過搜集、閱讀明朝朝報與明廷的政治表演發生聯系,但絕不希望其他國家通過類似的方式進入朝鮮的政治空間,明朝也概莫能外。朝鮮一方面標榜“事大至誠”,認為自己無異于明朝的“內服”;但另一方面,在可能沖擊本國政治運營的信息流通問題上,對明朝等其他國家展現出強烈的提防心態。
結語
考察16世紀朝鮮對明朝情報的搜集活動可知,明朝朝報、題本等文書作為比較可信的信息來源在這一時期進入朝鮮的情報搜集范圍,并成為重點關注對象。正德帝駕崩、嘉靖“大禮議”等重大事件發生時,朝鮮君臣面對紛紜雜亂的信息,往往依賴明朝朝報、題本等來判斷消息是否屬實。通過這些文書,朝鮮可以詳細了解明朝政局的最新動向,從而采取符合明廷期待的回應舉動,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國利益。
明朝朝報、題本等文書作為有效的信息傳遞媒介,在兩國間構筑出一個“共享”的信息世界。明朝自身的信息生產和傳播能力和方式,是這個機制的物質基礎。朝鮮君臣通過閱讀這些文書,得以近距離地觀察明朝政治動向,并可以通過事大禮儀介入明廷的政治博弈,強化本國在明朝中心的東亞秩序中的地位。
明朝憑借政治地位,讓它的信息生產和流通模式成為封貢體系內的主流形式,但朝貢國仍有利用和調整它的主動性。表現之一是朝鮮士人能主動利用明朝的這些信息資源來作為干預朝鮮本國政治,表達自身政治理想的一種手段,如趙憲對明朝朝報的閱讀與記錄,將明朝朝報作為一種政治情報資源,引入朝鮮的政治討論中;表現之二是朝鮮受到明朝朝報影響并開始模仿明朝朝報的發行方式時,會根據本國的情況加以調整,如宣祖禁止模仿明朝朝報以活字印行朝鮮朝報。總之,明朝朝報等文書的流通作用,給朝鮮開啟了兩方面的可能:一是朝鮮作為明朝的重要政治合作伙伴,參與明廷政治博弈的可能;二是朝鮮士人通過閱讀與記錄這些文書,將其引入本國政治實踐的可能。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