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作為媒介考古學的電影史:追溯數(shù)字電影》是埃爾塞瑟二十五年間對媒介考古學的整體反思之作,也是他對數(shù)碼轉型視野下電影史的重新評估。西方影像文化受數(shù)字技術沖擊已然經(jīng)歷了決定性的范式轉變,埃爾塞瑟的著作以此為背景建立了新的電影史學模型,測繪運動影像和視聽經(jīng)驗的場域,探尋多個源頭、多種形態(tài)的電影史。他采用“回溯—前瞻”的研究路徑,發(fā)現(xiàn)了早期電影與數(shù)字電影的平行視點,質詢以數(shù)碼為代表的斷裂時刻,并在超越新舊媒介對立的嘗試中顯露出媒介考古學當前作為一種方法、實踐以及可能的學科所面臨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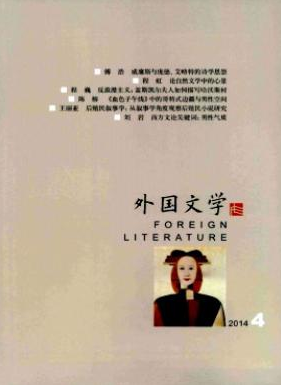
張馳, 外國文學 發(fā)表時間:2021-09-22
關鍵詞:埃爾塞瑟 媒介考古學 電影史 數(shù)碼轉型
2016 年,托馬斯·埃爾塞瑟(Thomas Elsaesser)的《作為媒介考古學的電影史:追溯數(shù)字電影》(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 Tracking Digital Cinema,以下簡稱《電影史》)出版。作為“轉型中的電影文化”(“Film Culture in Transition”)系列的第 50 部著作,該書的面世在提示著電影史之豐盈、電影研究之蓬勃的同時,確認了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并顯現(xiàn)出埃爾塞瑟本人因長久以來的理論關切所促成的影響軌跡。在《電影史》中,埃爾塞瑟經(jīng)由媒介考古學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二十五年來對電影史諸議題的分析,在考掘和納新的交織中放大了電影史主流敘述的不確定性,是其系列著述的延續(xù)和結晶。推動埃爾塞瑟將其漫長思考集結成書的根本原因,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示,在于數(shù)字媒介的迅速普及和迭代,它引致的文化斷裂及其對電影命運的深刻影響使得人們很難用直接的單一因果鏈條解釋其中機理。在埃爾塞瑟看來,“數(shù)碼已不再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危機和轉型的‘文化隱喻’” (Film 232)。就身處數(shù)碼轉型中的電影而言,埃爾塞瑟既懷疑“完善技術”“愈加寫實”(greater and greater realism)或“媒介融合”等類目的論式的描述,更否認伴隨而來的數(shù)見不鮮的電影已 / 將終結的宣言。相應地,他把數(shù)字媒介視為一場契機,媒介考古學則為其反應與癥候,用以重新探尋認識的連續(xù)性與斷裂處,重新思考電影史觀的變革,重新劃定電影研究的邊界,以便在學術、文化和經(jīng)濟的新圖景中認知“電影的特殊性和運動影像在現(xiàn)代性和大眾媒體歷史中占據(jù)的角色”(埃爾薩瑟 26)。本書評將在概覽媒介考古學理論語境的基礎上,呈現(xiàn)埃爾塞瑟涵納新舊媒介的影史模型,及其對新舊媒介之緊密聯(lián)系的闡釋和對電影未來的冀望,反思媒介考古學面對當代電影研究的主要局限,以期加深對埃爾塞瑟及其電影史觀的理解,并由此在更廣闊的意義上反思(電影的)數(shù)碼轉型問題。
“媒介考古學”的概念溯源
就其命名而言,“媒介考古學”顯然受惠于福柯的理論資源,加之本雅明、法國 “年鑒學派”、麥克盧漢等人的思想導引,媒介考古學始終嘗試回返媒介技術的發(fā)生源頭,打開具有內在裂隙的、充滿“漏洞”的媒介時空,集結媒介更迭的紛繁插曲,恢復逸出主脈 / 捷徑的媒介實踐,重估媒介歷史與媒介文化的意義和價值。簡言之,媒介考古學旨在改寫媒介正史中連續(xù)、自洽的發(fā)展主義邏輯。這一取向與 20 世紀后半葉反思現(xiàn)代性、總體性、歷史主義的話語相符合,也與多數(shù)聚焦復雜系統(tǒng)中復雜關系的現(xiàn)代科學研究相符合:“因與果是雙向且多樣的”(McClintock),沒有任何必然的指向或匯流。通過重訪那些在寬廣時空內同時發(fā)生的媒介現(xiàn)象,召喚那些被壓制、被忽視和被遺忘的媒介幽靈,媒介考古學拓寬了自身視野,并日漸為學界所熟悉、青睞。
若想繼續(xù)對媒介考古學分類,按照胡塔莫等(Erkki Huhtamo)的觀點,該領域通常呈現(xiàn)一種二元劃分,“一方是以社會性和文化性為導向的英美研究,另一方是以技術—硬件為導向的德國學者”,而這種差異基本可以歸結為雙方對福柯理論進行不同解讀的結果:英美學界傾向于強調福柯的話語作用,認為媒介的意義來源于它們被引入和被調解的語境;德國學界則認為非物質力量次于物體、技術、制度等“原初動力”,相對更為重視“硬”技術的影響力(7-8)。德國傳統(tǒng)對于媒介“恢復物質性”“尋訪異質性”和“捕捉復現(xiàn)性”的重視(施暢 39-44),使其在媒介考古學的脈絡中更為凸顯。基特勒(Fredrich Kittler)和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方法是當中較為重要的兩條路徑。盡管基特勒曾否認自己與此領域的關聯(lián),但他在《話語網(wǎng)絡 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和《留 聲 機,電 影,打 字 機》(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中對媒介—技術之于西方文化的開創(chuàng)性論述強烈影響了德國媒介考古學的各種變體。基特勒主張將技術—歷史事件納入福柯的話語分析,因為媒介技術的革新改變著意義生成、詮釋與傳遞的條件,決定了人的構成而非僅是“人的延伸”,話語自身、權力以及歷史的性質都在發(fā)生不可逆轉的范式變革。與基特勒不同,齊林斯基則用大量歷史幽深之處的異質性材料來對抗不斷進化的媒介演變,拆解漸趨同化、固化的媒介霸權。他在代表作《媒體考古學:探索視聽技術的深層時間》(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中帶著譜系學視野進入歷史斷層,挖掘了數(shù)位失落的媒介天才及其被淹沒或邊緣化的技術裝置,嘗試追蹤媒介往復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運動軌跡。盡管齊林斯基在重繪媒介文化版圖時對系統(tǒng)化和理論化的抵抗值得稱道,但又不乏原子論的風險(胡塔莫等 12)。
受上述兩種問題意識影響而發(fā)展起來的各種媒介考古學變體,業(yè)已成為當前人文科學最具生產(chǎn)力和影響力的前沿領域之一,受其滋養(yǎng)、與之并行的“新電影史”(new film history)選擇了聚焦電影媒介的問題域。1986 年,埃爾塞瑟首次發(fā)表以“新電影史”為題的文章,涉足這一領域的學者始于伯奇(Noël Burch)和索特(Barry Salt),歷經(jīng)馬瑟(Charles Musser)、岡寧(Tom Gunning)、戈德羅(André Gaudreault)、多恩(Mary Ann Doane)、弗萊伯格(Anne Friedberg)等人,還包括自 2005 年起埃爾塞瑟與其同事召集的“想象(過)的未來”(Imagined Futures)研究項目,新電影史的事業(yè)仍在拓展。與其他媒介考古學家對電影議題的淺嘗或“偏航”相比——比如齊林斯基謂之“間奏” (intermezzo),烏里吉奧(William Uricchio)的“彎路”(detour),以及馬諾維奇(Lev Manovich)理解的繪畫側線——新電影史始終將電影置于其系列關注的中心地位。這種關注意味著對電影史的本質、范圍、目的、材料和方法進行全面而連貫的重新檢驗(艾爾薩埃瑟 104):通過廣泛地引入眾多參數(shù)——既包括形塑我們今日謂之電影的種種元素,還涉及電影與其他媒介—技術現(xiàn)象、與其社會文化語境、與其背后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之間千絲萬縷的歷時和共時聯(lián)系——還原電影誕生與發(fā)展的多媒介環(huán)境,搜尋電影史的另類線索。埃爾塞瑟將新電影史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帶入《電影史》一書,按他本人的表述,“作為媒介考古學的電影史”這一計劃旨在將電影史從重新定位線性年表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后者基于嚴格的二元論如早期電影與古典電影、景觀與敘事、線性敘事與互動性。相反,電影史需要承認其獨特的地位,并且成為一種從各自的現(xiàn)在通往不同過去的追溯性路徑和軌道,它能適應連續(xù)性也能適應斷裂的模式。我們應如此描繪媒介融合和自我分化——不是從目的論或追根溯源方面出發(fā),而是從各種可能分叉路徑的形式出發(fā),即從作為確定的多元化和永久的虛擬化出發(fā)。(35)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埃爾塞瑟對各種媒介—技術之間關系的重新評估、對電影發(fā)展軌跡的重新測繪、對電影文化地位的重新界定,除了源于新電影史的方向,還始自他“追溯數(shù)字電影”的初志。數(shù)碼轉型對于視聽媒介的通約,使其以各種方式與電影裝置相互交叉關聯(lián),引致當代泛影像化的文化景觀,亦需擴寬電影的歷史語境和傳統(tǒng)敘述以獲取關于數(shù)字斷裂(digital rupture)的有效闡釋。埃爾塞瑟在《電影史》中從多個層面描述了“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已經(jīng)因為它的無處不在而變得有所遁形”的視聽現(xiàn)狀(19),如在制作過程層面:“當我們今天談及電影時,我們說的是在電視、電子游戲、主題公園和 DVD 之后的電影”(234);如在意識形態(tài)功能層面:“電影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意即它無處不在,不僅填滿每塊可使用的屏幕,而且進入每個可通達的空間”(386),等等。因此,為了連接過去和現(xiàn)在甚至指向未來,埃爾塞瑟很少在《電影史》中留下迷影的懷舊痕跡,他“并不堅持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獨特性和作為一種媒介的特異性”,更關注“牢固嵌入其他媒介實踐、其他技術和其他社會用途的電影”(19)。這種對于新趨勢和新視角的開放態(tài)度,在《電影史》中一方面體現(xiàn)為媒介—技術的多樣態(tài),即將電影的攝制與放映裝置置于娛樂、科學、軍事等更為廣闊的媒介實踐范疇;另一方面體現(xiàn)為時間的綿延性,即將電影的存續(xù)向后回溯至“早期電影” (early cinema)階段,向前延伸至數(shù)字影像世界。依據(jù)技術與時間指引的方向,埃爾塞瑟將《電影史》分為六章:第一章“早期電影”、第二章“聲音的挑戰(zhàn)”(The Challenge of Sound)、第三章“互動考古學”(Archaeologies of Interactivity)、第四章“數(shù)字電影” (Digital Cinema)、第五章“電影的新譜系”(New Genealogies of Cinema)、第六章“作為癥候的媒介考古學”(Media Archaeology as Symptom)。每一章在各有側重的前提下,共同交疊出并響應著電影媒介考古學的三個重要場域:重新發(fā)現(xiàn)早期電影的傳統(tǒng)、規(guī)則與邏輯(第一、二章);評估數(shù)字媒介如何影響人們對于電影史的理解(第三至五章);探尋“過時的”運動影像進入裝置藝術的潛能(第六章)。在這三個彼此獨立又相互限制的視野中,埃爾塞瑟重新測定技術與藝術、聲音與影像、敘事與奇觀、觀眾與互動、能量與熵、記憶與檔案等理論概念在新舊媒介生態(tài)中的衍變,重新思考電影應被置于何處。
電影史的復數(shù)形式
確切說來,《電影史》一書錨定的不僅是電影的歷史(cinema and film history),更是歷史中的電影(cinema and film in history; Elsaesser, Film 20)。這里的電影意為廣義的運動影像,主要用以“修正”人們在傳統(tǒng)電影史觀中習焉不察的線性歷史設定—— 無論是“幼年—成熟—衰落—復興”的有機編年體模型,還是“愈加寫實”的目的論編年體模型,抑或是從幻覺 / 奇觀向邏輯敘事的發(fā)展模型(埃爾薩瑟 27)。無論何種形式,線性歷史已在媒介考古學視域下突顯其運作機制的重重問題。首先,線性發(fā)展通常是在后見之明中逆向書寫的過分平滑的因果鏈條,這一過程是對裂隙的縫合,即選擇特定事件連接變化以使它們成為朝向某一共同目的的序列,在傳統(tǒng)電影史中要么是聲音、色彩、寬銀幕或立體聲的技術變革,要么是頒布《派拉蒙法案》或廢除《海斯法典》之類的經(jīng)濟文化動機(埃爾薩瑟 30);同時,這一過程又是對差異的剪除,那些與因果鏈條相沖突的內容為歷史所流放。因而當某種媒介內容跨越時期、跨越形式復現(xiàn)時,或某些遺產(chǎn)碎片與主流敘述發(fā)生重疊或沖突時,這個看似自洽的秩序便顯得力不勝任了。其次,線性發(fā)展在以數(shù)碼轉型為代表的斷裂中更加無以為繼。一方面,傳統(tǒng)電影史前史(通常指光學史、攝影史、投影史和視覺暫留)的溯源與匯流已被大量經(jīng)數(shù)字媒介通約、增殖和更迭的視聽裝置打斷,若堅持將某個源頭定于唯一,“電影之死” 便是這個時代的必然;另一方面,“考慮到現(xiàn)在通過……(數(shù)字)設備收集到的關于世界的數(shù)據(jù)總量有著爆炸性的成長,這當然挑戰(zhàn)了古典因果關系作為組織原則的充分性和適用性。……計算機作為組織機器……似乎比人類更有能力應對海量數(shù)據(jù)信息的偶然性和隨機存取、相關性和模式識別”(Elsaesser, Film 364)。換言之,數(shù)字技術拒絕將自身及其介入的電影追加到單一的線性歷史中。鑒于因果程式或進化解釋的失效,埃爾塞瑟為電影史構想了一個“零度”空間,其中既不劃分外部與內部,也不固定此前和此后,因而就不存在任何對開端和起源的假設。在這個允許不同空間共存以及時間范圍重疊的地方,埃爾塞瑟主張借助一種“回溯—前瞻”(analeptic-proleptic)的考古學觀念對待電影史:不去證明過去如何能動地、持續(xù)地推入現(xiàn)在,而從現(xiàn)下特殊或緊迫的問題發(fā)掘過去,“回溯性地為過去之物賦予一種對當下的遠見,這些過去之物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突然地來到現(xiàn)在與我們對話”(埃爾塞瑟、李洋 114)。這要求媒介考古學家或電影史學家盡可能將該領域把握為一張巨網(wǎng),以便發(fā)現(xiàn)離散的歷史碎片之間的關聯(lián),以及它們被回收和挪用的多樣可能。或許這樣會相對減輕電影研究在當代常因起源和目的之爭而被攻擊的脆弱性。
依照上述非線性發(fā)展的電影史學模型,埃爾塞瑟溯至早期電影檢視了電影裝置的非娛樂用途,總結了電影曾經(jīng)作為“S/M 機器”的諸種實踐:科學與醫(yī)學成像裝置、監(jiān)控與軍事裝置、感覺—運動—模式(sensory-motor-schema)以及傳感與監(jiān)測(sensoring and monitoring)裝置(Film 121)。這些發(fā)現(xiàn)形構出電影原本包羅萬象或曰旁逸橫出的媒介環(huán)境、特別是其作為統(tǒng)治與規(guī)訓工具的歷史,正如埃爾塞瑟那句常被引證的“名言”所說:“電影(cinema)有許多歷史,屬于影片(movie)的卻不多”(Harun 17)。對于 S/M 實踐的造訪,迫使人們超越電影今日之娛樂—藝術的定位,去思考電影作為一種媒介—技術的存在。由此帶出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埃爾塞瑟對于電影作為一種敘事媒介的重估。事實上,若干電影研究學者都曾介入這一討論,比如庫比特(Sean Cubitt)希望人們認識到“敘事對于電影而言,既非首要亦非必要,它并不是媒介的任何假定本質的構成部分”(38);再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指出,“電影 [是] 被構成如今的模樣,成為敘事的,講述一個故事并排斥其他可能的方向”(38)。在新電影史看來,將事件按照建置、對抗和結局進行排列的敘事,尤以經(jīng)典敘事為主,在漫長的運動影像歷史中只占據(jù)了 1917 年到 1977 年這段時間。埃爾塞瑟透過拉賓巴赫(Anson Rabinbach)的“人形發(fā)動機”(human motor)概念指出,工業(yè)社會提升效率的核心在于對抗疲勞,電影因此成為負載能量轉換功能的勞動力再生產(chǎn)形式。有趣的是,電影的技術淵源(連續(xù)攝影)和社會用途在對時間的利用上格外不同:前者是維系生產(chǎn)的計量時間的工具,后者是克服疲勞的浪費時間的娛樂。對埃爾塞瑟而言,電影的藝術用途如講述故事、提供觀點則是調和上述張力的一種方案:“這些俗稱‘娛樂’ 的形式實則是一套極為復雜的實踐和流程,它們模仿(和復刻)工作生涯的方方面面,同時補償職業(yè)生活的”壓力(Film 319-23)。因而敘事成為一種與 20 世紀前半葉的電影相匹配的選擇。電影中觀眾熟悉的場景——現(xiàn)代生活日益增長的速度、效率和重復,以及結構這些場景的時間順序、邏輯關系,既是一種模仿,又是一種撫慰。尤其是經(jīng)典敘事,它對成規(guī)慣例的遵守使其成為一種符合人體“工效學”(ergonomics)的敘述方式:相對確定的情節(jié)點設置可以針對或將產(chǎn)生的認知、情感或官能刺激進行有效的預判和處理,從而減輕觀眾其他不可避免的感官過載,以此達到緩和放松的功能和目的。
隨著上世紀 60 年代末大敘事的崩潰,永無止盡的進步變成對空言說,因果環(huán)扣的歷史陷入終結危機。對電影而言,這些問題反映在敘事的轉折之上,首先是電影文本敘事的變化:伴隨數(shù)字信息的涌入,敘事開始在非線性與無序性的“混亂”中為觀眾制造涉及互文性與媒介間性的觀影感受,以因應新時代對于生成勝過存在、混雜性勝過特異性、聯(lián)通的節(jié)點網(wǎng)勝過垂直因果性和線性編年史的偏愛(Elsaesser, Film 43)。其次是電影自身敘事意識形態(tài)的動搖:媒介考古學家拒絕歸因與分期、追封與認定,而是在“大材小用、有意誤用、無奈棄用”的媒介實踐中不斷尋找電影的異質性歷史,嘗試還原電影的可能條件,界定電影的本體問題,并在此基礎上考慮它們可能會對歷史起到的注解作用和對現(xiàn)實的參考意義。
數(shù)字電影的舊錦新樣
盡管電影從外部看來仍舊保有其所以稱作“電影的”(cinematic)全部元素,但是計算機已然接管了從生產(chǎn)到傳播再到接受的全部環(huán)節(jié)。借用基特勒的表述,“一個完整的數(shù)字媒體鏈條將抹去媒介的概念”(2),這對電影而言意味著數(shù)碼轉型正在使其百年來的自足本性逐步失守。電影不再容易界定的事實再度引發(fā)關于電影終結的討論,事實上它已屢次被報死亡:每當技術或設備的更迭造成電影攝制過程或接受語境的改變時,“電影之死”的話題就會席卷而來,比如上世紀 20 年代末有聲片的興起, 50 年代初家庭廣播電視網(wǎng)的建立,自 70 年代起相繼出現(xiàn)的錄像帶、DVD、藍光原盤等。就此而言,電影的終結儼然成為一個“國王已死,國王萬歲!”的命題。然而,發(fā)軔于 90 年代的數(shù)字媒介卻仿佛是個例外,盡管它與模擬媒介的邏輯迥異,但吊詭的是,數(shù)字媒介卻史無前例地未經(jīng)討論、未被抵抗,就在世界范圍內急遽進入社會生活中,也似乎是第一次真正讓電影有了終結的惶恐。簡言之,模擬媒介采用機械邏輯,經(jīng)傳感器將不同物理形式的能量轉換為相應信號;而數(shù)字媒介采用符號邏輯,統(tǒng)一由二進制進行編碼和解碼。這一斷裂成為埃爾塞瑟及其《電影史》展開思考的巨大前提: “即使無法彌合這道裂痕,是否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它所發(fā)生的原因和方式?”該書并非旨在探究模擬與數(shù)字之間的分歧,它對技術維度的回避,典型呈現(xiàn)出人文話語在面對數(shù)碼轉型時那種難以應對的言說無力和格局窄小,易被指摘為能指游戲或虛假論述;相對地,它試圖聚焦“數(shù)字影像在模仿、增強和挪用攝影影像為其界面和‘特效’方面的成功(與繼承)”,意在更悠長的影像歷史和更廣泛的影像用途中重新定位電影的發(fā)展(370-71)。沿著“回溯—前瞻”的思路,埃爾塞瑟關于數(shù)字電影的討論以新的方式開啟了對于早期電影的認識,反過來又為探求電影由符號邏輯延續(xù)的“虛擬”生命注入了新的動力。
在這一反目的論的回溯軌跡中,埃爾塞瑟將兩個“在媒介技術和社會發(fā)展廣譜中發(fā)生突變”的、相隔百年的時期(1870—1900 年和 1970—2000 年)關聯(lián)起來(Film 101),征引若干概念和現(xiàn)象,用以說明數(shù)字技術其實并未造成電影的根本性斷裂 / 突破(break)。其一是岡寧的“吸引力電影”(cinema of attractions)與當代電影奇觀特效的一致性。吸引力電影強調電影對于視覺快感的原初關切和高度自覺,通過影像本身而非敘事,喚起觀眾的好奇心與注意力。在早期電影學者看來,數(shù)字時代的電影風格(尤以好萊塢大片為主)大都也是視覺奇觀壓倒敘事機巧,行動導向勝過懸念迭生。埃爾塞瑟在該書中將二者并行處理:“瘋狂追逐或圖形幽默(graphic humour)之于早期電影類型,就像‘過山車式’(roller coaster rides)、恐怖片、肢解(slasher)、血漿(splatter)或功夫片段之于當代電影”(78)。經(jīng)由巨幕和杜比系統(tǒng)外化的數(shù)碼奇觀制造了更為切近、更大限度的感官沖擊,其震驚效果對敘述流的中斷與早期電影的非敘事性不謀而合。這一周期性復蘇與新電影史中打斷線性和融合的論述相吻合,而更具顛覆性的是,埃爾塞瑟及其他早期電影學者指出,早期電影和數(shù)字電影因“吸引力”而成為兩個平行、接合的階段,導致身居其間的好萊塢經(jīng)典敘事電影更像一個例外、一段插曲。
其二是鮑特(Edwin S. Porter)的“鄉(xiāng)下人電影”(the Rube films)系列與當代電影交互邏輯的親緣性。對于數(shù)字電影蘊含的可操作形式,埃爾塞瑟摒棄了諸如鏡像、間離、雙重性等現(xiàn)代主義闡釋方式,轉而回到早期電影中零星出現(xiàn)但極為古老的“鄉(xiāng)下人魯比”形象。作為最早的自反電影之一,該系列通常以“影中影”結構展示一個不知道電影應當被“看”的鄉(xiāng)巴佬,因而總是試圖觸摸、融入銀幕上的影像,或尋找銀幕后的成像機制。對埃爾塞瑟而言,“鄉(xiāng)下人魯比”是在數(shù)字時代理解觀看行為(spectatorship)和交互敘事的重要載體(208),他介入銀幕的行為破壞了影像空間和觀影空間的絕對二分,不僅有助于理解電影從敘事向互動或其他形式過渡時發(fā)生的邏輯轉變,甚至可以打破電影研究與游戲研究之間潛在的不兼容性。
其三是 3D 的回返。3D 作為一種“吸引力”并非數(shù)碼轉型的產(chǎn)物。上一次 3D 的出現(xiàn),是 20 世紀 50 年代好萊塢針對電視普及之沖擊的倉惶回應,同時伴隨寬銀幕、史詩片對于觀眾的爭奪。然而 3D 的前身立體電影,可追溯至 19 世紀 30 年代末,以及緊隨其后的魔術幻燈、西洋鏡、環(huán)景影像(panorama)等立體視覺技藝。埃爾塞瑟認為, 3D 與數(shù)字技術的結合打造了一個“后歐幾里德”空間,“數(shù)字影像的延展性、伸縮性、流動性或‘曲率’被引入視聽空間”;但是,變得靈活而柔韌的立體視像并不代表“真實”之維的進入,它的回返其實是意欲成為數(shù)字影像的一個全新參數(shù),重置人們對于影像概念的理解(290-92)。換言之,此輪 3D 的復現(xiàn)并非意在特效,它的視野比影院更加開闊,旨在逐漸成為人類視覺的新單位和默認值。
其四是克拉里(Jonathan Crary)復興的生理光學對當代電影觸感視覺的先導性。 19 世紀生理光學與幾何光學共存的事實動搖了沿視錐形成的單眼透視法,前者與電磁學的融匯,或可構成理解數(shù)字影像(研究)轉向肉身思考觀看行為的第一步。當下對沉浸、情動、互動、觸覺等身心體驗的強調,以及對反復觀影的需要,都在表明電影與多維感官的聯(lián)系,這在埃爾塞瑟看來無不可回溯至早期生理光學玩具對身體感知的召喚;而當整個身體全部參與成為感知表面時,它或許預示著某種視覺跡象——“一種不同的知識型或將在整個文化中得以確立”(379-83)。
斯康斯(Jeffery Sconce)說過,“伴隨著新媒介的出現(xiàn),相似的故事披著新的外衣再次登場”(轉引自胡塔莫等 9),這也是我們可以在埃爾塞瑟建構的論域中有所發(fā)現(xiàn)的:若干早期電影的媒介實踐在被回收、挪用或改裝之后,出乎意料地存活下來,并在數(shù)字時代延續(xù)著它們的第二生命;也正因如此,數(shù)字制造仍能在電影史學和電影研究中保有位置。當然,埃爾塞瑟并無意復辟早期電影,其宗旨也不是驅逐經(jīng)典敘事;事實上,大量與電影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媒介—技術包括廣播電視、錄像機、DVD、遙控器、隨身聽、視窗等,仍待考察,亟需借助媒介考古學修正單一的因果線索,解構注定的歷史敘述。埃爾塞瑟相信,媒介考古學因為“既來自于它的時代、又服務于它的時代” 而成為歷史研究的最優(yōu)選擇;在他指出數(shù)碼轉型是媒介考古取向的決定性因素之外(383),還需注意的是,這一方法和實踐本身也與這個時代的數(shù)據(jù)庫邏輯相符:大量媒介—技術共同組成了無差別的結構化集合,方便隨時調用和比對。在此基礎上,媒介考古學除卻探索新與舊的平行軌跡和延續(xù)關系,也應重訪業(yè)已傾覆的夢想,適時打碎新興媒介—技術允諾的似曾相識的烏托邦,這同樣也是考古的意義所在。
自電影被迫從其媒介特異性與自足性中“解放”出來起,它就在頑抗因邊界被僭越而日益被削弱的危機。埃爾塞瑟在《電影史》中稱此情景為“過時”(obsolescence),他對電影過時之政治與詩學的討論被費爾法克斯(Daniel Fairfax)、薩瑟蘭(Thomas Sutherland)等多位學者譽為全書的精華所在。埃爾塞瑟所謂的過時并非針對資本主義工業(yè)化或消費主義的批評語匯,而是尼采意義上的“不合時宜”(untimeliness)。他援引阿甘本解釋道,“當某物失去效用時,它就成了真正當前的和緊迫的,因為只有這時,它才會展現(xiàn)自身所有的豐富和真理”(67)。因此,當電影已經(jīng)“不再是我們當下商業(yè)優(yōu)先選項、政治意識形態(tài)或技術烏托邦的載體”時(66),當賽璐珞、膠卷盒、剪輯臺、放映機連同它們一起再現(xiàn)的影像一并走進博物館、美術館和資料館的“白色立方體” 時,它們對埃爾塞瑟而言卻滿載積極意義:一方面,面對總是超越我們理解、逃避我們控制的數(shù)字進程,過時之物提示著模擬甚至更早時代的存在,它們既因消逝的悲情展示出“對不斷的加速、對新事物的暴政的英雄式反抗”(埃爾塞瑟、李洋 112),也因殘留的遺跡、未竟的事業(yè)而提供了通達數(shù)碼物的參照;另一方面,只有過時之物才能釋出不近功利的解放性潛能,以便重新搜尋遺失的靈暈,為電影作為一門藝術、一種審美的歷史提供依據(jù)。
“視舊如新”的方法困局
由于《電影史》一書匯集的是埃爾塞瑟二十余年的思考,其中不乏主題和觀點的重復,亦有學者對其提出諸如“零散”(Fidotta 123)、“調性參差”(Fairfax)、缺乏連貫性和系統(tǒng)性等批評(Sutherland 552-53)。費爾法克斯將《電影史》形容為“對稱的折疊結構”,意即首尾兩章以較長篇幅細察了媒介考古學的一般問題,主體部分則以案例研究聚焦更為具體的影史、影片、影人。盡管中間各個章節(jié)都引人入勝、論述充分,但讀者卻容易因線索不清而迷失方向。事實上,這些問題的根源已由埃爾塞瑟本人一語道破,在于媒介考古學“沒有明確的方法和共同的目標”(352)。他拒絕胡塔莫等人以完全去學科化的姿態(tài)為媒介考古學進行的辯護,即認為媒介考古學的“優(yōu)勢和價值正在于異質而多樣的研究、解構而反常態(tài)的方法、顛覆與抵抗的目標,媒介考古學是一門沒有固定邊界的游動學科”(qtd. in Film 352);“一大批思想已為媒介考古學提供了靈感。文化唯物主義、話語分析、非線性時間概念、性別理論、后殖民研究、視覺和媒介人類學以及新游牧主義哲學等多樣化的理論均屬這一混合體”(胡塔莫等 2)。埃爾塞瑟認為這種姿態(tài)潛藏包羅萬象的危險。他也拒絕簡單地鉤沉事實來填補歷史切面,因為斷裂本身可能富含新意。為了化解這樣那樣的方法質疑,埃爾塞瑟在該書中策略性地將媒介考古學轉化為一個更具元話語性質的表述:
我不太關心“何為媒介考古學”的定義,而是問自己“為什么(現(xiàn)在)需要媒介考古學”:……我傾向于將媒介考古學當作一種癥候而不是一種方法、一個預留位置而不是一個研究方案、一種對于多方危機的回應而不是一門突破性的創(chuàng)新學科。我問自己,媒介考古學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思想意識(ideology),而不是一種新型可靠知識的生產(chǎn)方式。(354)
沿著上述方向,埃爾塞瑟在《電影史》中以坦率的包容和清晰的邏輯分析了被他并置的諸論點及其反論點,整個過程在費爾法克斯看來相當辯證,但也極為搖擺。他認為這種不確定性源于新自由資本主義、后現(xiàn)代方法論框架和數(shù)碼轉型的合謀,導致“話語不再以任何對于真實性的潛在要求為基礎”,這在一定程度上質疑了媒介考古學的有效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媒介考古學脫胎于上述三個彼此嵌套、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場域,打開話語邊界、拒斥固定闡釋、進行癥候閱讀才是題中應有之義。或許媒介考古學作為一種方法或路徑的意涵尚不清晰,但是試圖回返因果性、總體性、特異性和目的論的做法注定無功而返。
方法的難以統(tǒng)合是媒介考古學最為棘手的問題。此外,《電影史》視域下的媒介考古學仍有如下幾處有待商榷。其一,媒介考古學是否在解構主流媒介史的過程中存有建制另類媒介神話的欲望?新電影史對早期電影的再發(fā)現(xiàn)似乎預設了兩件事情:一邊是拆解電影史學的傳統(tǒng)模型,其對電影成熟期之特權的顛覆具有內在反抗性;一邊卻是將早期電影“視為一種可能的模板”(埃爾薩瑟 29),其對早期電影與數(shù)字影像平行軌跡的認證又充滿建構性。“在否棄歷史目的論的努力中,一種新目的論不是正在悄悄取代它嗎?”(Fairfax)其二,媒介考古學對于物質性的強調能否真正觸及數(shù)字媒介的運作機制?數(shù)字媒介以符號邏輯結構于黑箱當中,若僅考察硬件設備的物性與存在狀態(tài),將使人文話語難以從軟件程序層面對當代虛擬文化進行具體而準確的描述;整合馬諾維奇在《軟件掌控一切》(Software Takes Command)中的發(fā)現(xiàn)或可構成一種新視角。其三是媒介考古學在政治維度上的擱淺。《電影史》關于工業(yè)化、商品化、認識論、過時等議題的見解已經(jīng)覆蓋電影研究或媒介研究的普通訴求,但是埃爾塞瑟對其潛在政治面向的論述卻略低于預期(Fidotta 123),這在某種意義上映射出媒介考古學因反對大敘事而導致的“自我窄化”傾向(施暢 52)。對于任何主流或另類媒介的剖釋,都應納入媒介—技術實踐與更廣泛的社會政治變革之間的結構性關聯(lián)。
2019 年末埃爾塞瑟去世,令整個電影研究領域深感惋惜,《電影史》一書也許是他的“絕筆”之作。埃爾塞瑟的學術遺產(chǎn)不能被低估,他對新電影史和媒介考古學的卓著貢獻在不斷膨大的電影與媒介研究中尤其令人欽佩。在數(shù)字時代對新裝置、新技藝亦步亦趨時,在瞬時、虛擬、互動的眾聲喧嘩中,埃爾塞瑟及其《電影史》有力地將歷史的維度再次引入,重建人們把握媒介史和電影史的時空坐標。同時,他從電影學進入當代媒介實踐的路徑,賦予電影此前在媒介考古學序列中鮮受認同的突出地位,使其成為“數(shù)字文化的內部參照點”(Elsaesser, Film 264)。埃爾塞瑟借其《電影史》再次中斷了“電影之死”的預言;相反,電影的邊界被打開了。當我們愈多發(fā)現(xiàn)電影與其他視聽媒介的相似性和兼容性時,就會愈加認知電影百余年來永恒的變動和生成,也會愈發(fā)理解巴贊(André Bazin)的預言:“一切使電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無非是使電影接近它的起源。電影確實還沒有發(fā)明出來呢!”(19)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