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xué)是語(yǔ)言的藝術(shù),民間文學(xué)是口頭語(yǔ)言的藝術(shù)。不同地方的民間文學(xué),是用不同方言傳播的口頭語(yǔ)言藝術(shù)。大量接觸民間文學(xué)的人們都知道:無論口頭講述的民間故事,還是口頭演唱的民間歌謠,其語(yǔ)言通常不會(huì)顯得文縐縐,而是通俗活潑,使用大量的方言字詞和俗語(yǔ)、諺語(yǔ);通篇語(yǔ)言貼近生活,具有很強(qiáng)的生活氣息,散發(fā)著泥土的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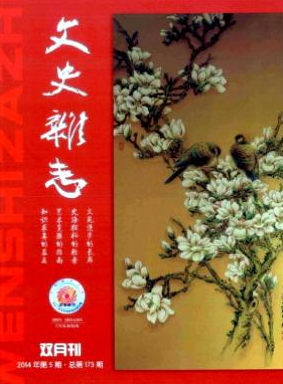
本文源自文史雜志 2021年1期《文史雜志》(雙月刊)創(chuàng)刊于1985年,是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館;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主辦的文史刊物。《文史雜志》積極評(píng)介中華民族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以及優(yōu)秀文化遺產(chǎn);向群眾進(jìn)行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普及宣傳,進(jìn)行社會(huì)主義與愛國(guó)主義的啟發(fā)教育,包含文學(xué),歷史,藝術(shù)三個(gè)范疇。
用地道的四川方言記錄的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一方面是四川民間文學(xué)地方特色的重要體現(xiàn),另一方面也積淀了豐厚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包含著歷史的、民族的、思想的、科學(xué)的、宗教的、民俗的等方面豐富多彩的信息。
面對(duì)著地方特色十分明顯的四川方言,外地人看不懂怎么辦?我們要做的一項(xiàng)重要工作,就是為方言做好必要的注釋。如此,既可以讓具有不同方言背景或基礎(chǔ)的人讀懂,又不減損民間文學(xué)的文化內(nèi)涵和地方風(fēng)味。
一、民間文學(xué)是四川方言匯集的海洋
讓我們先來面對(duì)這樣一個(gè)現(xiàn)實(shí)情況:由于普通話的全面推廣,四川方言總體呈現(xiàn)出向普通話靠攏的趨勢(shì)。首先表現(xiàn)為,青少年一代,已有不少人部分或全部使用普通話;其次表現(xiàn)為,城市人口中,已有一些人部分或全部使用普通話;再次表現(xiàn)為,前面提到的這兩類人即便說四川話時(shí),所使用的方言與傳統(tǒng)的四川方言也已明顯發(fā)生變異。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舍棄了方言中過于生僻、土俗的字詞和語(yǔ)言,并將部分方音較重的字,改用與普通話接近的讀音來說或讀。
比如,傳統(tǒng)四川方言中用“?”作聲母的那些字,不少的年輕人和城里人都舍棄了原有讀音,像“我”不讀“?o”而讀“wo”,“愛”不讀“?ai”而讀“ai”,“安”不讀“?an”而讀“an”,“歐”不讀“?ou”而讀“ou”。
再如,將四川方言中用聲母“j、q、x”與韻母“u”(烏)拼成的字,全部讀成與韻母“ü”(魚)拼成的音,如“局長(zhǎng)”“菊花”“歌曲”“冤屈”“繼續(xù)”“旭日”等,都讀“魚”韻。
除此之外,傳統(tǒng)四川方言中類似將“六”讀成“lu”、“俗”讀成“xu”(烏韻),將“藏”(cang)讀成qiang”,將“足”讀成“ju”(烏韻),將“攔”讀成“luán”等例子很多。而年輕一代和不少的城里人,基本都舍棄了原有讀音,改讀(說)普通話的聲韻。
可以想象,隨著時(shí)代的不斷向前發(fā)展,隨著人口的一代代更迭,今后的四川人口中和筆下的四川方言將越來越少。
方言的根基在鄉(xiāng)村里巷,民間文學(xué)的根基也在鄉(xiāng)村里巷。采錄自鄉(xiāng)村里巷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成為四川方言匯集的海洋;尤其是過去采錄的作品——過去采錄自上了年齡的講唱者的作品。通過廣泛閱讀四川各地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采錄時(shí)間越早的作品,方言保留越多一些,反之則少一些;采錄自農(nóng)村的作品,比采錄自城區(qū)的作品,方言保留更多一些;年齡大的講唱者講唱的作品,比年齡小的講唱者講唱的作品,方言保留更多一些。
比較可惜的是: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中記錄下來的方言讀音比較少。比較幸運(yùn)的是:四川方言字詞及話語(yǔ)在民間文學(xué)作品中得到了較好的保存。
盡管四川各地方言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甚至較大差異,但整個(gè)四川方言內(nèi)部還是有著較大的一致性。因此,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所使用的方言,大體展現(xiàn)了整個(gè)四川方言的基本面貌和特征,體現(xiàn)出四川方言豐富多彩和生動(dòng)形象的特點(diǎn)。
單就表示身體動(dòng)作方面,就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鏟:用手拍打、抽打,或被風(fēng)吹打。如“鏟你兩耳矢”;民歌中有“楊柳就怕風(fēng)來鏟,情哥就怕病來纏。”
搒:讀pǎng,碰的意思。如“你不要搒我嘛。”
抽:推的意思。如“快點(diǎn)抽倒起,要倒了。”
揍:塞、堵塞的意思。如“趕快揍起,要冒出來了。”
扚:讀diā,用手提的意思。如“輕輕就把它扚起來了。”
奓:讀zā,張開的意思。一般用在嘴巴和雙腿上。
?:讀wèng,掩埋、蓋住的意思。
憑:讀pēn,憑靠、靠著的意思。如俗語(yǔ)“坐在門口等天黑,憑在床頭等天亮。”
?:扛的意思,主要指單肩扛。有一篇故事就叫《?起半截就開跑》。
跍:讀gū,蹲的意思。德昌縣故事《傻男人和馬鹿》里,有“男人還跍在地上站不起來。”
迢:讀tiáo,跑的意思。川東地區(qū)有這樣的民歌:“迢起來像鳳擺尾,一對(duì)眼睛像燈籠。”
撻:摔打、抽打的意思。如“撻谷子”(使稻谷脫粒的摔打動(dòng)作)。
跶:摔跤、摔跟斗的意思。如“不小心跶他媽一撲爬。”
抓:讀zuá,用腳踢的意思。如“抓他兩腳。”
如此等等。再看表示身體部位的方言,也非常多:
克膝頭兒:指膝蓋。膝,讀xī。
連二桿:指小腿。
溝子:指屁股。
胩腳:指兩腿之間的部位。胩,讀kà。在達(dá)州民間的一個(gè)叫《看你咋個(gè)把書教》的故事里,挑水的婦女還擊占自己便宜的教書先生時(shí),這樣說:“先生不矮也不高,胩腳鼓起兩個(gè)包;要是長(zhǎng)在嘴巴上,看你咋個(gè)把書教。”
二、民間文學(xué)中的四川方言,
包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
四川地區(qū)在歷史上是一個(gè)五方移民不斷交融發(fā)展的地方,形成了豐富復(fù)雜的四川方言。除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四川話以外,還有土廣東話(屬客家話)、老湖廣話(屬湘語(yǔ))等。與此同時(shí),部分藏、彝、羌等民族地區(qū),還使用著與四川話口音接近的、帶著濃厚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方言。
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中使用了大量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的方言俗語(yǔ),使其散發(fā)著濃郁的泥土氣息。這些方言包含著豐厚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展示了四川人民豐富多彩的社會(huì)生活和民俗風(fēng)情。
山歌好唱口難開,櫻桃好吃樹難栽。
白米好吃田難種,鮮魚好吃網(wǎng)難牽。
這是一首在四川各地廣為流傳的山歌,有的版本第二句唱“林檎好吃樹難栽”。單以歌中的“吃”字,在四川不同地方的方言中有不同的讀音,從中透露出諸多的歷史文化信息。在原川東的合川、江北、鄰水、長(zhǎng)壽等地,歌中的“吃”被唱作“嘁”(讀qī);而在川中內(nèi)江、資中等地,“吃”又常被唱作“掐”(讀qiā)。二者皆是“吃”的意思。據(jù)有關(guān)專家研究表明:“嘁”和“掐”原本是兩湖語(yǔ)言,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幾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過程中,被帶進(jìn)了四川,并在一些地方保留到今天。如今,湖北人依然將“吃”說成“嘁”,湖南人則將“吃”說成“掐”。
再看四川人過去愛說的“帽兒頭”,在民間文學(xué)作品中常有出現(xiàn),其中也包含著諸多的社會(huì)信息。帽兒頭指的是裝得很滿的大碗白米飯,就像帽子的頂一樣。著名作家李劼人先生在其小說《大波》第二部第七章里寫道:“隊(duì)長(zhǎng)請(qǐng)我們到飯館子里,每人消繳他三個(gè)帽兒頭,外搭咸菜二碟,那才安逸哩!”“消繳”,是消受、吃掉的意思;帽兒頭,該書原注是這樣解釋的:“ 四川飯館里的專門名詞。一個(gè)帽兒頭即是一大碗盛得堆尖尖的白米飯。大約一個(gè)帽兒頭,可抵兩平碗之量。”
為什么過去盛飯要裝壘尖尖的帽兒頭,而現(xiàn)在一般都不會(huì)裝得很滿呢?這是因?yàn)椋凇洞蟛ā匪f的時(shí)代,下層人民食不果腹,能夠吃上兩碗白米飯?jiān)偌由宵c(diǎn)咸菜,就算讓口腹之欲得到大大的滿足了。請(qǐng)看李劼人先生寫隊(duì)長(zhǎng)請(qǐng)吃飯都吃的什么吧:“每人消繳他三個(gè)帽兒頭,外搭咸菜二碟。”接著說“那才安逸哩!”所以,在那個(gè)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無論到親友家作客,還是到飯館吃飯,人們都很在意端到自己面前的“帽兒頭”是不是“壘尖尖”的,壓得實(shí)不實(shí)。從某種角度講,這都是長(zhǎng)期被餓怕了的正常心理反映。
采錄自成都市原西城區(qū)的《秀才吃帽兒頭》,講的便是到皇城壩趕考的窮秀才們,因吃不起考場(chǎng)伙食而到皇城外的餐館吃“帽兒頭”。餐館老板看到來的秀才多,就打起了壞主意,將米飯?zhí)舳兜煤苌ⅲ粋€(gè)帽兒頭的飯用筷子一壓就只有一平碗了。于是引起了糾紛,最后主考大人出面才解決了問題。
我們?cè)賮砜?ldquo;啃兔腦殼”這個(gè)方言詞組,其包含著豐富的飲食文化和民俗文化信息。四川人愛吃兔子,麻辣兔腦殼是成都等地人們特別喜愛的一道美食。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很享受“啃兔腦殼”的愉快過程。當(dāng)然,“啃兔腦殼”還是一句雙關(guān)語(yǔ),一句只有四川人才懂得起的方言,即指接吻之事。
我們?cè)倏闯啥嫉鹊亓鱾鞯膬焊琛而f雀窩》:
鴉鵲窩,板板梭;
陶二姐,做饃饃。
客來了,倒鍋;
客走了,揭開鍋。
“?”:讀kàng,動(dòng)詞,“蓋”的意思,將鍋蓋或其他東西蓋下去的動(dòng)作就叫“?”。兒歌原本是嘲諷陶二姐吝嗇摳門的,其實(shí)何嘗不是那個(gè)缺吃少穿年代許多人的一種本能反應(yīng)呢!換作今天,誰(shuí)還會(huì)吝惜兩個(gè)饃饃呢?
三、正確注釋好四川方言,
是欣賞和傳承民間文學(xué)的重要基礎(chǔ)
采錄自各個(gè)方言區(qū)或方言島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里面攜帶著許許多多的方言詞匯或語(yǔ)句。不過,如果聽不懂方言,看不懂方言,那么,對(duì)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解讀、對(duì)作品魅力的體驗(yàn),便會(huì)大打折扣;更不用說對(duì)民間文學(xué)的采錄了。清人黃遵憲在《山歌題記》中說:“然山歌每方言設(shè)喻,或以作韻,茍不諳土俗,即不知其妙。”
舉一首川南民歌《情哥約我去賞月》為例:
初二晚上黑又黑,情哥約我去賞月。
媽媽叫我打火把,我說沒得烏梢蛇。
媽的心腸雖然好,兒女心事不明白。
歌詞不但情真意切,畫面感強(qiáng),而且用四川話讀起來非常押韻,朗朗上口。相反,如果不懂四川方言,用普通話去讀,就完全不押韻了,美感頓失。
所以,為方言注音注義,是采錄、整理和編纂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重要工作。
通觀四川各地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里面諸多的方言,有的已經(jīng)做了注釋但欠完整或欠準(zhǔn)確,有的還沒有做出注釋。為這些方言補(bǔ)充并完善注釋,是更好地保存、欣賞和傳承民間文學(xué)的題中之義。我們編纂的《民間文學(xué)大系·四川卷》便對(duì)這些方言做了上述工作,例如——
果子泡:指皮膚上磨出的大泡。果子,形容個(gè)頭大。
遇緣:碰巧的意思。
倒還:倒過來、反過來的意思。
生起:發(fā)生、出現(xiàn)的意思。
架勢(shì):使勁的意思。
風(fēng)風(fēng):消息、信息的意思。
一么多:很多的意思。
爭(zhēng)賬:差賬、欠賬的意思。
莽起:用力、使勁的意思。
將將好:剛剛好的意思。
煞閣:結(jié)束的意思。
擔(dān)怕:恐怕的意思。
一火鐮:一家伙、一下子的意思。
投:折算為、相當(dāng)于的意思。如“做一天投多少錢呢?”
起坎:找到了著落的意思。
磨肇人:折磨人的意思。
傳昂了:昂,讀āng,人人都在傳說、傳得人盡皆知的意思。
遭了:被人算計(jì)了的意思。
使勁板:板,動(dòng)詞,扭動(dòng)的意思。
行實(shí):行,讀háng,得行、能干的意思。川東地區(qū)有“生蛋母雞臉蛋紅,行時(shí)婆娘大不同”的民歌。
估諳:估計(jì)、猜測(cè)的意思。
陰倒:暗地里、私底下的意思。
迤頭:里頭的意思。
果子麻搭:不清不楚的意思。
黢黑:又說成黢媽黑,很黑、非常黑的意思。黢,讀qū。
背時(shí)倒灶:指人走背運(yùn),連灶臺(tái)都倒了。民以食為天,灶臺(tái)倒了,意味著沒有吃的了,真可謂倒霉透頂了。
起窖窖:很多的意思。窖窖:前一個(gè)窖,讀gào;后一個(gè)窖,讀gāo。四川吉利唱詞中有“金銀起窖窖”的句子。有人記錄為“告告”,這是錯(cuò)誤的,也無法正確解釋。
啷門:又記作啷么等,怎么的意思。川南民歌中有“千頭萬(wàn)緒心頭掛,拿來啷門改疙瘩。”改,同“解”,都讀gai,解開的意思。幽默智慧的四川人,還用這兩個(gè)字的同音關(guān)系,創(chuàng)造了歇后語(yǔ)“狗吃粽子——死不改(解)。”以狗喻人,嘲諷其不知道改習(xí)性。
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中,還有一些句末語(yǔ)氣詞使用非常頻繁,帶著濃郁的地方特色。比如“噻”“嗦”,都帶有感嘆加設(shè)問的多重語(yǔ)氣。舉例如“你罵了半天,罵夠了噻!?”“硬是懂不起嗦?”1992年,我從大竹縣坐長(zhǎng)途汽車回成都,剛上車就有一個(gè)男子將手伸進(jìn)我衣袋里到處摸。我問:“你做啥子?”他大聲武氣地說:“摸包,懂不起嗦!?”
下面,就四川民間文學(xué)作品里使用頻率特別高、知名度特別大的兩個(gè)方言字做一番特別說明。
首先是“”字,讀pā,形容詞,是“軟”“軟和”的意思,“硬”的反義詞。常用的組合詞匯有“和”“紅苕”“桃子”等等,最著名的組合是“耳朵”,指的是那些凡事都聽老婆的話、耳朵早已被老婆揪軟了的男人。這樣的“耳朵”角色和稱呼,在四川人的日常生活中和生活故事里比比皆是。“耳朵”是一群表面怕老婆、實(shí)際很快樂的幸福男人。
另有一個(gè)“倒”字,在四川話和四川故事中,出現(xiàn)的頻率非常高。它一般跟在動(dòng)詞后面,與助詞“著”的意思相同,表示動(dòng)作的持續(xù),如“跟倒(跟著)我走哈”“找張帕子來包倒(包著)”“頗倒(拼著)這條老命不要”。四川有一首家喻戶曉的兒歌:“紅蘿卜,蜜蜜甜,看倒看倒要過年。”其中的“看倒看倒”,就是“看著看著”的意思。我們《民間文學(xué)大系·四川卷》編委會(huì)也討論過是否可以用“到”字取代“倒”,注明讀三聲;但如果那樣,不但失去了四川方言的地方味道,詞性和意思都走樣了。所以,最后一致同意保留方言“倒”字,添加注釋。
少數(shù)民族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譯文中,常常出現(xiàn)一些音譯的特殊詞匯,這就需要我們做好注釋。如彝族故事中,便經(jīng)常出現(xiàn)“沙伍”(彝語(yǔ),對(duì)丈夫的稱呼)、“媳嫫”(彝語(yǔ),對(duì)妻子的稱呼)、“茲莫”(頭人)等詞匯,均需一一做注。像“克智”這樣的詞匯,更需認(rèn)真理解后完善注釋。“克”即“口”的意思,“智”有“移動(dòng)”“搬遷”的含義。“克智”一詞,譯成漢語(yǔ)即“嘴巴的靈活移動(dòng)和運(yùn)用”之意。克智,在彝族民間一般俗稱“克嘶哈舉”或“克格哈查”,即“嬉戲辯嘴”,意為對(duì)口詞或?qū)φf詞,是彝族一種傳統(tǒng)的二人“斗嘴”的擺談方式,一人說,一人對(duì),詼諧有趣。這是將歷史文化知識(shí)以幽默風(fēng)趣、嬉戲的形式,說唱給聽眾聽,讓聽眾在娛樂中受到教育。
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語(yǔ)言,使用了大量的方言土語(yǔ),顯得單純質(zhì)樸,有時(shí)甚至顯得“粗”“野”。相比之下,作家文學(xué)的語(yǔ)言則“細(xì)致”“復(fù)雜”一些。但“粗”“細(xì)”“單純”“復(fù)雜”本身,并不是衡量作品質(zhì)量好壞、高低的標(biāo)準(zhǔn)。細(xì)致是一種美,粗獷也是一種美!這如同四川人喜歡吃細(xì)絲的擔(dān)擔(dān)面,山西人喜歡吃粗塊的刀削面,各有各的嚼頭,各有各的風(fēng)味。如果說作家文學(xué)是一種“錯(cuò)彩鏤金”的加工美,民間文學(xué)則是一種“清水芙蓉”的本色美。
明白了民間文學(xué)廣泛使用方言,因而顯得自然清新、充滿泥土芬芳的特點(diǎn),我們?cè)谟涗洝⒄怼⒕幾牒蛡鞑ッ耖g文學(xué)作品的過程中,就會(huì)自覺地、更好地理解、保留并注釋好方言,更好地體現(xiàn)和傳達(dá)出民間文學(xué)作品固有的美學(xué)價(jià)值和地域特色。如此,也就能為更多的人在將來還能聽懂四川方言、看懂四川方言,提供一些幫助。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