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連珠體的出現是古人將墨家推類思想形式化的一種嘗試,透過它的發展可以看出墨家推類思想的興衰史。通過分析歷代連珠體與墨家推類思想,可以發現連珠體的創作機制同《墨子·經上》中“三知”說有密切關聯,即連珠體是將“聞知”、“說知”、“親知”三者融為一體的綜合表達,常以“聞知”起頭,以“親知”為轉合,以“說知”來結尾。歷代連珠在推理中,展現出一種歸納、演繹、類比、論證兩兩銜接或三者合一的語用邏輯,這正是對墨家推類的繼承和發展。
關鍵詞: 連珠體; 墨家; 推類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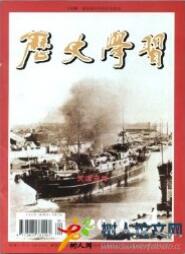
“推類”一詞最早見于《墨子·經下》“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1]319可見,“推類”乃建立在“說”的基礎上。又《墨子·經說上》“方不,說也”[1]350,又知“說”其實是以“類”為基礎,是一種“見者可以論未發”式的概括。也就是說,“推類”的本質是針對前提與結論所述對象的基本屬性在類同的前提下進行的一種推斷。早在《論語·八佾》中就有“推類”的實例:“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曰:‘禮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2]25并且據《論語·述而》載,孔子說過:“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2]68可見他對“舉一反三”的推類是多么重視,但他沒有就此深究方法和構建理論體系,這個工作最終由墨家完成。《墨子》一書中也有許多推類的實例,但不算典范,在中國早期文學中,有一種叫“連珠”的文體是以推類為基礎的,堪稱推類之典范。連珠的存在如同一種活化石,它是古人最早將推類思想形式化的一種標記。本文在剖析連珠體的結構、梳理連珠體的發展過程的基礎上,研究連珠體與墨家的邏輯思想和推類方法的關系。
一、連珠體創作機制與墨家的“三知”
《墨子·經說上》將人獲取知識依據分為三類:“知:傳受之,聞也。方不,說也。身觀焉,親也。”[1]350即“聞知”、“說知”、“親知”三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統一。“聞知”即通過傳授得來的知識。“說知”從已知推得未知,即所謂“以往知來,以見知隱”,是一種從推理過程獲得的知識。“親知”是“通過自己的親力親為,從繁雜的社會現象或實驗中概括總結出的新知”[3]。
縱觀歷代連珠體的形式,大體有兩類:一類為兩段式連珠,即“臣聞……,……”“臣聞……是以……”“臣聞……故……”另一類為三段式連珠“臣聞……是以(故)……故(是以)……”“臣聞……何則?……是以……”從形式上看,連珠體開頭常以“臣聞”起,類似于墨家所述的“聞知”。在二段式連珠中常采用“是以”“故”等連詞表達結論或論據,類似于墨家所述的“說知”。在三段式連珠中,“是以”“何則”之后的述說更偏向于墨家所述的“親知”。在“故”“是以”之后則是墨家所述的“說知”,分析如下。
(一)二段式連珠。
1.揚雄《連珠》:
“臣聞:明君取士,貴拔眾之所遺;忠臣薦善,不廢格之所排。是以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也。”揚雄根據“明君取士”“忠臣薦善”兩個行為指向的結果具有類同關系,即“人才不會被埋沒”;基于這種“聞知”他得出“說知”,即“巖穴無隱,而側陋章顯”的邏輯推理。此首連珠的推類本質是一個不完全歸納推理,其前提與結論之間是一種或然聯系。這種推類方式存在于墨家推類方法之中,即推理者以類同關系為基礎,將前提中行為結果的某種屬性貫通其類,推斷該類的全部對象都具有這種屬性。
2. 班固《擬連珠》: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公輸愛其斧”“明主貴其士”的行為指向結果具有類同關系,即“愛其物,成其治”。班固通過“聞知”,即“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來“說知”即“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前后形成類比推理,其前提與結論之間也是一種或然聯系。
3. 庾信《擬連珠》: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高門。盈虛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庾信借助“聽聞”先列舉事例,即“廉頗將軍和翟廷尉顯貴當權時,常常賓客滿堂,當失去權勢時,則無人拜訪,變換很快”。感慨“人與人交往都是以貴賤來衡量,有何交情可論?”同樣依據與廉頗將軍和翟廷尉得勢與失勢的類同性,庾信又從反面感慨“說知”,即“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表達了對知己之可貴,忠友之難遇的認知。
(二)三段式連珠。
1.陸機《演連珠》: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圣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此類連珠為陸機首創,常以“臣聞”起頭,“是以”轉合,最后以“故”來引申結尾。完美融墨家“三知”理論為一體,具體先以“聞知”表述臣聽說“音樂以悅耳為美,女色以悅目為喜”,后以“親知”認為“眾人聽感所喜歡的,就無需借用北里古樂的歌曲;許多人所欣賞的美,就不必等待古代西施容顏的再現”。依據“眾聽所傾”“萬夫婉孌”行為所指的類同性,即“當順應時代之有,無空慕古人”,最后通過“說知”推類出“圣人應當順著時代所擁有的人才來選拔輔佐的大臣;明智的君主當順應時代的需要來任命官吏”。從“聞知”到“親知”是一種演繹推理,從“親知”到“說知”是一種類比推理,從“聞知”到“說知”又表現為一種演繹推理。
2.陸機《演連珠》:
“臣聞:尋煙染芬,熏息猶芳;征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于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此類連珠也首創于陸機,其基本形式為“臣聞……何則?……是以……”從推理形式看,以“聞知”述所聽來的道理,即“順著煙氣沾染香味,煙氣消散后仍有芳香。求歌曲的節奏就記下它的音調,等那歌曲結束時,音調也會沒有了”。次以“何則?”為轉合引出作者“親知”的見解,即“用書面文字留在世上的法則可以繼續流傳,局限于自身抽象的神感應是不可傳的”,最后“說知”推類出“禮教的流風常常存在,變動不測的政化卻早已泯滅了”。從“聞知”到“親知”是一種歸納推理,從“親知”到“說知”是一種演繹推理,從“聞知”到“說知”又表現為一種演繹推理。值得注意的是,“親知”所得到的認識也并非全部正確。在今天的物理學中,知“尋煙染芬,熏息猶芳”其實是空氣分子運動的結果,“征音錄響,操終則絕”其實是物體振動的結果,并非陸機所認識。從側面證明“親知”是作者通過親身實踐得來的知識,但由于古人認識水平有限,因此此類連珠中“何則?”后“親知”所得到的觀點存在詭辯可能性。
通過對連珠不同形式的分析,發現連珠體創作機制其實是將《墨子·經上》中“聞知”、“說知”、“親知”三者融為一體的綜合表達,從側面說明連珠最早是墨家推類思想的形式表現。二段式連珠的創作機制常以“聞知”起頭,以“說知”推類來結尾,它表現出一種歸納、演繹、類比兩兩銜接的語用邏輯形式。三段式連珠的創作機制也常以“聞知”為起頭,以“親知”為轉合,以“說知”推類來結尾,表現出一種歸納、演繹、類比兩兩銜接或三者為一體的語用邏輯形式。
二、歷代連珠體的推類邏輯分析
縱觀連珠體的發展脈絡,它萌芽于《墨經》,起源于韓非子,肇名于揚雄,成熟并興盛于魏晉南北朝時期,唐以后雖漸衰,但宋時開始回溫,明朝又復興,至清代再次達到頂峰,清末至民國時期再次衰微。通過梳理歷代連珠體語料,發現連珠體的出現絕非偶然,是后人在論辯中繼承發展了墨家推類實用性的結果,也有學者認為:“連珠是古人為了建立一種有效的論證推理形式而做出的一種嘗試”[4]。事實上,墨家推類思想也是借助連珠體得到了強化與實踐,某種程度上連珠體的發展史也是一部研究我國推類思想興衰的發展史。
(一)先秦至兩漢時期。
依據早期文獻,在先秦至兩漢時期,連珠除推類式外,還存有論證式。推類式中又可分類比式、歸納式、歸納演繹式,而此階段類比式最為豐富。無論是推類式,還是論證式,皆在類同原則下推理。具體如下。
1.類比式。
班固《擬連珠》:“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廈,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班固通過描述好的工匠會衡量材料的適宜與否,因而才能建成大廈。班固將“英明的君主”與“良好的工匠”在成其業的行為上作類比,找出其共同點即重視衡量其材之所宜。
2.歸納式。
潘勖《擬連珠》:“臣聞媚上以希利者,臣之常情,主之所患;忘身以憂國者,臣之所難,主之所愿。是以忠臣背利而修所難,明主排患而獲所愿。”潘勖以類同為基礎說明兩種行為“諂媚君上以希求利益”、“忘身憂國”,從君臣角度點明了君臣利害的相反性,進一步歸納出忠臣能舍己之利,去君之害,做到使君臣利害一致。
3.歸納演繹式。
蔡邕《連珠》:“臣聞目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蔡邕先說庶民當遇到“目潤耳鳴”“狐鳴犬嘷”的異常時尚且知道收斂行為并以符箓驅邪,而作為君主當遇到天示災異時,則更需恐懼反省,改善政務。細加分析,這里有兩層推理。人人遇此類征兆都戒懼惶恐、謹慎行為,君主當亦不能例外,用的是歸納推理。君主之禍可及天下,不止于其身,故君主避禍,必須“修政”,這又暗含了演繹推理。
推薦閱讀:《歷史學習》本刊為全國惟一面向高中生的歷史雜志。本刊以研究高參、輔助學習、啟迪思維,培養能力為宗旨,結合高參復習實際,在應試訓練中培養學科素質,提高歷史思維能力。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