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地大物博,而且每個地區和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地域文化和文學作品也有很大的聯系,地域文化、文學作品與作家,這三者密不可分。本文是一篇文化期刊投稿范文,主要論述了西海固與中原地域文化差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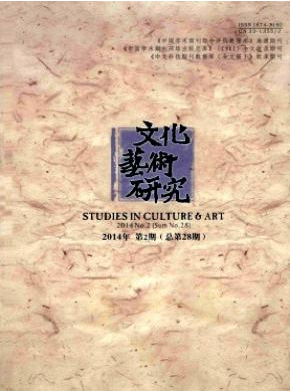
摘要:基于地域文化與文學的關聯性,對西海固作家馬金蓮與中原作家傅愛毛的作品進行比較,從不同的性別意識、生存困境、精神信仰三個方面入手,呈現西海固和中原地區的不同生存背景和社會風貌,分析現代性進程中所造成的精神苦難。以不同的視角切入,旨在探求西海固與中原地區的文化差異。
關鍵詞:西海固文化,馬金蓮,中原文化,傅愛毛
地域文化既是文學作品所表現的重要內容,又影響著作家的思維方式、藝術風格等;文學作品既體現了地域文化的內容,又反映了作家對文化的認知與體悟;作家是地域文化與文學發生關系的紐帶。從西海固回族馬金蓮與河南傅愛毛兩位青年女作家的創作來看,她們的作品都流露出了女性主義的光輝,又體現出西海固與中原地區不同的性別文化。因為馬金蓮作為回族穆斯林作家,她的作品體現出由于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差異。這些差異和特點,為我們以她們作品的比較來探求西海固與中原文化差異提供了可能性。
一、不同的性別意識
以性別批評的視野來看,在馬金蓮與傅愛毛的作品體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性別文化心理與女性的地位差異。馬金蓮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是逆來順受的性別悲劇形象,而傅愛毛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敢于追求自己的意愿,抵抗傳統文化強加給女性的悲劇。馬金蓮的作品中,造成女性悲劇的往往不是男性的壓迫,而是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造就的不合理的文化枷鎖。《碎媳婦》中,雪花新婚第二天就早早起來打掃房間,生怕引起婆家人的不滿,懷孕四個月時,嫂子即便看出來也裝作不知道,還是將重活推給她,“嫂子在婆婆手下熬了多年,該是站在婆婆的位置上使喚別人的時候了。”1可見這種舊觀念已經根深蒂固,雪花一樣逃脫不了這種壓迫模式,處處小心隱忍。雪花、嫂子、婆婆就像是女人的輪回,從生看到死。正如馬曉燕所述,“她們可以與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做堅韌的抗爭,但她們并沒有試圖打破舊觀念主宰自我命運的努力。”2從馬金蓮的小說可以看出,西海固的女性地位低下,也沒有擺脫文化的因襲與制約,人們的性別文化觀念相對落后。傅愛毛作品中的女性追求靈與肉和諧的生存狀態,雖然她們也是卑微的甚至是悲劇的,但來自性別壓迫的文化模式已經消弱了,更多的是現代性帶來的悲劇,傅愛毛作品中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試圖沖破的是現代性的裹挾。在《女兒嫂》中,秋禾在相親中看中了王石根,卻因為揣摩不出王石根的心思而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自尊。《你是我的眼》中楊靜云長期被丈夫冷落,她對盲人按摩師木耳發生興趣,帶著對命運的反抗和掙脫,她將情感投入到木耳身上,使自己的生命之花重新綻放。“她所認可的性,不是力比多的純粹釋放,它是身體的交合,也是生命的交流與升華,是靈魂參與的精神燃燒’。”3傅愛毛在很多作品中寫出了女性對性的覺醒,甚至直白地寫男性對女性的依賴。性別文化在她的作品中已經被消解了,展現的是小人物在冷漠功利的現代性潮流中以近乎偏執的姿態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
二、不同的生存困境
馬金蓮和傅愛毛在作品中分別描寫了物質的貧瘠和精神的貧乏,關照了人的生存困境。饑餓、天災、人禍是馬金蓮在作品中不斷被敘寫的,面對西海固極端貧瘠的物質生活,人總是顯得卑微、渺小,尊嚴、信仰都在生存面前讓步。如果說馬金蓮寫出了西海固的生存苦難,那么傅愛毛就是寫出了現代化的弊端給普通的小人物帶來的精神苦難。精神的貧乏如同物質的貧瘠一樣危險,都威脅著人的生存。馬金蓮展現的是西海固的生存文化。生存是第一性的,西海固的極端貧窮和缺水使它一度被人們稱為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地區之一。西海固文學仿佛就是苦難的影子,遠離了現代性。馬金蓮說“生長在這樣的土地上,并將生命里將近三十年的時光留在這里,不寫苦難,那我寫什么?還能寫什么?我們本身的生活,就是一段苦難的歷程。”4《父親的雪》中隊長擔心耕種的人偷吃糧食將一桶尿倒進糧食里,耕種的人還是忍著惡心偷吃,饑餓讓人無暇顧及尊嚴。生活的艱辛使原本心善的二娘也開始“摔摔打打”,“她是在抱怨丈夫,收留了我們,叫她原本艱難的日子更加艱難。”5饑餓和貧困是真實存在、無法擺脫的,在生存面前,人們無法顧及情感。作為八零后的女作家馬金蓮所書寫的苦難毫不矯揉造作,是屬于西海固的苦難,是貧瘠的土地自帶的苦難,是由物質的極端匱乏引起的苦難。作品對現代性的消解和隱匿使得西海固的生存文化顯示得更加清晰,西海固落后、封閉的生存環境使作品像在其中生存的人一樣有一種樸素的韌勁。傅愛毛書寫的是現代性帶來的異化和物化,她的大部分作品展現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傅愛毛將人物置于極端環境下,以小人物的視角俯看現代化文明帶來的一切變化。《桃花劫》中,夜來香偏執地追求愛情,吳瘋子本來愛她如癡如醉,將價值連城的蟲草送給她,在清醒以后卻要回了蟲草離開了夜來香。“那個不動聲色的草棒子總是最終不費吹灰之力地瓦解和粉碎她的愛情。”6現代文明和商品意識沖垮了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堅守,金錢的分量超過了情感,物化了人的心靈。在現代化進程中,生存不再成為問題,而人的靈魂與情感卻無處安放。正如艾愷所說,“現代化及與其同時存在的反現代化批判,將以這個二重性的模式永遠地持續到將來。”7傅愛毛在作品中雖然關注的是處于社會邊緣的殘缺的小人物形象,但其中無不映射了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原文化現象。
三、不同的精神信仰
馬金蓮是以回族身份進行寫作的,她的作品處處體現著伊斯蘭宗教文化的侵染。因為作品呈現出強烈的精神歸宿感,可謂是“有根”的寫作。相比較而言,傅愛毛則呈現為“無根”的寫作,她作品中的人物是脫離于社會生活的,沒有精神支撐的,游離的生存狀態折射出作家內心對社會生活的感知。馬金蓮作為回族作家,作品中處處有回族生活和伊斯蘭宗教文化生活的呈現。在《吃油香》一文中村支書家有權有錢,玲子的奶奶每年都可以過古爾巴尼,向真主獻牲,賽麥的奶奶一向很守教門,但因為家里貧窮連羊也宰不起,“賽麥的奶奶還是少著一樣,只一樣,讓她沒法和玲子奶奶平起平坐。活著沒法比,顯然無常后也沒法比。”8古爾巴尼就是穆斯林的宰牲節,宰牲節的意義是敬真主、濟貧困、去私欲、近親友。但是支書家的古爾巴尼卻另有含義,吃油香就是走人情,家家戶戶都想跟支書家西海固與中原地域文化差異探微——馬金蓮與傅愛毛作品之比較王軍利呂穎(北方民族大學750021)•文藝評論•拉關系。這顯然與伊斯蘭文化真正的要義相違背。由于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等文明日益發生交集,引發了西海固回民的文化心理沖突,馬金蓮對這一文化現象做了反思,并且對這些問題有更為準確和自覺的理解。《長河》中的母親在死前不吃不喝為了能夠干凈地離開世界,死亡對于她是真主的召喚,是一種“復命歸真”。馬金蓮對死亡的描述是平靜和從容的,體現了伊斯蘭文化的生死觀。西海固文化中少不了伊斯蘭宗教文化的支撐,馬金蓮在她的作品中展示了西北回民的生活風貌和他們獨特的精神品質。作為對比,傅愛毛的作品恰恰反映了沒有宗教文化支撐的中原地區人們精神信仰的崩塌和民俗文化的沒落。《桃花劫》中,劉瘸子是賣涼粉的手藝人,后來為夜來香燒制泥塑,做的出神入化。《天堂門》中的端木玉在殯儀館做遺體整容師,在孤獨中注意到了殯儀館巷子深處做紙扎吹嗩吶的手藝人,雖然是個啞巴,但和端木玉一樣有著自己的獨特的精神世界和情感需求,最終他們走在了一起。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帶有非理性的偏執堅守自己的精神世界,不為現代文明帶來的弊端所動搖。傅愛毛將民俗文化的魅力敘寫得生動感人,期間蘊含著作者對民俗沒落的惋惜和對現代性的批判。結語從不同的性別意識來說,馬金蓮的小說反映了西海固各個年齡層次的女性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中隱忍、卑微的生存狀態,而傅愛毛的小說中展現的中原女性則懷著強烈的自尊和自覺的意識抵抗性別壓迫的文化模式;從不同的生存困境來說,馬金蓮在作品中展現的是西海固貧瘠的土地給堅韌的人們帶來的生存苦難,傅愛毛則是在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沖突中敘寫現代性帶給人的精神苦難;從不同的精神信仰來說,馬金蓮的作品顯示了在西海固生存的人們對自我精神信仰的堅守,傅愛毛則展示了現代文明和商品意識帶給人精神信仰的崩塌和民俗文化的沒落。通過對馬金蓮和傅愛毛兩位作家作品的比較,可以看到,她們分別對西海固和中原地域的文化所進行的反思、認同與批判。作品當中也寄寓了作家的人文關懷和理想追求。讀者不僅要在她們的作品中品味文化對人發生的作用,還要看到文學作品對人的影響以及人對文化的促成和改變作用.
優秀文化論文投稿期刊推薦:《文化藝術研究》(雙月刊)創刊于2007年,是由浙江省文化藝術研究院主辦的戲劇藝術刊物。發表最新創作整理的優秀劇本(包括現代劇、新編歷史劇、經整理加工的傳統劇),當代著名藝術家及藝壇新秀的藝術經驗和勇于探索的心得,同時發表有關戲曲改革和現代戲劇創作方面的理論及有關戲劇史料等文章。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