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14年修改的《行政訴訟法》在第 70條增加“明顯不當”作為“濫用職權”之外對行政裁量行為合法性審查的依據(jù),第6條仍堅持合法性審查的訴訟原則。修法后的合法性審查原則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兩個階段。《行政訴訟法》第70條前四項是基于合法性審查要素,即事實認定、程序合法、法律適用和職權法定所作的劃分,屬于第一階段的形式合法性審查,而“濫用職權”和“明顯不當”是對行政裁量行為內(nèi)部界限的審查,是第二階段的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標準。兩者的區(qū)別在于審查要素,前者適用于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程序裁量與處理決定中裁量的濫用,而后者適用于法定職權這一要素,并回歸至是否具有主觀過錯的判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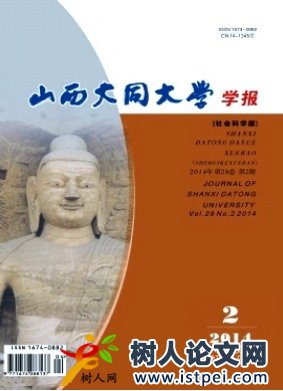
陳子君, 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發(fā)表時間:2021-08-18
關鍵詞:合法性審查;明顯不當;行政裁量;實質(zhì)合法性
2014 年《行政訴訟法》修改,增加“明顯不當”作為撤銷判決的適用依據(jù)之一。法院對行政行為合理性問題的審查由此得到立法確認,“行政訴訟堂而皇之地進入合理性審查的時代”。[1] 但總則部分仍堅持合法性審查基本原則。這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即如何認識“明顯不當”與本法第 6 條仍堅持的合法性審查原則間的關系。
1989年《行政訴訟法》第54條遵循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要素對審查依據(jù)予以劃分。有觀點基于審查標準劃分依據(jù)上的統(tǒng)一,認為包括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凡涉及事實認定的適用“主要證據(jù)不足的”,法律適用則依據(jù)“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的”,“程序違法”適用“違反法定程序”標準,而“明顯不當”則適用于效果裁量的處理決定中。[1-2] 問題在于“明顯不當”是否仍遵循行政行為合法性要素的劃分標準,是否僅適用于效果裁量上的結果不當,還是包括行政程序、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等要件裁量不當?本文將基于“明顯不當”的分析,對合法性審查原則的適用關系予以探討。
一、“明顯不當”的一般內(nèi)涵
“明顯不當”本身即為不確定法律概念,學界對其適用標準和適用范圍等存在不同觀點。以下將從生成路徑和性質(zhì)兩方面對其進行探討。
(一)“明顯不當”的生成路徑
1.“明顯不當”的詞源生成 學理上的生成路徑包括:一是行政訴訟的審判依據(jù);二是國家賠償?shù)臍w責原則。
首先,明顯不當是行政裁量行為審查的重要依據(jù)。如有學者在論述司法權對行政裁量權的控制時指出,“行政機關的決定如果明顯不當,即使在法定范圍和幅度之內(nèi),人民法院亦應當依法予以撤銷或變更”。[3] 具體適用有:一是“明顯不當”直接、單獨作為規(guī)制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依據(jù)。如沈巋教授主張在立法中增加“裁量明顯不當”標準以彌補“濫用職權”對行政裁量規(guī)制的不足。[4] 張澤想教授認為“只有當行政機關作出的罰款決定不合法或明顯不當,通過行政訴訟途徑人民法院才能撤銷。”[5] 二是“明顯不當”是“顯失公正”的具體認定標準。陶積根認為: “在法律沒有對行政處罰明顯失公、具體行政行為明顯不當作出明確規(guī)定前或作出司法解釋,上述十種比較方法,是可供參考的。”[6]
其次,在國家賠償?shù)臍w責原則中,“明顯不當”是違法性歸責原則的補充。違法性歸責原則是指行政行為違反客觀法律規(guī)范,著眼于合律性審查。雖然標準客觀,易于掌握,但它完全排斥了嚴重不當?shù)男姓昧啃袨榈那謾噘r償問題。[7-9] 明顯不當歸責原則彌補了對行政裁量賠償責任認定的缺漏。
2“. 明顯不當”的規(guī)范生成 “明顯不當”最先出現(xiàn)于 1991 年《行政復議法》第 28 條的規(guī)定中。1989年《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只有在行政處罰中可適用“顯失公正”作出變更判決。在此階段《行政訴訟法》堅持以合法性審查為主,例外進行合理性審查的原則。 “明顯不當”成為行政復議對行政行為進行合理性審查的重要標志。2014 年《行政訴訟法》增加“明顯不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情況的匯報》闡明了立法修改的考慮因素,即對明顯不合理的行政行為予以審查。“明顯不當”的立法目的之一在于對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
綜上,“明顯不當”完善并擴大行政訴訟的審查標準,彌補了行政訴訟中對行政裁量行為審查不足的弊端。
(二)“明顯不當”的性質(zhì):實質(zhì)合法性 修法后的立法不銜接在于“明顯不當”如何與總則中的合法性審查原則相銜接。而合法性的內(nèi)涵與“明顯不當”的性質(zhì)明晰成為立法協(xié)調(diào)的關鍵。
1.合法性與合理性的關系明晰 兩者的關系主要存在以下觀點:一是以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例外進行合理性審查說。行政訴訟的功能之一即監(jiān)督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而監(jiān)督強度隨法律對行政權的約束強度不同而有所差異。正如“法律約束的松動相應地引起行政法院審查的松動,因為行政法院只審查行政活動的合法性。一旦行政機關享有裁量空間和判斷余地,就享有‘最后決定’的權利”。[10] 1989年《行政訴訟法》確立了“合法性審查為原則,例外進行合理性審查”的原則。該說主張第6條的合法性審查原則為形式合法性,明顯不當為合理性審查。二是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原則說。該說認為明顯不當在“合法性審查”基礎上,在內(nèi)容的廣度與深度上進行了擴展,實現(xiàn)了從形式合法性到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的轉(zhuǎn)變。[2] 如何海波教授認為,合法、合理和合憲性審查共同構成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1] 程琥法官從法律淵源角度認為,形式合法性不能完全實現(xiàn)法律目的和立法精神,需將行政行為置于社會需求、社會價值、社會變化中進行考量。[11] 該說從廣義角度理解合法性審查原則,包括合理性和合法性。
觀點二契合當前實質(zhì)法治的發(fā)展現(xiàn)狀。不足在于:一是違反法律制度中的立法初衷。合法性審查原則的功能在于明確司法權對行政權的審查界限。但廣義合法性將合理性囊括其中,若以廣義合法性的觀點理解合法性審查原則,難免會使行政權的自主空間被侵蝕,對行政裁量行為的司法審查邊界可能日益模糊;二是未明確合法性與合理性之間的界限。行政裁量行為是司法審查的重要內(nèi)容。[12] 但鑒于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專業(yè)性程度上的差異,司法審查需進行不同強度的審查。[13] 故不區(qū)分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構建一個籠統(tǒng)廣義的合法性概念無法對行政訴訟的審查強度予以類型化建構。因此認為,應堅持合法性與合理性區(qū)分的傳統(tǒng),避免司法權對行政權自治空間的越界,并將合法性原則區(qū)分為形式合法性與實質(zhì)合法性。
2“. 明顯不當”的性質(zhì)定位 在形式合法性、實質(zhì)合法性與合理性的三分結構下,“明顯不當”的性質(zhì)定位應結合其生成路徑和內(nèi)涵予以分析。
首先,從審查對象上看,“明顯不當”適用于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行政裁量行為的特殊性決定其審查模式不同于傳統(tǒng)上的形式合法性。立法者明確了對羈束行為的行為方式,行政主體需嚴格遵循立法規(guī)定。而行政裁量行為要求行政主體在具體案件中運用其專門知識、根據(jù)公益目的選擇判斷,補充立法的不足。易言之,在行政管理過程不僅蘊含著對政策執(zhí)行技術手段的判斷,還蘊含著對多元的、彼此競爭的社會價值給予優(yōu)先權的判斷。[14] 故行政裁量行為的合法性審查需要填補裁量權運行過程中行政機關所享有的法律條文字面含義之外的自主空間。因此,其審查依據(jù)在于廣義上的法,包括正式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立法目的、法治基本原則和習慣法等法律淵源。
其次,“明顯不當”最初的含義即“合法但不適當”。而行政訴訟法中的“明顯不當”是否與行政復議中含義相同呢?1989年《行政訴訟法》中行政處罰顯失公正,表現(xiàn)為行政處罰在“量”上的畸輕畸重,違背了過罰相當原則。修法后,“顯失公正”被修改為 “明顯不當”,從體系解釋角度看,“明顯不當”延續(xù)了 “顯示公正”在內(nèi)涵上的適當性審查,且范圍擴大至所有行政裁量行為。但由于第 6 條規(guī)定的合法性審查原則,且作為外部審查機制的行政訴訟僅在“明顯不合理”的情形下進行審查,有別于內(nèi)部審查機制的行政復議,“明顯不當”屬于實質(zhì)合法性。
二、與其他撤銷依據(jù)間關系的實證分析
與其他撤銷依據(jù)的區(qū)別在于,“明顯不當”屬于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適用于行政裁量行為,但是否僅適用于效果裁量階段?當明顯不當適用于要件裁量時,與其他撤銷依據(jù)間的適用關系仍需進一步分析。
(一)司法適用的實然圖景 本文以“關鍵詞:明顯不當;案件類型:行政-行政行為種類;時間: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繼 2014 年修法后, 2017 年再次對《行政訴訟法》進行修改,并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故選取修法后的 2018 年案例進行實證分析);法寶推薦;判決書”為檢索條件,對北大法寶中的相關案例進行檢索,有關“明顯不當”的案件共2376 例(最后檢索時間為 2019 年 10 月 13 日)。除去不符合標準和不相關案件(出現(xiàn)在原告的訴稱、被告的辯稱和法院的裁判說理中及非裁量爭議中),有66 例案件在裁判文書中將“明顯不當”作為審查依據(jù)。以下將對其司法適用予以分析。
1. 與其他依據(jù)間的適用關系 司法實踐中“明顯不當”與第 70 條中其他撤銷判決依據(jù)的適用關系有三種情形:一是單獨適用,即單獨作為案件的裁判依據(jù),共 35 例;二是共同適用,即與其他撤銷依據(jù)共同作為裁判依據(jù),共 25 例;三是未具體明確,但在說明理由中援引“明顯不當”,但在裁判依據(jù)中僅指出依據(jù)第 70 條進行裁判,共 6 例。共同適用具體包括兩類:一是并列式適用,共 16例;二是遞進式適用,共 9 例。并列式適用指的是雖然“明顯不當”與其他撤銷依據(jù)共同作為被訴行政裁量行為的撤銷依據(jù),但各依據(jù)間不存在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分別指示不同的違法情形。遞進式適用是指將“明顯不當”與其他撤銷依據(jù)共同作為被訴行政裁量行為的撤銷依據(jù),“明顯不當”具體指效果裁量中的違法,與其他依據(jù)存在因果關系。實踐中,“明顯不當”較常見的與“主要證據(jù)不足的、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的、違反法定程序的” 存在并列適用或遞進適用的情形,詳見表1。
首先是并列式適用。在“紹興欣琦酒業(yè)有限公司與安義縣市場和質(zhì)量監(jiān)督管理局行政處罰案”① 中,被告在查處原告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違法行為過程中,分別存在兩處違法情形,一是在處罰決定中沒有依法同時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二是對于被告作出的罰款決定,違反罰過相當原則。法官以第 70 條第(二)、(六)項之規(guī)定,作出撤銷判決。可見, “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與“明顯不當”分別指示不同的違法情形:一是在罰款的同時沒有作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等物品的決定;二是罰款數(shù)額不適當。兩者間不具有邏輯上的因果關系。
其次是遞進式適用。在“天長市振威機械有限公司訴天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行政確認案”② 中,依據(jù)《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規(guī)定, “明顯不當”表現(xiàn)為對“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自然人”這一法律概念的解釋存在瑕疵。由此,行政行為“明顯不當”與行政過程中的要件事實認定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
2. 要件裁量與效果裁量上的區(qū)分 有觀點認為 “明顯不當”僅適用于效果裁量中,要件裁量中的法律適用、程序和事實認定等要素適用第 70 條前四項撤銷依據(jù)。[1] 但“明顯不當”在實踐中的單獨適用也并非僅適用于在效果裁量階段存在爭議的案件中,也適用于要件裁量過程中,包括程序裁量、法律解釋中、事實認定中,詳見表2。
在行政強制案件中,爭議焦點在程序裁量階段。如在劉占軍訴哈爾濱市香坊區(qū)人民政府行政強制案③ 中,法院認為:“強制拆除房屋時,在劉占軍室內(nèi)物品未搬出的情況下,直接對房屋進行破壞性拆除,其拆除方式明顯不當”。“明顯不當”適用于行為方式上的選擇。
法律解釋階段的裁量爭議主要存在于工傷類案件中。如陳彩姬訴賀州市平桂區(q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行政確認案,④焦點在于如何解釋“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在 48 小時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的”。最終,法院依據(jù)“明顯不當”作出撤銷判決。
在事實認定中,以沈勇訴資中縣民政局行政登記案⑤為例。該案中,法院認為第三人謝敏的冒用行為導致資中縣騮馬鎮(zhèn)人民政府在辦理婚姻登記時對女方的身份認定錯誤,并依據(jù)冒用的身份信息頒發(fā)了結婚證,故該婚姻登記行為明顯不當,應予撤銷。登記決定不當?shù)闹苯釉蚣此罁?jù)的要件事實錯誤。
綜上,“明顯不當”作為行政裁量爭議的審查依據(jù),不僅存在于效果裁量中的處理決定,在實踐中也廣泛適用于要件裁量中。
(二)具體適用情形的歸納 “明顯不當”司法適用存在類型化趨勢,可從事實認定、程序選擇和法律適用三個環(huán)節(jié)予以歸納。
1. 要件事實不具備和事實錯誤 事實裁量明顯不當表現(xiàn)為:一是事實要件不具備,例如李兆芳訴天長市振威機械有限公司行政確認案。⑥爭議焦點在于《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四項規(guī)定的要件事實是否具備。后法院對《拋光加工協(xié)議》的審 查,認為其并不構成“將工程(業(yè)務)或經(jīng)營權發(fā)包”的事實。故認為原行政行為作出的要件事實不完全具備,依據(jù)“明顯不當”作出撤銷判決。二是事實錯誤情形。在沈陽兄弟港龍建材有限公司訴沈陽市環(huán)境保護局蒲河新城分局處罰決定案⑦中,被告沈陽市環(huán)境保護局蒲河新城分局在對原告擅自進行石材加工生產(chǎn)予以處罰時并未依照該生產(chǎn)項目的總投資計算處罰金額,而是以總投資9900萬元為標準進行處罰,系處罰標準選取錯誤,造成處罰結果明顯不當。
因此,只有在事實不具備或顯然錯誤時,法院認定為“明顯不當”,即案件事實真實性的審查,而非優(yōu)劣審查,屬于較低強度的審查。
2. 程序裁量中處理方式不當 程序裁量明顯不當主要出現(xiàn)在行政強制類案件中,表現(xiàn)之一即為行為方式上的不適當,具體指強制措施的實施方式。如劉占軍訴哈爾濱市香坊區(qū)人民政府行政強制案,③ 法院認為“強制拆除房屋時,在原告室內(nèi)物品未搬出的情況下,直接對房屋進行破壞性拆除,其方式明顯不當,缺乏正當性”。
此外,違反正當法律程序是否屬于“違反法定程序”?在“西熱里·吾布里哈斯木訴烏魯木齊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行政處罰案”⑧中,法院認為行政機關在未通知行為人監(jiān)護人當場,且未對監(jiān)護人進行詢問時,對其進行處罰已違反法律規(guī)定。這一行為違反法律程序,且行政處罰明顯不當,故依據(jù)“違反法定程序”與“明顯不當”作出撤銷判決。其中雖運用了“明顯不當”,但從論證路徑來看,我國《行政處罰法》和《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并未規(guī)定在對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進行詢問或處罰時,應通知其監(jiān)護人在場。與之相關的條款見諸于第 84 條“詢問不滿十六周歲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應當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監(jiān)護人到場”。可見,法官援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運用了擴大解釋的方法,將“違反法律程序”這一依據(jù)適用于本案,而“明顯不當”是對處罰決定實體效果的評價。由此從廣義上解釋“法”的內(nèi)涵,使正當法律程序成為“違反法定程序”的適用標準。
3. 法律適用中的不當 法律適用明顯不當表現(xiàn)為:一是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問題。此類情形大量出現(xiàn)于工傷認定行政確認案件中。如在陳彩姬訴賀州市平桂區(qū)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行政確認案④中,法院認為程某在上午8時左右請假回家休息,當日10時左右經(jīng)搶救無效在家死亡,滿足“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fā)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nèi)經(jīng)搶救無效死亡的”,行政機關的法律解釋不適當,依據(jù)“明顯不當”作出撤銷判決。二是對經(jīng)驗性概念的擴大或限縮解釋問題。在李勝訴沈陽市蘇家屯區(qū)交通運輸管理處行政處罰案中,爭議的焦點在于原告在無運營手續(xù)的情形下以順風車行使開展旅客運輸經(jīng)營活動的行為是否屬于傳統(tǒng)上的非法營運活動。關鍵在于面對當前尚無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規(guī)范的新生業(yè)態(tài),能否將其直接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運輸條例》第79條中關于違法運營的規(guī)定。最終,法院認為被告未從提供服務指導的角度規(guī)范該新生業(yè)態(tài),法律解釋“明顯不當”。
三、合法性審查標準體系的完善
“明顯不當”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程序選擇環(huán)節(jié)也存在適用空間,并呈現(xiàn)出適用情形上的類型化。為此,有必要對各撤銷依據(jù)間的關系進行再思考,以完善合法性審查標準體系。(一)雙階段的合法性審查標準體系 第70條中的六項標準依據(jù)不同的劃分標準,前四項依據(jù)合法性審查要素,而“明顯不當”是在審查標準層面上確立,適用于效果裁量和要件裁量。故合法性審查包括形式合法性與實質(zhì)合法性兩階段的審查,區(qū)別有:首先,在審查對象上,行政裁量實質(zhì)上是指行政機關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nèi)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一種選擇。[15] 但行政裁量行為的合法作出存在內(nèi)在界限和外部界限的控制標準。外部界限,是為了防止裁量活動的結果在內(nèi)容上超越法律設定的界限,行政裁量越出其外部界限,構成裁量權逾越;內(nèi)部界限,是為了防止行政機關以與事件無關的動機作為裁量的基礎,或未考慮該當考慮的因素,行政裁量越出其內(nèi)部界限,構成裁量權濫用。[16] 兩者分別以行政裁量行為的外部界限和內(nèi)部界限為審查對象。
其次,在審查標準上,形式合法性分別適用于行政行為的某個合法性要素,而實質(zhì)合法性則適用于所有合法性要素,是在形式合法性基礎上進行的不同強度的審查。正如“法治不僅僅是制定和遵循一些具有法律形式的規(guī)則,而是尋求和貫徹良好規(guī)則的治理”。[17] 形式合法性以合律性為基礎,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的是行為內(nèi)容是否滿足法律原則、立法目的以及法治精神等。
此外,在審查方式上,對行政裁量的適當性判斷不再單獨從結果的嚴格適法性角度來認定,而側(cè)重于以行政法律關系為重心的過程性審查模式。這構成兩者的另一重要區(qū)別,即要素性審查和過程性審查。過程性審查是指法院根據(jù)行政機關的陳述,對行政機關以何種方式考慮何種事項作出行政行為進行重構,并在此基礎上對裁量過程的妥當性進行判斷。[18] 其標準有目的適當、考慮相關因素和比例原則的滿足。
綜上,合法性審查包括形式合法性和實質(zhì)合法性標準的統(tǒng)一。前者包括主要證據(jù)不足;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違反法定程序和超越職權;后者包括包括濫用職權和明顯不當。
(二)多強度的合法性審查標準體系 “明顯不當”內(nèi)含審查強度類型化的修法目的。德國聯(lián)邦憲法法院在審查公權機關行為是否符合比例原則時,在手段適當性、限制的必要性和利益均衡性三階段,區(qū)分低度審查、中度審查和嚴格審查強度。而合法性審查原則本身即關涉司法權與行政權權力邊界的明晰。[19] 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應基于以下因素在審查強度上予以類型化:對專業(yè)性事實問題的尊重性;在不同裁量階段中裁量空間的大小。
首先,在事實認定上,形式合法性著眼于證據(jù)規(guī)則的適用,而“明顯不當”則是對案件事實內(nèi)容真實性的審查,表現(xiàn)為事實錯誤或缺乏事實基礎。鑒于事實問題中的專業(yè)性判斷,故進行較低強度的審查。其次,在法律適用中,形式合法性審查標準中的“適用法律、法規(guī)錯誤的”以法律條文的選擇適用是否錯誤為審查內(nèi)容。而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表現(xiàn)為對內(nèi)容的解釋:一是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解釋不適當,例如未考慮相關因素、違背立法目的等。二是經(jīng)驗性概念的不當擴大或限縮解釋;再次,形式合法性審查中“違反法定程序”以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程序為審查前提。而程序裁量 “明顯不當”表現(xiàn)為立法授予下程序啟動和多種程序選擇中的裁量空間。法律適用和程序裁量多涉及要件裁量中不確定法律概念的運用。當涉及到技術性行政裁量或計劃行政裁量等專業(yè)性較強的事項時,法官對行政機關的裁量理由進行中度審查。最后,在效果裁量上,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以是否違背法律原則以及合目的性為參照系,進行強度較深的審查。
(三)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標準的內(nèi)部區(qū)分 如何認識“明顯不當”與“濫用職權”的關系呢?學界對此存在以下兩種觀點:一是主觀過錯說。這一學說基于法律用語之語義在法律體系內(nèi)部的統(tǒng)一性,而將其內(nèi)涵與刑法中的“濫用職權罪”相關聯(lián)。認為行政機關的主觀故意是濫用職權與其他不當行為的關鍵區(qū)分,過失不構成濫用職權,即便其實施的行政行為違背了法律規(guī)定的目的、原則和精神等。司法實踐也多遵循這一認定標準。二是濫用裁量權說。此說將“職權”界定為裁量權,“濫用職權”即為“濫用裁量權”。[20-21] 朱新力教授認為“濫用職權”存在五種情形:背離法定目的;對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的嚴重不當;行政不作為;不正當程序;行為結果顯失公正。[22] 而胡建淼教授主張存在六種情形:不正當目的或動機支配;不合法考慮致使行為結果失去準確性;任意無常;強人所難,不正當遲延或不作為,不正當?shù)牟襟E和方式。[23] 可見,學界多將“濫用職權”適用于對行政裁量行為的審查,且并不局限于主觀過錯的情形,還包括行為過程與結果上的適當性與否的評價。
以上探討混淆了“濫用職權”適用對象與審查標準的關系。觀點一從具體的審查標準來探討,而觀點二著眼于適用對象層面。從司法實踐中“濫用職權” 的低出鏡率來看,與主觀過錯相聯(lián)系的認定標準加劇了“濫用職權”的認定難度。為此,主張從審查要素與審查標準兩方面認識兩者之間的關系:一是在審查要素上,“明顯不當”適用于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程序裁量以及處理決定中,鑒于實踐中“明顯不當”與“超越法定職權”之間較少存在共同適用的情形。而“超越法定職權”卻經(jīng)常與“濫用職權”之間存在轉(zhuǎn)換性適用的現(xiàn)象,[24-25] 故“濫用職權”表現(xiàn)為濫用法定職權;二是在審查標準上,“明顯不當”以合目的性審查、相關因素考慮、違反比例原則等為判斷基準,而“濫用職權”回歸至行政機關在行為時主觀過錯的判定,即目的正當性審查。[26]
綜上,實質(zhì)合法性與形式合法性間的適用關系詳見表3。
結 語
隨著我國實質(zhì)法治發(fā)展步伐的加快以及行政裁量權的不斷擴展,應當從審查對象、審查范圍、審查標準等方面對合法性審查原則予以完善。合法性審查原則應當順應實質(zhì)法治的內(nèi)在要求,構建形式合法性與實質(zhì)合法性相統(tǒng)一的立體性的審查標準體系。概念體系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制度規(guī)范的健全。為此主張將第70條中的六項裁判標準依其劃分標準分別規(guī)定在兩條或兩款之下,區(qū)分為形式合法性與實質(zhì)合法性審查標準兩個層面。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