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舞劇創作實踐,從舞劇敘事形態切入并進行分類梳理,可以總結出四種不同時期:情節、性格、沖突等均以線性結構方式展開的 “啞劇敘事” 形態時期;情境、性格、沖突等均以多重交織方式展開的 “交響敘事”形態時期;以心理動機推進劇情方式展開的 “心理敘事”形態時期;以引導出某種觀念或發人深思的主題為目標方式展開的 “隱喻敘事”形態時期。四個時期的敘事形態有差異,也互有交叉。這些形態表達既是編導個人能動選擇的產物,同時也是對舞劇生產時代大背景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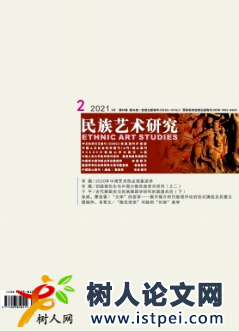
本文源自董麗, 民族藝術研究 發表時間:2021-06-25
關 鍵 詞:舞劇;敘事形態;中國舞劇史
在舞劇成為一門藝術時,關于舞劇的本性是 “舞”還是 “劇”,便成為舞蹈理論界爭辯的焦點。“舞”自不必說,這里的 “劇”,指的是 “講故事”,即所謂的 “敘事”。至于舞劇的敘事形態,則是舞劇敘事的全部要素所形成的舞劇整體性的精神品質和藝術特點,它包含著創作者對舞劇本質及其藝術特征、藝術手段等問題的認知與思考。本文就當代中國舞劇的敘事形態進行考察,旨在為當下 “舞劇敘事”形態的發展提供參照,為中國舞劇的創新貢獻內涵和新鮮特質。需要說明的是,雖然 “當代中國舞劇” 發軔于 20世紀30年代末是客觀事實,但本文所做的 “當代中國舞劇敘事形態”研究將其時間做了后移,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舞劇創作實踐。
一、以 “啞劇敘事”形態為代表的時期
關于 “啞劇舞蹈”或者說 “舞蹈的啞劇敘事”,首先是由 18世紀法國偉大的舞蹈大師、舞蹈評論家喬治·諾維爾提出的。他認為:舞蹈的生命和表現力是由 “情節” 和 “啞劇”賦予的。在他看來,“啞劇舞蹈”是 “動作舞蹈”的靈魂,而 “啞劇敘事”的主要手段則是采用 “手勢”;百余年后的福金繼承并發展了諾維爾的主張,進一步提出了 “擬態敘事”的觀點,即: “在一切場合上都要努力用整個身體的啞劇表演來取代手勢,人可以也應該從頭到腳整個身體都成為富有表情的”,① 他認為要用 “整個身體進行啞劇表演” 來進行舞蹈的敘事;此后,經歷了 “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更是有諸多編導更新發展了 “舞劇敘事”的進程,開始關注于如何 “使啞劇服從于舞蹈動作的規律” 以及 “構成富有情節性的、舞蹈化了的啞劇手段 ……”
我們追溯原始生發時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 “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舞劇創作,發現其對于 “舞劇敘事”的表達與認識,正是受上述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從 “啞劇敘事”開始的。雖說這一時期是中國舞劇創作的初始期,卻也成為中國舞劇史上的第一次創作高潮期,創作出多部具有代表性的舞劇。如現實主義形式下的 “新舞劇” 《和平鴿》《蝶戀花》 《五朵紅云》,傳統主義形式下的 “民族舞劇”《寶蓮燈》 《小刀會》 《魚美人》等等。其中, 《和平鴿》被稱為我國 “大型舞劇”的 “第一次嘗試”,《寶蓮燈》更被公認為鮮明成型的中國第一部大型民族舞劇。縱觀這一時期的舞劇創作,我們發現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在探索解決 “如何在民族文化藝術的傳統基礎上,吸收外來的經驗,創作新型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舞劇形式”,① 而這個探索最終的落腳點就是 “啞劇敘事”的編舞理念。不僅在實踐層面,當時的舞蹈理論研究也有不少關于講述舞劇中 “啞劇敘事” 的文章,如耐石的 《關于舞劇的戲劇結構》、曉符的 《淺談舞劇中的啞劇》、楊 書 明 的《淺析啞劇和舞蹈》等,這些文章既有對啞劇構成形態進行的界定,還有對啞劇表現手段的功能、啞劇手段運用的 “舞蹈化”問題以及啞劇與舞劇藝術的 “民族化”問題等諸多方面較為詳細的闡述。當然,文章的觀點大都認為啞劇的表現手法比較適合舞劇用來表現對情節的敘述。此外,“更有論者認為啞劇是我國傳統藝術 (特別是戲曲藝術)中的重要表現手段,以至于對啞劇這一表現手段的運用甚至構成了這一藝術的重要表現特征。”②
“啞劇敘事”形態的中國舞劇創作,對舞劇中 “啞劇”手段的理解和應用是最為突出的問題,有觀點就認為:“啞劇”是舞劇表現中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切不可只 “啞” 無 “劇”,也不可見 “劇” 不見 “舞”。看來, “啞劇”問題在我國舞劇理論建設的萌生之期就已經開始被關注了,它的根本就是如何理解 “舞劇”藝術中 “舞”與 “劇”關系的問題,而這也是至今我們仍然在探討的問題。這一時期舞劇的敘事結構基本遵循了故事現象層的發展邏輯來鋪陳劇情,即按照 “引子、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線性時空結構進行,具體體現在情節敘述的完整統一以及 “起承轉合”的脈絡清晰,呈現出 “劇舞交融”的敘事形態特征。以 1959年創作的大型民族舞劇 《小刀會》為例,最能清晰地顯示出這種敘事特征。當時創排該劇時,編劇張拓提出: “先把舞劇腳本按啞劇形式排出來 ……這種試排要求演員進入角色的規定情境,合乎邏輯地進行舞臺行動,惟一的限制是從不準說話卻要使觀眾看得懂表演的內容。預定有獨舞和雙人舞的地方,要求演員準備符合角色性格的內心獨白和潛臺詞;需要表演舞的地方則暫時用其他情緒接近的舞蹈代替 ……”③ 于是,這部舞劇的 “情節舞” 是以 “揭示規定情境中角色的內心世界”為原則(舞中有劇), “表演舞”也意在 “合情合理地存在于規定情境中” (劇中有舞);再如同一年創作的少數民族舞劇 《五朵紅云》,也是同樣強調 “以劇揚舞” “以舞言劇”并且同樣致力做到 “劇舞交融”。隆蔭培對其評論道:“《五朵紅云》舞蹈和戲劇情節的發展緊密無間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它們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④
以 “啞劇敘事”形態為代表時期的舞劇創作,雖說編導們已經開始關注如何更好地處理 “舞”與 “劇”的關系,但是由于對舞蹈自身規律的認識不足,因此仍有諸多問題存在。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此類舞劇無法離開啞劇來塑造人物、更無法刻畫人物的內心世界,因而 “影響著舞劇把握現實、特別是當代現實能力,也嚴重影響著舞劇作為一種獨特舞臺表演藝術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魅力”。⑤
二、以 “交響敘事”形態為代表的時期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使得國家在各個方面都遭受了難以彌補的嚴重損失,當然也給 “舞劇創作”帶來了浩劫。在 “演革命戲,做革命人”的號召下,作為優秀樣板的芭蕾舞劇 《紅色娘子軍》《白毛女》被推向了全國。“即便是 ‘優秀樣板’,也無 法 遮 掩 創 作 的 凋 敗 和 舞 臺 的 荒涼。”① 在這里我不多做贅述。轉眼到了 1979年,這一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年,同時我們也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30周年的慶典,這些都為中國舞劇創作的再崛起提供了歷時性機遇。這一階段,中國舞劇創作也呈現出蓬勃噴發之勢,創作了大批優秀作品,包括 《絲路花雨》 《文成公主》 《半屏山》《奔月》 《銅雀伎》 《鳳鳴岐山》 《大禹的傳說》等等。創作上呈現的百花齊放之勢皆源自作品在風格、流派、題材、手法上的不同,敘事形態當如是。
雖說這一時期舞劇敘事形態多樣,但首要提及的還是 “交響敘事”。實際上,這一從蘇聯借鑒而來的敘事手法不論是對此階段還是之后的舞劇創作影響都是頗深的。于平指出,“直至 20世紀 70年代末,我國的舞劇創作 才 在 局 部 不 自 覺 地 出 現 了 ‘交 響 敘事’———起 初 叫 ‘復 調 式 手 法’。”② 說 到 “交響敘事”,我們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是 “交響化”。其實它是一種音樂戲劇形式,往往通過作曲家寫一個性格主題,然后不斷發展變化,并在不同場景出現,以此加強作品表達的意蘊。舞劇的 “交響敘事”由此借鑒而來,表現為 “編導對劇中人物心理進行多層次的剖析與舞蹈動作的線條、舞姿、韻律、空間的多樣化的占有及節奏的轉換、動與靜的對比調節等諸方面作獨特的組合排列。”③ 作為這一時期極為推崇的創作手法,眾多編導們創作出了一批富有審美價值的舞劇作品,如舒巧的 《奔月》、蘇時進的 《一條大河》、張守和等人的 《無字碑》、范東凱和張建民的《長城》、蔡國英等人的 《阿 Q》 等等。其中,創作了 《無字碑》的張守和在 《舞劇的交響詩化———交響舞劇 〈無字碑〉的創作意識》一文中就寫道:“交響樂是我們創作 《無字碑》的主要支柱。全劇結構也正是深受其影響而構思設置,四幕的構成如同四個相互獨立又有機聯結的四個樂章;將幾個側面的心理狀態、情感變化、矛盾對抗,交織成多層次、立體化的心理情態結構……”④ 從劇中可以看出,“復調”的運用形成了戲劇構成的對話,而 “奏鳴曲”的運用則完成了戲劇沖突的展開與解決。這部舞劇的成功也充分說明,采用 “交響化”手段進行創作并沒有削減舞劇的 “戲劇性”,而是把 “戲劇性”建構在了人物性格沖突的基礎之上。和之前的 “啞劇敘事”形態相比,我們發現, “前者更注重情節的線性發展、性格的線性成長以及沖突的線性展開,而后者更注重情境的多重意蘊、性格的多重組合以及沖突的多重交織。”⑤ 可以說, “交響敘事”形態下的舞劇構成更符合舞蹈的審美,它提高了舞劇創作 “生產力”的水準,推動了舞劇創作的進步。
雖說此時舞劇創作因 “交響敘事”手法的應用而彰顯出開創性,但是也有因沿襲并深化傳統敘事手法并同樣表現不凡的作品出現,如仲林等創作的 《木蘭飄香》。這部舞劇仍然采用了線性敘事結構,但是它較好地解決了 “戲劇性結構的舞劇化問題” (啞劇敘事),使得舞劇在對題材處理、情節安排、人物形象塑造及性格刻畫等方面都有長足進步,它可以說是 “民族舞劇”創作的一次重要挺進。除此之外,還有以 “心理描述和心理結構”為敘事亮點的舞劇 《祝福》 《魂》 《家》《林黛玉》等;有以追隨話劇 “戲劇處理舞蹈化” (盡可能避免 “啞劇化”形態)結構的舞劇 《雷雨》;有以具有 “散文詩式”敘事結構的舞劇 《紅樓夢》 《覓光三部曲》;還有以 “戲劇性結構與主體意識有機結合”結構的 《悲鳴三部曲》……正如傅兆先所言,這一時期的 “中國舞劇在走向成熟階段,舞劇的結構方式也早已打破了情節結構單一線狀的形態,而有了多種新的結構方式的創造。”① “舞劇結構方式上的演變促進著中國舞劇藝術形式多樣化的發展。”②
20世紀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可以說是中國舞劇創作的第二個大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敘事形態把觸角伸到了之前傳統敘事舞劇不能到達的地方。從只能講述表層的故事或做出有限的心理探索,到能較為深入人物和故事的各個層面,舞劇的張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當然,肯定一種形式的創新時,也要看到其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能否認,這一階段也有一些舞劇過于強調敘事形態的 “個性化”,結果變成 “為敘事而敘事、為手法而手法”,使得劇情割裂得支離破碎,讓人不知所云。然而不管怎樣,以 “交響敘事” 形態為代表的這一時期的舞劇敘事確實為中國舞劇的探索提供了積極的力量,它不僅在當時,也對后來的舞劇創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以 “心理敘事”形態為代表的時期
20世紀 90年代至 21世紀初,就在舞劇編導個人的創作風格得到有效呈現之時,一種新的舞劇敘事形態,即:“心理敘事”形態也以它的方式開始了表達。追溯其產生的背景,則是源于 “舞劇整合的精細化必將由內向心理之維發展,舞劇對人的表現將會有內在深化的更高層次。”③ 這一時期,不僅初步形成了舞劇敘事形態的理論體系,而且創作實踐也開始走向了藝術的自覺。
首先,在理論上,胡爾巖從舞蹈創作心理學角度提出了 “非傳統式結構”理論。她闡述道,“非傳統式結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不受傳統的戲劇式結構規律的限制,不強調故事情節的完整性,不依據故事情節發展線索進行場次安排,而是以人物的內心活動為依據進行場次或舞段的安排,強調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多方面開掘與表現。”④ 這一理論觀點無疑為 “心理敘事”形態舞劇的創造發展提供了最好的注腳。此時在實踐領域,也確實創作出一批具有上述敘事特征的優秀舞劇。具有代表性的舞劇有舒巧創作的 《紅雪》《玉卿嫂》《胭脂扣》 《三毛》 《青春祭》,以及應萼定創作的 《女祭》 《誘僧》 《倩女幽魂》 《如此》等。胡爾巖就 《玉卿嫂》曾評論道: “舒巧舞劇 《玉卿嫂》作品具有感染觀眾的人物內心展示,在舞劇心理結構樣式上,做了開辟性的創作探索。”⑤ 雖說舒巧、應萼定二人舞劇創作的構成方式不盡相同,但大概由于他們之前有著多年的合作關系,因此對于結構舞劇的理念還是相當一致的,即:以心理動機為推進劇情發展的動力。與此觀點如出一轍的還有門文元、鄧一江以及與舒巧在精神上達成某種默契的 “現代舞” 編導王枚。門文元創作的舞劇 《阿炳》, “摒棄講故事、交代情節的陳舊的創作思維方式,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開掘和揭示人物內心深處最隱秘、最真實的情感上來”;鄧一江創作的《情殤》, “關注的不是 ‘戲劇性’賴以發生的 ‘環境沖突’,而是 ‘戲劇性’的 ‘心境較量’”;而 王 枚 創 作 的 《雷 和 雨》,則 是 “做了人物深層心理的剖析,使我們看到一部 ‘心理現實主義’的 ‘現代舞劇’”。⑥ 以 “心理敘事”形態進行舞劇結構,其優勢還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可以運用內心直視的手法,深入到人物的內心,當然也就避免了忽視人物內心表現的非舞劇化弊病。
“心理敘事”形態外,此時期也還有一些采用 “交響敘事”形態創作的舞劇,但是在敘事上出現了一些革命性的變化,表現為更加追求 “虛與實結合、心理描寫與劇情發展結合”的特征,如周培武等創作的 《阿詩瑪》、肖蘇華創作的 《陽光下的石頭———夢紅樓》、陳維亞創作的 《大夢敦煌》、張建民創作的 《二泉映月》等。另外,還有一個編導不得不提及,那就是蜚聲中國舞壇的張繼鋼。張繼鋼可謂是量多質高的舞蹈編導,他早期的舞蹈作品如 《獻給俺爹娘》 《俺從黃河來》《黃土黃》 《一個扭秧歌的人》 《好大的風》等奠定了業內至高的地位,而其創作的舞劇 《野斑馬》 《花兒》及后來的 《千手觀音》《一把酸棗》也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當然,他的舞劇敘事手法也在不斷求索中得以多元化,直至 《千手觀音》所采用的 “格式塔”編舞理念,更是開掘了 “心靈的可舞性”。于平在文章中寫道: “舞劇 《千手觀音》 的 ‘舞蹈自覺’,不 是 一 般 意 義 上 的 ‘自覺地舞蹈’,而是舞蹈作為一種造型媒介 ‘直指心靈’的自覺,一種把內心的意念外化成可感形象的自覺,一種把內心的情操外化成可感情節的自覺,一種把內心的視像外化成可感動態的自覺……”① “當我們評價一部作品的優劣時,不能僅僅從結構樣式的 ‘新’ 或 ‘舊’上論成敗,而要看它是否深刻、生動、完整地同表現內容融為不可剝離的整體來進行綜合的評價。”② 胡爾巖如是說。這些優秀創作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舞劇敘事形態的不斷發展與變換,正是源于創作者們對敘事規律的不斷探索。
與 20世紀 80年代的舞劇敘事形態相比較就會發現,雖然這一時期的作品在敘事上仍然具有多元化特征,但是它們總體表現為更加注重情境的多重意蘊、性格的多重組合以及沖突的多重交織。即:能夠注意表現豐富的現代意識,塑造立體化的形象和深入解剖民族的社會文化心理。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因為沉迷于自由敘事的愉快而忽視了對人物整體形象的塑造和對故事意義的深掘,也有部分舞劇給觀眾造成了像是一篇淺顯的哲理性敘事文的印象。
四、以 “隱喻敘事”形態為代表的時期
何為 “隱喻”? “從經驗主義角度來看,隱喻是一種富有想象力的理性。它使人們能通過一種經驗來理解另一種經驗,通過賦予由經驗的自然維度結構化了經驗完形來創造連貫性。新的隱喻可以創造新的理解,從而創造新的現實。”③ 借鑒這一概念,21世紀以來,中國舞劇創作也開啟了 “隱喻” 敘事之路。
“隱喻敘事”形態的舞劇創作不再單以人物或相關事件為中心,而是著重于 “敘事視角”的靈活轉換和巧妙設置,如對其背景、情節、事件、時空進行提煉重組,根本目的在于 “引導出某種觀念目標或發人深思的主題”。事實上,對于 “隱喻敘事”這一創作理念的最先運用,應是 20世紀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在中國舞蹈創作界不遺余力推廣 “交響編舞”的肖蘇華,他在 1992年創作的舞劇《紅樓夢幻曲》中就已初露端倪。用肖蘇華自己的話說,這部舞劇 “首次擺脫了講原著故事而轉向自我表達,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借題發揮’。”④ 其實,這里的 “借題發揮” 就是 “隱喻”。而其在 2005年現代舞劇 《夢紅樓》及 2007年創作的現代芭蕾舞劇 《陽光下的石頭———夢紅樓》 (在 “交響敘事”中也有提及),更是直接將表達的焦點移向了現代青年的生存狀態,開創了我們在此文中所要表述的 “以一個概念去建構另一個概念” 的 “隱喻敘事”形態時期。而這一時期,也當仁不讓地成為中國舞劇創作最為蓬勃發展的時期,涌現出大批的代表性舞劇作品。例如韓真、周莉亞創作的 《杜甫》。這部舞劇沒有進行杜甫傳記的敘事,沒有設計情節因果的戲劇沖突,而是以體現杜甫一生偉大成就的詩歌進行架構,“提供了一個依托舞蹈本體展開舞劇敘事的契機”。① 這里特別需要提及,舞劇用了幻覺 (幻化出另外一個 “杜甫”)的手段去努力地開掘人物的內心。雖然幻覺中的 “杜甫”與敘事情節無關,但卻是一種具有精神內核的人文指代 (本我、超我的對抗與自我救贖),它讓舞劇在敘事層面上獲得一種更為飽滿的情緒與意蘊空間,也使整部舞劇形成一個相對完整且涵意深厚的隱喻體系,所寄托的是導演對人性的參悟和期望;還比如上海芭蕾舞團聘請德國導演帕特里克創作的芭蕾舞劇 《長恨歌》,其敘事結構是以 “夢” 為線索,通過 “入夢、夢尋、現實、入夢”這一倒敘并首尾呼應的形式講述了唐明皇與楊玉環的凄美愛情故事。此外,編導還從具體事物中剝離并抽象出來一個 “意象化”的人物——— “月宮仙子”,應該意在以她獨特的存在方式告誡眾生———相對于歷史的滾滾車輪,再刻骨銘心的愛情也終歸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朵小小浪花 (人類的命運走向)。這個意象化 “月宮仙子”,當然也是一種理性世界的隱喻和象征。在對上述作品進行敘事形態分析中,我們會發現,它們除了都采用 “幻化”人物的手法外,在空間結構上也都具有相同的特征,就如張萍所述:“采取空間結構方式的舞劇,在舞臺上不再受事件的順序、倒序還是插敘等時間秩序的規限 ……空間可以自如穿梭、并置、交織、疊套,但絕不隨意,舞劇結構的空間性取向唯一可參照的是舞劇敘事的邏輯。”② 而這一觀點最早可以追溯到胡爾巖提出的 “時空互化”理論,她說道:“人物的主觀意識活動可以任意穿插于現實性很強的場景之中;在時空關系上,打破現實生活中的時空順序,把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在一起,組成一種新的、人物的心理時空順序。”③ 總括而言,一部優秀的舞劇正是通過這種多層次的 (包括 “幻化”人物)、交錯重疊的復雜的手法,才能最終達成 “切中題旨”的 “隱喻敘事”目的。說到這里,筆者認為還有必要提及一部 “現象級”的舞劇——— 《永不消逝的電波》。對于這部被冠以 “首部諜戰”題材舞劇的敘事手法,編導之一周莉亞如是說:“舞劇采用時空上的敘事切割方法,在有些段落,本來有的畫面全部打碎、重組;有些用了倒帶,有些用了假定空間中的真實性,還有真實空間中的假定性。總之,用了非常多敘事上面的功能性的表現形式。”④ 可以說, 《永不消逝的電波》以自身為最恰切的實踐,為我們思索今后的舞劇創作該如何更好地敘事提供了絕佳契機。
總體說來,近年來以 “隱喻敘事”形態進行創作并且取得成功的舞劇作品可以說非常之多,除上述作品外,還有包括 《西施》《唐寅》 《沙灣往事》 《粉墨春秋》 《水月洛神》《梅蘭芳》 《塵埃落定》 《朱#》 《醒· 獅》 《大禹》 《天路》 《草原英雄小姐妹》《打金枝》 《趙氏孤兒》……同樣,它們的敘事手段也非常多樣化,影像交互、戲中戲,以及 “蒙太奇”手法多次運用等等,這些不僅讓舞劇敘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流暢與自由,也讓舞劇有了一種 “詩學性”的闡釋,從而進入更加深厚的哲學層次。當然,有探索就會有失誤,有些舞劇只顧探索新穎的敘事方式,甚至只為敘事方式的與眾不同,難免會出現 “形式與內容”本末倒置等問題。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編導們對于敘事方式上的探索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它不僅為舞劇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成果,更為舞劇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結 語
徐岱在其著作 《小說敘事學》 中提道: “在小說世界中,常態與異態,規范與超越永遠是一對矛盾,但其結果卻是藝術模式的自我更新于蛻變而不是退出歷史舞臺。”① 縱觀中國舞劇敘事形態從啞劇、交響、心理到隱喻的更迭演變,我們不難發現其規律與小說的演進相仿,也是常態與異態、規范與超越、模式與反模式之間的辯證運用。不妨說,一部中國舞劇敘事形態的發展演變史,也是一部中國舞劇發展的歷史。換言之,中國舞劇敘事形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邏輯,參與和建構了中國舞劇發展的歷史進程。我們堅信,中國舞劇敘事的探索之路還在繼續著!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