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dāng)前,我國的外語專業(yè)教學(xué)面臨著時代的巨大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已經(jīng)不能滿足國家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的需求。在此背景下,T字型人才培養(yǎng)問題成為外語教育界關(guān)注與討論的熱點問題。所謂T字型人才,即橫向上涉獵較廣,縱向上在某一領(lǐng)域具有較深造詣的人才,是一專多能,同時兼具廣博度和精專度的復(fù)合型人才。T字型人才的培養(yǎng),應(yīng)該從各地區(qū)、各高校的實際情況出發(fā),避免“大一統(tǒng)”和“一刀切”。在這方面,小語種專業(yè)進(jìn)行了探索,如德語界不僅在20世紀(jì)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養(yǎng)的問題,還在跨文化交際等領(lǐng)域多有嘗試。此外,德國高校雙主專業(yè)和一主兩輔的專業(yè)組合形式以及“柏林模式”更可為我國外語類特別是小語種T字型人才的培養(yǎng)提供有益的借鑒與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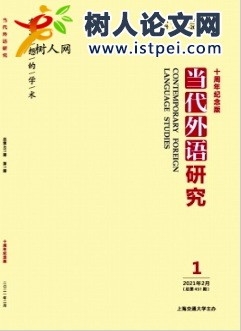
本文源自魏育青,當(dāng)代外語研究發(fā)表時間:2021-02-28《當(dāng)代外語研究》雜志,于1980年經(jīng)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zhǔn)正式創(chuàng)刊,CN:31-2039/H,本刊在國內(nèi)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學(xué)術(shù)爭鳴、語言學(xué)研究、翻譯研究等。
關(guān)鍵詞:小語種;外語人才培養(yǎng)模式;T字型人才
面對新時代的巨大挑戰(zhàn),外語專業(yè)的教學(xué)應(yīng)對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努力實現(xiàn)高質(zhì)量發(fā)展。傳統(tǒng)的人才培養(yǎng)可以概括為阿拉伯?dāng)?shù)字“1”字型的“專才”和漢字“一”字型的“通才”兩種類型。“專才”和“通才”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片面性也是明顯的,可能被人詬病為“書呆子”或“萬金油”:前者求專深,只涉一點,不及其余;后者偏廣博,面面俱到,不求甚解。相較于二者,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以其創(chuàng)新性引發(fā)了外語教育界的廣泛關(guān)注與思考。
德語界在20世紀(jì)末就提出了T字型人才培養(yǎng)問題。T字型人才是一專多能的復(fù)合型人才,兼具廣博度和精專度,最初探索復(fù)合是嘗試使核心專業(yè)與復(fù)合內(nèi)容有機結(jié)合,力求造就T字型人才,即橫向上涉獵較廣,縱向上在某一領(lǐng)域具有較深造詣的人才。但這絕非是提倡為了“泛讀”而丟掉“精讀”,通覽之外更須不斷鉆研,T字型人才應(yīng)該是釘子型人才。此后,沿著這一思路,又出現(xiàn)了關(guān)于π型人才和X型人才的討論。π型人才具有較大的覆蓋面,且兼通兩個領(lǐng)域,因此,比T型人才機會更多,適應(yīng)性更強。當(dāng)然,π型人才也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所謂“斜杠青年”。所謂X型人才,需較為系統(tǒng)地掌握兩門專業(yè),且這兩門專業(yè)之間要有顯著的交叉。X型人才與T型人才的區(qū)別在于更強調(diào)交叉,而不是突出博專廣精的結(jié)合。這一點倒是與之前德國大學(xué)的專業(yè)組合頗為類似。德語學(xué)術(shù)著作扉頁上的作者介紹中常常寫著其在某時某地攻讀過A專業(yè)、B專業(yè)、C專業(yè)等,這幾乎是德國高等教育的常態(tài)。在所謂“博洛尼亞進(jìn)程”之前,德國第一級學(xué)位(其實譯為“本科”或“碩士”都不合適)的專業(yè)組合有雙主專業(yè)和一主兩輔兩種類型。雙主專業(yè)與X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不無相似之處,一主兩輔則更接近于一般意義上的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上述人才培養(yǎng)模式之間雖然存在著一些差異,但其主要傾向大致相同,即不提倡金雞獨立,而主張多重適應(yīng),相得益彰。由此一來,就產(chǎn)生了一些問題留待我們思考與探討。
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有助于增強學(xué)生在就業(yè)市場上的競爭力和職業(yè)生涯中的靈活度,比如德語區(qū)的中學(xué)老師普遍能教幾門課,數(shù)專多能。此外,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在科研工作、學(xué)科發(fā)展等方面也不無裨益,有互補融合、觸類旁通之功效。創(chuàng)新的概念和構(gòu)想不少源自于其他領(lǐng)域,并且不僅僅是來自于臨近學(xué)科和相關(guān)專業(yè)。創(chuàng)新的火花往往是在交界處迸發(fā)出來的,這樣的例子在學(xué)術(shù)史上不勝枚舉。當(dāng)然,在這個意義上,也有人將T字型人才從負(fù)面評價為有廣度和深度,卻不善于創(chuàng)新,轉(zhuǎn)而強調(diào)要培養(yǎng)善于推陳出新、敢于向上冒尖的所謂“+”型人才。不過從廣義上說,以上提及的π型,X型、+型人才等,實際上都可以看成是T型人才的各種變體。
當(dāng)今世界的變化快速而劇烈,不確定性增加,人工智能等新技術(shù)的興起對高校外語專業(yè)形成了巨大的挑戰(zhàn),這些都對學(xué)生的知識系統(tǒng)、能力格局、素質(zhì)結(jié)構(gòu)等提出了新的要求。T字型人才培養(yǎng)實際上在相當(dāng)程度上符合新文科關(guān)于“堅持問題導(dǎo)向,打破學(xué)科壁壘,力求融合協(xié)同,促進(jìn)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理念。
外語專業(yè)要致力于中外文明互鑒和文明互譯,構(gòu)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話溝通,求同存異,兼顧引入和輸出。在這些方面,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更是顯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緊迫性與必要性。雖然在20世紀(jì)80年代我們就已經(jīng)在跨文化交際等領(lǐng)域有所嘗試,但現(xiàn)在更應(yīng)該銳化意識,增加強度。
我們討論外語專業(yè)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問題,也要適當(dāng)顧及一般人所說的“小語種”,即英語之外的其他通用語種和非通用語種。英語作為linguafranca,其交際功能無可替代,在不少人眼里,英語儼然就是外語的代名詞。相比之下,小語種的交際功能則是相當(dāng)受限的,在許多國際交流場合,默認(rèn)選項就是以英語溝通,以至于瓦爾特·本雅明一度成了沃爾特·本杰明,顧不上“名從主人”了;懷疑尼采著作、里爾克小說的漢譯有錯,卻以“英文原文”為勘誤的依據(jù)。這些都從側(cè)面表明了英語的無敵“霸權(quán)”。在全球化的進(jìn)程中,小語種的一般性交際功能似乎并不突出,其用武之地主要也不在傳遞一般信息的“實用”方面,而更多體現(xiàn)在對有關(guān)該語種的文學(xué)、文化、社會、歷史等學(xué)科知識的傳播,以及在該語言區(qū)特別發(fā)達(dá)、傳統(tǒng)悠久、影響巨大的領(lǐng)域的交流等方面。以德語區(qū)為例,在其哲學(xué)、音樂、古典學(xué)、宗教學(xué)、考古學(xué)、機械、化學(xué)、醫(yī)學(xué)等領(lǐng)域,使用德語進(jìn)行學(xué)習(xí)與交流至少與使用英語同樣重要。深層和精細(xì)的交流,尤其是涉及以上領(lǐng)域的深層和精細(xì)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離不開小語種的。將小語種的文化傳遞功能和英語作為linguafranca的交際功能結(jié)合起來,對小語種專業(yè)而言才是既有意義又具可行性的T字型人才培養(yǎng)的選項之一。
T字型人才的培養(yǎng),不可能是大一統(tǒng)型的,而應(yīng)該從各地區(qū)、各高校的具體情況出發(fā)。在這方面,德國二戰(zhàn)后影響頗大的所謂“柏林模式”頗有值得借鑒之處。柏林學(xué)派的教學(xué)論主張系統(tǒng)地考慮條件場和決斷場這兩大范疇的集合。所謂“條件場”,是指制約教學(xué)要素的現(xiàn)實狀況,通常教師對其是難以左右的,包括人類—心理前提(即與學(xué)生相關(guān)的所有因素,如個體特性、群體關(guān)系等)和社會—文化前提(即學(xué)校等機構(gòu)框架條件、文化環(huán)境,如政治、宗教、意識形態(tài)、科學(xué)等)。所謂“決斷場”,指的是教學(xué)過程中的基本結(jié)構(gòu)成分,這是教師在課堂教學(xué)中可以作出決斷的范圍,如目標(biāo)、內(nèi)容、方法、媒介等。“柏林學(xué)派”的教學(xué)論并未試圖理想主義地設(shè)計一本包羅萬象的教師手冊,而是努力建立理論分析的框架,究其原因在于教學(xué)并非預(yù)先設(shè)定的流水線生產(chǎn)過程,而是涉及人與人之間的、錯綜復(fù)雜的互動過程,猶如下棋,必須根據(jù)不同情況進(jìn)行增減取舍。教師并無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其最重要素質(zhì)的之一就是在了解各種可能性的基礎(chǔ)上酌情“決斷”的能力。這種因X制宜、實事求是的思路對T字型人才培養(yǎng)乃至其質(zhì)量指標(biāo)、評判標(biāo)準(zhǔn)的設(shè)定亦不無啟發(fā)。雖然難免聽到諸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結(jié)果什么也沒學(xué)好”之類的尖銳批評,但是,必須指出的是,T字縱橫兩條線各自的長度和濃度、涉及的廣度和深度要根據(jù)具體情況進(jìn)行制定和調(diào)整,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搞所謂的大一統(tǒng)式的理想主義。同時,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也有利于維護(hù)外語學(xué)科的生態(tài)多樣性,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總而言之,T字型人才的結(jié)合應(yīng)該是有機的,而不是拼湊的。核心素質(zhì)或稱關(guān)鍵素質(zhì)才是檢驗這種結(jié)合是否有效的試金石。橫向的寬度和縱向的深度體現(xiàn)了人才培養(yǎng)“高質(zhì)量”的程度,而核心素質(zhì)則是不可或缺的靈魂。國內(nèi)外的相關(guān)討論已經(jīng)開始涉及這一問題,如以上提到的+型人才培養(yǎng),還有所謂的“新T字型人才”或者“T字型人才2.0”等亦是如此。這些新的T字型人才培養(yǎng)模式突出了動態(tài)轉(zhuǎn)型,一方面繼承了傳統(tǒng)T字型人才寬而深、廣且精的培養(yǎng)模式,注重對實體層面知識和技能的扎實掌握;另一方面,則更加關(guān)注對其內(nèi)在素質(zhì)以及創(chuàng)新、突破、變革等意識和能力的養(yǎng)成與提高。雖然這當(dāng)中難免有些難以測量的非智力因素,但從總體上看,這一目標(biāo)的設(shè)定,無疑有益于我國現(xiàn)有外語人才特別是“小語種”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完善與提升。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