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與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境遇值得關(guān)注。本文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訪談尋親成功后的被拐兒童及其家鄉(xiā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成員,以生命歷程理論為指導(dǎo),揭示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化,考察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情況。研究發(fā)現(xiàn):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主要經(jīng)歷被拐、被收養(yǎng)、尋親與尋親成功 4 個(gè)重大生命事件。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主要有主動(dòng)融入型、自主選擇型與猶豫隔離型 3 種。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所遭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與家庭網(wǎng)絡(luò)成員的社會(huì)反應(yīng)對(duì)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具有重要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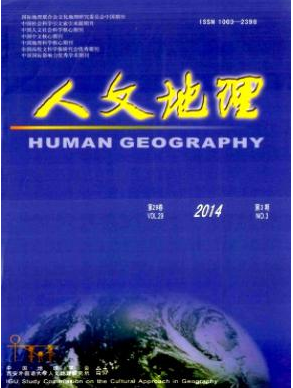
本文源自薛淑艷; 李鋼; 王會(huì)娟; 付瑩; 劉玲, 人文地理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6-15
關(guān)鍵詞:被拐兒童;尋親成功;生命歷程;原生家庭融入
1 引言
拐賣兒童犯罪極大威脅著公民人身權(quán)利與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一直是世界各國(guó)關(guān)注的社會(huì)熱點(diǎn)問題。1990 年聯(lián)合國(guó)兒童基金會(huì)將拐賣兒童犯罪確定為一項(xiàng)世界各國(guó)協(xié)同合作治理的重大國(guó)際問題,倡導(dǎo)近 30個(gè)國(guó)家簽署 《巴勒莫議定書》,旨在提升國(guó)際兒童保護(hù)合作的深度和力度。在我國(guó),拐賣兒童犯罪自古有之,雖經(jīng)多次打擊,仍十分猖獗,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統(tǒng)計(jì)全國(guó)各級(jí)法院共審結(jié)拐賣婦女、兒童犯罪案件 7719 件。隨著社會(huì)各界對(duì)拐賣兒童犯罪的日益重視,相關(guān)防拐與反拐的政策也持續(xù)得到貫徹實(shí)施,但目前聚焦點(diǎn)仍停留在解救被拐兒童與提升拐賣兒童犯罪破案率上,針對(duì)被拐兒童群體返鄉(xiāng)后的原生家庭融入問題關(guān)注較少。
目前,學(xué)術(shù)界針對(duì)拐賣兒童犯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5個(gè)方面:①重視拐賣兒童犯罪法律的完善與量刑。國(guó)外學(xué)者認(rèn)為加強(qiáng)國(guó)際合作和加強(qiáng)立法可有效抑制該犯罪[1],且在公共場(chǎng)所張貼人口販運(yùn)熱線電話可有效預(yù)防人口販運(yùn)[2]。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提出應(yīng)對(duì)“出賣親生子女”罪加以界定[3],對(duì)“勞役被拐兒童”行為應(yīng)加重量刑[4];同時(shí)修改關(guān)于收買犯罪的 “但書”免責(zé)條款,對(duì)“可以不追究刑事責(zé)任”這一立法表述進(jìn)行限制性解釋[5]等措施以抑制拐賣犯罪。②探討拐賣兒童犯罪的特點(diǎn)與變化。國(guó)外更關(guān)注跨國(guó)販賣兒童,以討論販賣女童到性交易場(chǎng)所和販賣兒童為勞工的較多[6,7],并指出常遭受虐待和離家出走的兒童被販賣后遭受虐待的可能性更大[8]。國(guó)內(nèi)學(xué)者則發(fā)現(xiàn)中國(guó)拐賣兒童犯罪呈現(xiàn)農(nóng)村向城鎮(zhèn)、個(gè)體向集團(tuán)與國(guó)內(nèi)向國(guó)外發(fā)展的特點(diǎn)[9],且近年來熟人作案尤其是“親生親賣”現(xiàn)象較為明顯[10]。③解析拐賣兒童犯罪的時(shí)空特征。該類研究國(guó)內(nèi)較多,如部分學(xué)者[11]發(fā)現(xiàn) 20 世紀(jì) 80 年代至 21 世紀(jì)初是中國(guó)拐賣兒童犯罪的高發(fā)期,貴州至福建是拐賣兒童犯罪的高發(fā)路徑;隨著時(shí)間變化拐賣兒童犯罪呈現(xiàn)由東南沿海向西南地區(qū)轉(zhuǎn)移的特征[12];在國(guó)內(nèi),四川和河南分別為兒童的凈販出地和凈販入地,被販賣的兒童主要從西部流向了中東部[13];同時(shí),收買方也具有較強(qiáng)的性別偏好,華南地區(qū)傾向于收買男童,河北、河南和浙江傾向于收買女童,同一省內(nèi)男童的被拐風(fēng)險(xiǎn)高于女童[14]。④探究拐賣兒童犯罪的根源與形成機(jī)制。國(guó)外學(xué)者認(rèn)為極度貧困[15,16]和高生育率[17]是造成兒童被拐的重要因素。國(guó)內(nèi)學(xué)者提出兒童被拐與計(jì)劃生育政策[18-21]、拐賣方的僥幸心理[22]、被拐兒童監(jiān)護(hù)人的疏忽大意、城市化進(jìn)程的加快與流動(dòng)人口的增多有關(guān)[23]。同時(shí),李鋼等[24]提出可用“推— 拉”模型來解釋拐賣兒童犯罪,并指出區(qū)域地理環(huán)境、經(jīng)濟(jì)、文化、政策等方面的“梯度”差異對(duì)其具有重要影響。⑤討論被拐兒童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與社會(huì)救助。該類研究國(guó)外較多,側(cè)重于對(duì)兒童被拐后所面臨的身體、心理和健康方面風(fēng)險(xiǎn)的研究[25],以及從醫(yī)學(xué)、社會(huì)和家庭等方面提出相應(yīng)的救助方案[26]。綜合來看,當(dāng)前學(xué)術(shù)界對(duì)被拐兒童在尋親成功后是否返鄉(xiāng),返鄉(xiāng)后如何重新融入原生家庭與社會(huì),以及后期人文關(guān)懷等問題的研究較為缺乏,因此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身心發(fā)展困境與原生家庭融入研究亟需開展。
近年來,生命歷程理論以個(gè)人年齡增長(zhǎng)發(fā)生的不同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duì)個(gè)體影響的研究廣受學(xué)者關(guān)注。該理論于20世紀(jì)20年代萌芽,歷經(jīng)百年發(fā)展已在國(guó)外形成為相對(duì)成熟的理論。在國(guó)內(nèi),李強(qiáng)等[27]引介生命歷程理論,就其在西方的歷史發(fā)展、分析范式、理論應(yīng)用等問題進(jìn)行了綜述。目前,運(yùn)用生命歷程理論針對(duì)弱勢(shì)群體的研究較為普遍,如學(xué)者們利用該理論剖析了老年人、婦女、留守兒童、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人口等的生命歷程變遷[28,29],解析重大事件對(duì)個(gè)人生命軌跡的塑造和負(fù)向生命事件對(duì)個(gè)人生命軌跡的影響等。被拐兒童亦屬于弱勢(shì)群體范疇,其被拐賣、開始尋親、尋親成功等這些重大生命事件對(duì)其生命軌跡具有重要影響,但目前鮮見運(yùn)用該理論對(duì)被拐兒童的研究。
鑒于此,本文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訪談尋親成功后的被拐兒童及其家鄉(xiā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成員,以生命歷程理論為指導(dǎo),分析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與原生家庭融入情況,并提出對(duì)策建議,為我國(guó)兒童安全環(huán)境改善、家庭社會(huì)和諧穩(wěn)定及制定犯罪防控策略與人文關(guān)懷方案提供參考。
2 理論與方法
2.1相關(guān)理論
生命歷程理論最早源于生活史研究,是指?jìng)€(gè)體在一生中按照社會(huì)規(guī)定不斷扮演的角色和事件,且這些角色和事件是按年齡順序進(jìn)行排列的[30]。生命歷程理論有4個(gè)主要原則:一是時(shí)間與空間,即一個(gè)人的生命軌跡與其所出生的歷史時(shí)代與地域空間密切相關(guān);二是相互依存的生命,即個(gè)體并非獨(dú)立存在,其生活鑲嵌于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且注定要受別人的生命歷程中所發(fā)生的生活事件的影響;三是生命的時(shí)間性,即個(gè)人生命事件的發(fā)生時(shí)間會(huì)嚴(yán)重影響到個(gè)人的生命歷程軌跡,生命事件發(fā)生時(shí)間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事件本身;四是個(gè)人能動(dòng)性,即個(gè)體除了受到所生活的社會(huì)歷史時(shí)期的結(jié)構(gòu)性因素的影響外,個(gè)體能動(dòng)性作用和自我選擇對(duì)自己的生命歷程軌跡也有重要的影響[31]。本文以生命歷程理論為指導(dǎo),構(gòu)建被拐兒童的長(zhǎng)期空間行為生命路徑,以實(shí)現(xiàn)對(duì)被拐兒童生命歷程與原生家庭融入境況的全面理解。
2.2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個(gè)案研究法對(duì)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進(jìn)行梳理,識(shí)別影響被拐兒童生命歷程變遷的重大生命事件及其對(duì)尋親成功后與原生家庭融入的關(guān)系。基于“寶貝回家(https://www.baobeihuijia.com) ”網(wǎng)站中尋親成功案例數(shù)據(jù)庫(kù),經(jīng)過多方聯(lián)系與多次嘗試最終聯(lián)系到5個(gè)愿意接受訪談的被拐兒童,并分別于2015年7月、2016年6月與2018年1 月對(duì)被拐兒童 (表 1) 及其家鄉(xiā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成員 (表 2) 開展了實(shí)地調(diào)查與電話訪談。訪談的 5 名被拐兒童 (男性 3 名,女性 2名) 年齡均在 30歲左右,被拐時(shí)長(zhǎng)在 25年左右。資料收集采用以筆錄為主、音頻與視頻為輔的方式,所有的個(gè)案均進(jìn)行了化名處理。而且為了清晰呈現(xiàn)被拐兒童生命歷程的變遷與原生家庭融入,以常用的生命故事訪談法展開訪談 (雖然受訪者已經(jīng)長(zhǎng)大成人,但是下文仍以被拐兒童相稱)。
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無意探討有關(guān)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上的總體性推論,而是通過“過程—事件”的邏輯順序,突出被拐兒童在經(jīng)歷“被拐”等一系列重大生命事件后生命歷程軌跡的變化,從而呈現(xiàn)這些生命事件對(duì)于其生命歷程變化的影響,進(jìn)而探究被拐兒童在尋親成功后與原生家庭的融入狀態(tài),以及“被拐”等一系列生命事件與其原生家庭融入的關(guān)系,希望能夠引起相關(guān)學(xué)者、公眾或部門的關(guān)注。
3 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
個(gè)體生命歷程變遷必然是一個(gè)軌跡的變化過程,在這個(gè)過程中,會(huì)經(jīng)歷一種狀態(tài)到另一種狀態(tài)的轉(zhuǎn)變和某一行為或傾向的延續(xù)[32]。受訪的5個(gè)被拐兒童生命歷程中的重大生命事件較為相似,在時(shí)間序列上主要表現(xiàn)為“被拐”“被收養(yǎng)”“尋親”與“尋親成功”4 個(gè)事件 (圖 1)。將這 4 個(gè)重大生命事件嵌入歷史時(shí)間、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與個(gè)人生命史中,根據(jù)變動(dòng)環(huán)境產(chǎn)生的影響來探討其生命軌跡的變遷。
3.1 被拐
時(shí)間與空間是生命歷程理論中的重要原理,兒童“被拐”正是在特定的時(shí)間與空間下發(fā)生的,在這個(gè)特定的時(shí)間與空間中,受犯罪人“實(shí)施拐賣犯罪”事件的影響,直接導(dǎo)致兒童“被拐”,從而使得兒童的整個(gè)生命軌跡與同齡人相比發(fā)生重大變化,進(jìn)而促進(jìn)了后續(xù)“被收養(yǎng)”“尋親” “尋親成功”等一系列重大生命事件的發(fā)生。從兒童被拐的時(shí)間來看,被拐年份分布在 1987—1994 年間,進(jìn)一步來分析其“被拐”的原因,發(fā)現(xiàn):①該時(shí)間段正是中國(guó)拐賣兒童犯罪的高發(fā)期[33],受計(jì)劃生育政策多變性與嚴(yán)苛性的影響,人們傳統(tǒng)觀念下的“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等生育意愿無法得到滿足,從而衍生出龐大的收買兒童市場(chǎng),進(jìn)而刺激了拐賣犯罪的發(fā)生[34]。②在社會(huì)層面,該時(shí)期收養(yǎng)制度的不盡完善與防拐宣傳的不到位,在催生了非法收養(yǎng)的同時(shí)加劇了兒童的被拐風(fēng)險(xiǎn);同時(shí),由于社會(huì)就業(yè)政策和社會(huì)保障體系的不成熟,致使許多流動(dòng)人口與失業(yè)人員將實(shí)施拐賣作為謀生手段。③在個(gè)體層面,于兒童而言,群體弱勢(shì)性使其成為可交換的“商品”,且由于年齡小辨識(shí)能力弱,對(duì)于陌生人毫無防范之心,易輕信他人和被誘騙,如張某、曲某和楊某正是由于犯罪分子的食物誘騙而被拐賣。對(duì)監(jiān)護(hù)人來說,受家庭情況與文化程度等差異化的影響,使其對(duì)兒童的監(jiān)管存在一定疏漏,間接導(dǎo)致兒童被拐;從犯罪分子來看,受家庭貧困、文化程度低、缺乏謀生謀利技能等的影響,使其認(rèn)為拐賣兒童是“高成本、低風(fēng)險(xiǎn)”的工作,甚至是一種“濟(jì)貧”“做好事”的方式,從而促進(jìn)了拐賣兒童犯罪的發(fā)生。
我生了兩個(gè)丫頭人家就不讓生了,人家都有男娃……我在村里抬不起頭,說我生不出男娃,我男人就說那買一個(gè)吧。(收養(yǎng)家屬)
村里面沒有人管這個(gè)事情,更沒有宣傳過什么防拐,大家都是自己看自己的孩子,而且村里面對(duì)這些事情也不是很上心,對(duì)孩子都是放養(yǎng)。(原生家屬)
我當(dāng)時(shí)在火車道路邊與小伙伴捉知了時(shí)被人帶走。當(dāng)時(shí)一起去的有一個(gè)小伙伴和我表哥,人販子先把我的那個(gè)小伙伴抱走了,但他又從車子上溜了下來,然后人販子將我抱上車子,給了我好多零食,我就跟著走了,沒想到就被拐了。(張某)
被拐時(shí)是星期天,傍晚的時(shí)候我一個(gè)人回家。路上遇到一男的,他說叔叔給你買玉米棒,我就跟他走了。后來,人販子用麻袋把我裝起來,帶上火車,不記得火車坐了多久。(曲某)
當(dāng)時(shí)家里就我一個(gè)人,家里人都出去了,我自己在外面玩,后來來了一個(gè)人,給我買零食吃,我就跟著他走了。后來就到了一個(gè)陌生的地方,我想跑,可是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家在哪里。(楊某)
個(gè)體的存在并非獨(dú)立,而是鑲嵌于具體的社會(huì)關(guān)系中,其生命軌跡的變遷也會(huì)影響社會(huì)關(guān)系中他人生命軌跡的變化。通過對(duì)被拐兒童的深入了解,發(fā)現(xiàn)兒童被拐對(duì)原生家庭的影響最大,兒童被拐給原生家庭造成了巨大打擊,家庭結(jié)構(gòu)和家庭成員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①妻離子散型。即因孩子被拐賣刺激了家庭內(nèi)部矛盾,外加部分家庭成員意志堅(jiān)定常年在外尋找孩子,致使家庭內(nèi)部破碎瓦解。②家庭成員因受過度刺激而患病型。如張某的母親,在其被拐后長(zhǎng)年思子心切,導(dǎo)致精神異常;曲某的母親,在其被拐后憂思成疾,最終抱憾離世。
聽說我媽在我被拐賣后精神出現(xiàn)了問題,老是對(duì)著別的小孩喊我的名字。(張某)
最重要的是,媽媽已經(jīng)不在了,是因我。(曲某)
找到母親之后,才知道他和我父親已經(jīng)離婚了,現(xiàn)在還沒找到父親。(魚某)
3.2 被收養(yǎng)
已有研究表明,兒童被拐后的去向有被收養(yǎng)、強(qiáng)迫婚姻、勞動(dòng)力剝削、性剝削、乞討盜搶工具和器官移植等,但以“被收養(yǎng)”為最。本文所訪談的被拐兒童去向均為 “被收養(yǎng)”,因此本文著重討論“被收養(yǎng)”這種被拐去向。受“養(yǎng)兒防老”“多子多福”與“結(jié)婚難”境況下的剛性需求,許多家庭去收買兒童,迫使兒童商品化,進(jìn)而導(dǎo)致越來越多的兒童被拐,可以說兒童被拐本質(zhì)上受收養(yǎng)家庭收買意愿的影響,而收養(yǎng)家庭的收買意愿則與所處的社會(huì)背景、歷史因素與個(gè)人生育偏好有關(guān),已在前文進(jìn)行了闡述。
兒童在“被收養(yǎng)”后從原生家庭轉(zhuǎn)入收養(yǎng)家庭,生活的時(shí)間與空間發(fā)生變化,從而導(dǎo)致其面臨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景觀與擁有的生活機(jī)會(huì)、權(quán)力和回報(bào)等也發(fā)生變化[35]。從被調(diào)查的5個(gè)案例來看,被拐兒童的收養(yǎng)家庭存在顯著差異,主要表現(xiàn)為兩類:一為良好型收養(yǎng)家庭,即有完整的家庭功能與結(jié)構(gòu),能夠給予被拐兒童與親生子女同等待遇,被拐兒童能夠享有基本的生存權(quán)、受保護(hù)權(quán)、發(fā)展權(quán)、參與權(quán)的收養(yǎng)家庭。如張某、曲某和魚某的第二任養(yǎng)家,三者的收養(yǎng)家庭結(jié)構(gòu)較為完整,在收養(yǎng)家庭中能夠獲得家庭成員的愛護(hù)與接受教育的機(jī)會(huì),其被收養(yǎng)的家庭為良好型家庭。
我養(yǎng)父母對(duì)我算是視如己出了,我在養(yǎng)父母家里還有兩個(gè)姐姐,由于家里條件困難,他們都早早的出去打工,來供我讀書,讓我順利的讀完大學(xué),是真心的感激。(張某)
養(yǎng)父母家里就我一個(gè)孩子,對(duì)我很好,這也是我在尋找親生父母時(shí)一直猶豫的原因,他們給了我接受教育的權(quán)利。在心底里還是很感謝我的養(yǎng)父母的。(曲某)
這是我的第二任養(yǎng)父母,養(yǎng)父是一位教師,他們對(duì)我的關(guān)愛讓我有了家的感覺。我小時(shí)候都很自卑,一直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人。是在養(yǎng)父母的幫助下,才一點(diǎn)點(diǎn)敞開心扉的。(魚某)
反之為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被拐兒童在被收養(yǎng)家庭中無法獲得基本的生存、受保護(hù)、發(fā)展與參與的權(quán)利,不能享受在原生家庭中所擁有的愛與呵護(hù),并在一定程度上會(huì)遭受身體、心理等的傷害。如楊某、肖某和魚某的第一任收養(yǎng)家庭均屬于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家庭功能相對(duì)缺失,被拐兒童不能享有同齡人應(yīng)該享有的愛護(hù)和關(guān)心,且經(jīng)常遭受虐待和毒打,對(duì)其心理造成嚴(yán)重創(chuàng)傷。
我一直都不想留在養(yǎng)父家里,感覺很壓抑。他們對(duì)我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想早點(diǎn)出去,自己賺錢,尋找親生父母。(楊某)
第一個(gè)養(yǎng)父酗酒嚴(yán)重,總在酒后打媽媽和我,感覺那段時(shí)間很灰暗。(魚某)
在養(yǎng)父母家里,總會(huì)因?yàn)楦鞣N事情被養(yǎng)父打,我一個(gè)人偷偷躲在被窩里哭的時(shí)候,便開始想象自己的親生父母是什么樣,會(huì)不會(huì)對(duì)我更好。(肖某)
3.3 尋親
“尋親”是被拐兒童生命歷程中經(jīng)歷的第三個(gè)重大生命事件,被拐兒童的被拐經(jīng)歷和在收養(yǎng)家庭中的生活狀態(tài),激發(fā)了他們的個(gè)體能動(dòng)性和自我選擇性,進(jìn)而開始主動(dòng)尋親。其主動(dòng)尋親的原因有二:一是血緣親情促使他們主動(dòng)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二是由于收養(yǎng)家庭的遭遇使他們更向往回到原生家庭,期望能得到更好的生活條件和家人的關(guān)心與愛護(hù)。同時(shí),我們也發(fā)現(xiàn),被拐兒童的尋親與外出工作是相結(jié)合并行的,其外出工作的原因主要有3種:①因?qū)びH而工作型:尋親是尋找工作最主要的因素,往往所選工作地離親生父母較近。如張某為了方便尋親畢業(yè)后選擇到洛陽工作。②因逃避而工作 (尋親) 型:逃避現(xiàn)有生活環(huán)境,找尋一個(gè)無人認(rèn)識(shí)的地方重新開始。如曲某本來對(duì)去廣州工作心存忐忑,但出于心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逃避,還是選擇去外地重新開始,重獲自由。③因謀生而工作 (尋親) 型:由于在收養(yǎng)家庭遭受虐待,以外出打工作為自我獨(dú)立、自我謀生手段,并且尋找親生父母。如楊某由于在收養(yǎng)家庭常遭虐待,所以想遠(yuǎn)離傷心之地,自己賺錢立足社會(huì)。
畢業(yè)后選擇到了洛陽工作,也是知道親生父母在陜西,想著能離他們近一點(diǎn),方便自己尋找他們。(張某)選擇去廣州打工也是很糾結(jié)的,又要到一個(gè)完全陌生的城市,心里還是有忐忑。可是,很想去到一個(gè)沒人認(rèn)識(shí)自己的地方,這里不會(huì)有人知道自己拐賣身份的地方,也不會(huì)有人對(duì)我格外關(guān)心,不會(huì)有人對(duì)我有什么看法,這樣的生活更加很輕松,也算是自由了吧。(曲某)我一直都不想留在養(yǎng)父家里,感覺很壓抑。他們對(duì)我也不是很好,所以就想早點(diǎn)出去,自己賺錢,尋找親生父母。(楊某)
被拐兒童在收養(yǎng)家庭中的生活狀況對(duì)其個(gè)人能動(dòng)性的發(fā)揮和自我選擇也具有重大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良好型收養(yǎng)家庭對(duì)于被拐兒童尋找工作具有正向引導(dǎo)和積極促進(jìn)作用,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對(duì)于被拐兒童尋找工作具有負(fù)向作用。如張某在 23歲讀完大學(xué)后去工作,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他具有良好的三觀,對(duì)自己未來有詳細(xì)且合理的規(guī)劃,因此他選擇了既可以照顧養(yǎng)父母也可以尋找親生父母的地點(diǎn)工作。而曲某和楊某都形成了回避型性格,一直介意自己的被拐賣身份,因此曲某一直在外地打工常年不回家,楊某則處于逆反心理最強(qiáng)的時(shí)期,對(duì)社會(huì)的敵意、周圍人的怨懟致使他走上犯罪的道路。
3.4 尋親成功
被拐兒童在被拐后經(jīng)歷的第四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為尋親成功,即找到親生父母。從受訪者的情況來看,尋親時(shí)長(zhǎng)最短為2 年,最長(zhǎng)為 24年。尋親時(shí)間在 1998—2014年間者,開始尋親的時(shí)間越早,尋親成功的時(shí)間跨度越長(zhǎng)。將被拐兒童的尋親成功置于歷史時(shí)間中,來探究其尋親成功的早晚與時(shí)代背景的關(guān)系,可以發(fā)現(xiàn)早期被拐兒童救助以公安部門為主,且在20世紀(jì)90年代至21世紀(jì)初,其他類型犯罪大幅增加,公安部門警力有限,難以在較短時(shí)間幫助其尋親。后隨著拐賣兒童犯罪的越發(fā)猖獗,在中國(guó)民間興起了以“寶貝回家”(2005年創(chuàng)立) 為代表的公益尋親組織,越來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其中幫助尋親;且隨著網(wǎng)絡(luò)通訊技術(shù)的發(fā)展,大量被拐兒童家庭與被拐兒童開始上網(wǎng)登記被拐信息,從而為被拐兒童與被拐兒童家庭創(chuàng)造了均等的時(shí)空對(duì)接機(jī)會(huì),進(jìn)而縮短了尋親成功的時(shí)間。從社會(huì)層面來看,人們的打拐防拐意識(shí)逐漸增強(qiáng),且具有較強(qiáng)的社會(huì)同理心,因此真心愿意幫助尋親的志愿也較多,進(jìn)而提高了尋親成功的幾率。從個(gè)人來看,被拐兒童的個(gè)人能動(dòng)性是推動(dòng)尋親成功的重要因素,尋親之路雖艱難坎坷,但被拐兒童們從未放棄,血濃于水的親情使他們堅(jiān)持不懈的奔走在尋親之路上,直至最后的尋親成功。
尋親之路真的很辛苦啊,五年之后我才找到我的親生父母。(張某)我一直想找我的親生父母,只是在零三年的時(shí)候我才開始,找到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是一四年了。(曲某)尋找父母真的是很艱難,還好我沒有放棄,過了 19 年我才找到(親生父母)。(魚某)
在尋親成功后,被拐兒童將會(huì)面臨是否回歸原生家庭的選擇。從受訪的被拐兒童可以發(fā)現(xiàn),因被拐后的經(jīng)歷各不相同,各自的選擇也相對(duì)不同 (詳見下述)。
被拐兒童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重大生命事件后,由于其所處的時(shí)空環(huán)境與所擁有的環(huán)境景觀發(fā)生變化,對(duì)被拐兒童的心理都將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害,主要表現(xiàn)為:①自我認(rèn)同感削弱:表現(xiàn)為懼怕自己的身世暴露以及具有較深的自卑感。如曲某不愿被人談?wù)撍还盏氖聦?shí),怕別人對(duì)自己格外關(guān)心,對(duì)自己有“別的”看法。同時(shí),通過對(duì)其它諸多被拐兒童案例的分析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被拐兒童被拐后明顯比正常兒童更容易自卑。②負(fù)面情緒擴(kuò)張:表現(xiàn)為對(duì)社會(huì)的反抗與敵意較大,易誤入歧途。如楊某因缺乏自我謀生手段鋌而走險(xiǎn)去偷盜。③負(fù)性生命事件下的安全感降低:表現(xiàn)為懼怕一些經(jīng)歷過得不好的、對(duì)心理造成創(chuàng)傷的事。如魚某由于在第一任收養(yǎng)家里遭受虐待,所以總害怕喝酒的人,害怕吵架、害怕激烈的事。同時(shí),我們也可以看出,良好型的收養(yǎng)家庭可以撫慰心理創(chuàng)傷,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會(huì)加劇被拐兒童的心理傷害。
很想去到一個(gè)沒人認(rèn)識(shí)自己的地方,這里不會(huì)有人知道自己拐賣身份的地方,也不會(huì)有人對(duì)我格外關(guān)心,不會(huì)有人對(duì)我有什么看法,這樣的生活更加很輕松,也算是自由了吧。(曲某)我中間因?yàn)橐淮瓮当I,還坐過牢,感覺很對(duì)不起父母。(楊某)我到現(xiàn)在還是很害怕喝酒的人,害怕他們耍酒瘋,也害怕吵架,害怕打架,總之害怕一切激烈的事物。我小時(shí)候都很自卑,一直覺得自己是被拋棄的人。(魚某)
4 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
4.1原生家庭融入類型
本文的原生家庭融入借鑒了社會(huì)融入[36]的概念,是指特殊情境下的社會(huì)群體,融入原生家庭關(guān)系網(wǎng)當(dāng)中,能夠獲取正常的經(jīng)濟(jì)、關(guān)愛、身份認(rèn)同、社會(huì)關(guān)系等資源的動(dòng)態(tài)過程或狀態(tài)。被拐兒童在尋親成功后往往面臨著收養(yǎng)家庭與原生家庭的兩重選擇,受其在重大生命事件下不同生活狀況的影響,其與原生家庭的融入表現(xiàn)為三類:主動(dòng)融入型、自主選擇型與猶豫隔離型。
4.1.1主動(dòng)融入型
主動(dòng)融入型是指被拐兒童愿意回歸原生家庭,基本成功的融入到原生家庭中。影響該融入類型的因素主要有三個(gè):一是惡劣型的收養(yǎng)家庭。被拐兒童在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難以獲得生存與生活的權(quán)利,更難獲得長(zhǎng)足發(fā)展與參與的權(quán)利,他們更渴望獲得心理支持與情感歸宿,因此當(dāng)尋親成功后,他們迫切想融入原生家庭以改變現(xiàn)有社會(huì)關(guān)系,從而實(shí)現(xiàn)心理與情感的融入。②當(dāng)前糟糕的生活狀態(tài)。處于不穩(wěn)定生活狀態(tài)的被拐兒童受當(dāng)前生活條件的限制難以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而原生家庭將為其提供新的生活環(huán)境與社會(huì)關(guān)系,幫助其更好的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③家鄉(xiā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成員積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通過對(duì)被拐兒童家鄉(xiāng)網(wǎng)絡(luò)成員的訪談,發(fā)現(xiàn)“欣喜”“欣慰”“開心”等積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在對(duì)待被拐兒童返鄉(xiāng)的態(tài)度上更為和善和包容,對(duì)被拐兒童融入原生家庭具有正向的積極影響。
現(xiàn)在,我和父母回家了,感覺有了父母的陪伴生活也有了希望。……跟著父母做一點(diǎn)小生意,還能生活下去。跟著父母在一起,還能享受一下他們的關(guān)愛,這是我一直渴望的。我也不是很想讓他們失望,想盡我的能力更多的陪伴他們,也能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楊某)孩子回來的時(shí)候家里面大擺酒席,就是慶祝孩子找到回來了。我們也為這家人高興的,二十多年了,終于找回來了。(村民1)我們作為鄰居,看著他們找孩子找了這么多年,真是不容易,都是做父母的人,也是佩服他們能堅(jiān)持這么多年。現(xiàn)在孩子回來了,也真心為他們高興。(鄰居3)
4.1.2 自主選擇型
自主選擇型是指被拐兒童在與原生家庭的融入上具有個(gè)別性,即在不同的時(shí)間與空間實(shí)現(xiàn)短暫性的融入,該融入類型的主要目的是平衡原生家庭、收養(yǎng)家庭與被拐兒童自我家庭之間的關(guān)系。主要受良好型的收養(yǎng)家庭和當(dāng)前良好生活狀態(tài)的影響。①良好型的收養(yǎng)家庭中家庭結(jié)構(gòu)與功能較為完整,被拐兒童與正常兒童享有同等的愛與呵護(hù),因此在心理上他們難以割舍收養(yǎng)家庭而去融入原生家庭,進(jìn)而促使他們選擇在不同的時(shí)間與空間短暫性融入,以達(dá)到維持收養(yǎng)家庭與原生家庭平衡的目的。如張某在收養(yǎng)家庭獲得了與原生家庭同等的權(quán)利,因此他選擇既不離開收養(yǎng)家庭又去照顧原生家庭。②當(dāng)前良好的生活狀態(tài)使得兒童難以隔離現(xiàn)有的社會(huì)關(guān)系,雖然在心理上已經(jīng)主動(dòng)融入原生家庭,但在社會(huì)交往層面無法完全融入,因此以自主選擇融入來平衡原生家庭與自我家庭之間的關(guān)系。如肖某由于目前的工作與生活環(huán)境已相對(duì)成熟穩(wěn)定,且現(xiàn)居地與原生家庭較遠(yuǎn),因此選擇在現(xiàn)居地生活。
目前,還沒有回到父母身邊的打算。養(yǎng)父母一家對(duì)我非常好,養(yǎng)父已經(jīng)去世,姐姐們都已經(jīng)出嫁了,養(yǎng)母只有我一個(gè)兒子,我準(zhǔn)備給養(yǎng)母養(yǎng)老送終。現(xiàn)在把父母找到了,我也可以把父母接到身邊來住,兩邊都不耽誤。(張某)
這家人對(duì)我的兒子也還是很不錯(cuò)的,他們自己家里有兩個(gè)女兒,但是為了供這個(gè)兒子上學(xué),都是早早的打工去了,我們現(xiàn)在也算是結(jié)成親戚了。現(xiàn)在他家就剩下他母親了,兒子在河南洛陽生活,給這家的母親養(yǎng)老,我們也是挺支持他的決定,在去年的時(shí)候還把他母親接過來住了一段時(shí)間。(原生家屬)
現(xiàn)在找到了自己的親生家庭,卻發(fā)現(xiàn)母親已經(jīng)去世了,很后悔自己沒能早點(diǎn)找到他們,早點(diǎn)去做 DNA入庫(kù),沒準(zhǔn)還能見到媽媽呢。現(xiàn)在完全回家不太可能,工作、孩子上學(xué)等等問題很多,所以想著把爸爸接到身邊來照顧幾年吧,為他養(yǎng)老送終。(肖某)
4.1.3 猶豫隔離型
猶豫隔離型是指被拐兒童在回歸原生家庭上表現(xiàn)出較低取向,難以融入到原生家庭中。主要原因有三點(diǎn):①原生家庭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是影響被拐兒童與其隔離的首要因素。兒童被拐使原生家庭遭受重大變故,對(duì)原生家庭成員和被拐兒童均造成較大創(chuàng)傷,進(jìn)而產(chǎn)生心理隔閡,阻礙了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如曲某和魚某認(rèn)為自己被拐賣是導(dǎo)致其母親離世與父母離婚的重要因素,因此他們對(duì)于是否回歸較為猶豫,進(jìn)而選擇與原生家庭隔離,避免創(chuàng)傷繼續(xù)深入。②當(dāng)前良好的生活狀態(tài)促使被拐兒童選擇維持現(xiàn)有生活,不回歸原生家庭,如魚某和曲某的家庭與工作都距原生家庭較遠(yuǎn),且當(dāng)前的生活狀態(tài)較為穩(wěn)定,因此選擇在現(xiàn)居地繼續(xù)生活。③家鄉(xiāng)網(wǎng)絡(luò)成員中性和消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對(duì)被拐兒童融入原生家庭具有阻礙作用,如“憐憫”“排斥” “不接受”“歧視”“不了解”等社會(huì)反應(yīng),會(huì)加劇被拐兒童的自我懷疑與否定,從而弱化其主動(dòng)融入原生家庭的意愿,進(jìn)而對(duì)被拐兒童的原生家庭融入產(chǎn)生阻力。
目前還是會(huì)和養(yǎng)父母生活在一起,(原生)父母的離婚,總讓我有些愧疚和難過。我的家庭和工作都在安徽,這很難改變了。(魚某)回家了,看到了父母,看到了所有的親人。我很想留在家,想留在父母身邊,和他們一起生活。可是在廣州呆了這么長(zhǎng)時(shí)間,人脈朋友都在這邊,回去之后不知道干什么了。最重要的是,媽媽已經(jīng)不在了,是因我。我回去,也會(huì)更想念媽媽,家人看見我,也會(huì)想到媽媽是因我去世的,大家應(yīng)該也不會(huì)特別開心吧。(曲某)現(xiàn)在孩子幾乎不回來,接觸也很少,這家人因?yàn)楹⒆觼G了就離婚了,然后現(xiàn)在他媽媽改嫁走了,他爸爸也是不務(wù)正業(yè),日子過得也很艱難,孩子回來知道這個(gè)情況也沒怎么在家呆。這孩子也是夠慘的了,好不容易找回來了,卻沒有家了。(鄰居1)這個(gè)孩子在外面的生活還行吧,已經(jīng)結(jié)婚了,還有個(gè)可愛的兒子,聽說這次尋親就是兒媳婦在網(wǎng)站登記的,夫妻二人常年在外打工,過年過節(jié)回來幾次,從小也不在本村長(zhǎng)大,比較生疏,和周圍鄰居也沒有什么聯(lián)系交流。(鄰居2)
4.2 原生家庭融入的影響機(jī)制
通過深入探究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狀況,發(fā)現(xiàn)本研究的 5 個(gè)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融入度較低,多數(shù)選擇 “回家不回鄉(xiāng)”,這主要與其生命歷程的變遷、被拐兒童心理創(chuàng)傷與家庭網(wǎng)絡(luò)成員的社會(huì)反應(yīng)有關(guān) (圖 2)。被拐兒童在經(jīng)歷了“被拐”后,給原生家庭造成的創(chuàng)傷對(duì)被拐兒童主動(dòng)融入和自主選擇融入具有阻礙作用,對(duì)與原生家庭的猶豫隔離具有促進(jìn)作用。兒童在“被收養(yǎng)”后的收養(yǎng)家庭對(duì)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具有差別化影響,良好型的收養(yǎng)家庭會(huì)促進(jìn)兒童自主選擇融入和猶豫隔離融入,惡劣型的收養(yǎng)家庭會(huì)促進(jìn)被拐兒童主動(dòng)融入原生家庭。被拐兒童在經(jīng)歷了“尋親”與“尋親成功”后,當(dāng)前的生活狀態(tài)對(duì)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也具有重要影響,良好的生活狀態(tài)會(huì)促使兒童自主選擇融入和猶豫隔離融入,糟糕的生活狀態(tài)則會(huì)促進(jìn)兒童主動(dòng)與原生家庭融入。兒童在經(jīng)歷了這一系列重大生命歷程變遷后,對(duì)其心理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創(chuàng)傷,不論創(chuàng)傷程度如何,都會(huì)弱化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家鄉(xiāng)網(wǎng)絡(luò)成員的社會(huì)反應(yīng)也是影響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融入的重要因素,積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會(huì)促進(jìn)兒童主動(dòng)融入原生家庭或自主選擇融入,而消極的、中性的社會(huì)反應(yīng)則會(huì)促進(jìn)兒童自主選擇融入或與原生家庭隔離。
5 結(jié)論與討論
5.1 結(jié)論
正如本文開篇所述,本文無意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學(xué)的總體推論,而是以尋親成功后的5位被拐兒童為研究對(duì)象,以生命歷程理論為指導(dǎo)深度解析被拐兒童與原生家庭的融入狀況,其意義超出了案例本身。主要結(jié)論如下:
(1) 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主要經(jīng)歷被拐、被收養(yǎng)、尋親與尋親成功4個(gè)重大生命事件;兒童被拐是一定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家庭與個(gè)人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被收養(yǎng)與收養(yǎng)家庭的收買意愿有較強(qiáng)關(guān)聯(lián),收養(yǎng)家庭主要為良好型收養(yǎng)家庭與惡劣型收養(yǎng)家庭兩種;尋親是被拐兒童個(gè)人能動(dòng)性與自我選擇的重要體現(xiàn),且尋親一般與工作同時(shí)進(jìn)行,尋親受血緣關(guān)系與收養(yǎng)家庭類型的影響,工作原因與尋親、逃避現(xiàn)有生活環(huán)境和謀生有關(guān)。尋親成功受被拐兒童個(gè)人能動(dòng)性與其生活的時(shí)間與空間的影響。
(2) 被拐兒童在被拐后心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創(chuàng)傷,主要包括自我認(rèn)同感削弱、負(fù)面的情緒擴(kuò)張和負(fù)性生命事件下的安全感降低3種。被拐兒童所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從不同程度上會(huì)對(duì)被拐兒童融入原生家庭產(chǎn)生阻力。
(3) 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社會(huì)融入主要有主動(dòng)融入型、自主選擇型與猶豫隔離型3種。惡劣型的收養(yǎng)家庭、當(dāng)前糟糕的生活狀態(tài)與家鄉(xiāng)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成員積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會(huì)促進(jìn)兒童主動(dòng)融入原生家庭。良好型的收養(yǎng)家庭和當(dāng)前良好的生活狀態(tài)會(huì)促進(jìn)兒童自主選擇與原生家庭融入。原生家庭所遭受的創(chuàng)傷、當(dāng)前良好的生活狀態(tài)和家鄉(xiāng)網(wǎng)絡(luò)成員中性與消極的社會(huì)反應(yīng)會(huì)促使兒童與原生家庭隔離。
5.2 討論
本文探索性地從生命歷程視角對(duì)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與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展開研究,是對(duì)被拐兒童案例數(shù)據(jù)獲取困難的一次積極嘗試。本文揭示了被拐兒童在被拐賣后的生命軌跡變化,探究了其對(duì)原生家庭與收養(yǎng)家庭的影響,以及與其原生家庭融入之間的關(guān)系,是對(duì)拐賣兒童犯罪的社會(huì)學(xué)地理學(xué)研究的深入拓展[37]。同時(shí)發(fā)現(xiàn)被拐兒童在被拐后所受的心理創(chuàng)傷與其他兒童如散居孤兒、留守兒童等較為相似,表明兒童在非正常生活環(huán)境下其弱勢(shì)性更易凸顯[38]。盡管本文取得一定的認(rèn)識(shí),但仍存在以下局限:①數(shù)據(jù)源僅為能聯(lián)系成功且愿意接受訪談的被拐兒童案例,案例數(shù)量較少且未涉及其他數(shù)據(jù),致使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應(yīng)重點(diǎn)同公安部門進(jìn)行合作,獲取更為全面數(shù)據(jù),為被拐群體尋親成功后的社會(huì)融入機(jī)制提出更為全面的評(píng)估與建議。②在訪談中為避免對(duì)被拐兒童產(chǎn)生二次傷害,只是聚焦于其被拐相關(guān)的經(jīng)歷與感受,未全面詳盡挖掘被拐兒童完整的生命歷程變遷,在后期研究中,應(yīng)探索新的訪談方法,在不傷害被拐兒童的同時(shí)獲取其更為詳盡完整的生命歷程事件,進(jìn)而深入分析個(gè)體的主觀能動(dòng)性與社會(huì)網(wǎng)絡(luò)關(guān)系等對(duì)其尋親成功后的社會(huì)融入的影響。
根據(jù)本文研究結(jié)果,針對(duì)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社會(huì)融入現(xiàn)狀,提出如下對(duì)策建議:首先應(yīng)完善收養(yǎng)制度與杜絕拐賣現(xiàn)象。被拐兒童的原生家庭融入問題由拐賣犯罪所引起,拐賣犯罪則由買方市場(chǎng)所主導(dǎo),因此公安部門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拐賣兒童犯罪的打擊力度,家庭與社會(huì)應(yīng)重視對(duì)兒童的監(jiān)護(hù),為兒童營(yíng)造健康安全的成長(zhǎng)環(huán)境。其次,充分發(fā)揮家庭的血緣紐帶作用,為被拐兒童提供包容、和諧的家庭氛圍,使其真正感受到家庭的溫暖與愛護(hù),促使其更快的適應(yīng)與融入原生家庭。第三,充分展示社會(huì)的包容力。被拐兒童尋親成功后的融入不僅是家庭問題,更是社會(huì)問題,因此社會(huì)各界以及社會(huì)救助機(jī)構(gòu)應(yīng)加強(qiáng)對(duì)被拐兒童情感與心理訴求的關(guān)注與輔導(dǎo)。最后,重視對(duì)被拐兒童“去污名化”。社會(huì)要充分發(fā)揮作用,如通過樹立優(yōu)秀被拐兒童融入社會(huì)的典型,加強(qiáng)對(duì)被拐兒童積極形象的宣傳與塑造,促進(jìn)社會(huì)對(duì)被拐兒童群體角色的認(rèn)同,從而促進(jìn)被拐兒童的原生家庭與社會(huì)的融入。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