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經(jīng)過(guò)幾代學(xué)者的努力,數(shù)字人文從無(wú)到有,在學(xué)科的制度化建設(shè)方面已取得長(zhǎng)足的進(jìn)步。然而,目前數(shù)字人文領(lǐng)域內(nèi)發(fā)表的專著、論文和制作(圖像、數(shù)據(jù)和編碼)雖然數(shù)量可觀,真正令人滿意的成果卻是鳳毛麟角,其原因在于大多數(shù)研究者過(guò)于偏重證明數(shù)字工具的可行性,而忽視學(xué)術(shù)發(fā)現(xiàn)的重要性。數(shù)字人文的突破之路在于把關(guān)注的重心從工具理性自我把玩轉(zhuǎn)移到外向性的、可傳達(dá)的發(fā)現(xiàn)性學(xué)術(shù)。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數(shù)據(jù)本身的價(jià)值及其對(duì)于人文研究的意義,相信數(shù)據(jù)的言說(shuō)意義,但不迷信數(shù)據(jù)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絕對(duì)、唯一的再現(xiàn)。只有把數(shù)字化文本納入文本闡釋理論的范疇,糅合遠(yuǎn)距離閱讀的功能和人工閱讀的智慧,我們才能充分凸現(xiàn)數(shù)字文本的社會(huì)與文化寓意,從而把信息轉(zhuǎn)變?yōu)橹R(sh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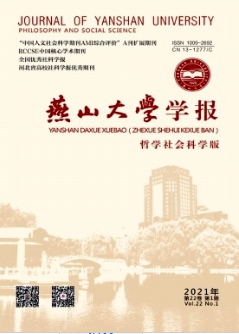
本文源自燕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發(fā)表時(shí)間:2021-02-26《燕山大學(xué)學(xué)報(bào)》雜志,于2000年經(jīng)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zhǔn)正式創(chuàng)刊,CN:13-1277/C,本刊在國(guó)內(nèi)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shí)效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其中主要欄目有:政治學(xué)、法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倫理學(xué)等。
關(guān)鍵詞:數(shù)字人文;遠(yuǎn)距離閱讀;工具理性;數(shù)據(jù)崇拜;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
幾年前我在本學(xué)報(bào)發(fā)表了一篇介紹數(shù)字人文的短文,其中談到了數(shù)字媒介和傳統(tǒng)人文的聯(lián)姻形成了數(shù)字人文的基礎(chǔ)。正是由于這種學(xué)科交叉性給數(shù)字人文學(xué)科造成了界定的困難,因此我把人文科學(xué)的數(shù)字化進(jìn)程比喻為“幽靈”:“數(shù)字化對(duì)于人文學(xué)科而言仍然是個(gè)幽靈,因?yàn)樗勤呄蛴谖磥?lái)的現(xiàn)在,一個(gè)未知超過(guò)已知的現(xiàn)象,一個(gè)幻想多于現(xiàn)實(shí)的概念。” 1 時(shí)至今日,我依然喜歡這個(gè)比喻,因?yàn)閿?shù)字人文這個(gè)幽靈變化莫測(cè),既親近而又飄渺,同時(shí)又讓我們魂?duì)繅?mèng)繞,難以釋?xiě)选?/p>
數(shù)字人文的何作何為、何去何從是數(shù)字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中的“天問(wèn)”,從其問(wèn)世之日起從未停息。在人類科學(xué)史上,所有新興學(xué)科都在懷疑和質(zhì)詢的聲音中生長(zhǎng)成型,數(shù)字人文也不例外。在加利福利亞的硅谷, “炒作周期” (hype cycle) 是一個(gè)廣為人知的術(shù)語(yǔ)。 這個(gè)具有自嘲意味的術(shù)語(yǔ)描繪的是一般高科技公司發(fā)展成熟的的五個(gè)周期:首先是“科技起因” (technology trigger), 這時(shí)新科技的發(fā)明,引起風(fēng)投基金和媒體的興趣;其次是“過(guò)度期望的高峰” (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s),其間因?yàn)檫^(guò)高的目標(biāo)未能實(shí)現(xiàn),投資方略有微詞,創(chuàng)業(yè)者無(wú)所適從;于是高科技公司陷于“失望的低谷” (trough of disillusionment) ,生死存亡在于調(diào)整決策,適應(yīng)市場(chǎng);再其次是“啟迪的山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這時(shí)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換來(lái)了腳踏實(shí)地的規(guī)劃和穩(wěn)固扎實(shí)的發(fā)展;最后是“生產(chǎn)效率的高原” (plateau of productivity), 這便是高科技公司鳳凰再生,走向成熟的標(biāo)志。
這個(gè)卓卓有名的“炒作周期”理論是否能有效地解釋高科技公司的成敗興亡另當(dāng)別論,但數(shù)字人文目前處于“失望的低谷”已從個(gè)別學(xué)者的竊竊私語(yǔ)幾乎變成了學(xué)界的共識(shí)。跟前期的激烈批評(píng)不同——那時(shí)一些捍衛(wèi)傳統(tǒng)人文價(jià)值觀念的學(xué)者往往對(duì)數(shù)字人文持徹底否定的立場(chǎng),時(shí)而甩出有點(diǎn)聳人聽(tīng)聞的標(biāo)題,如史蒂文·馬赫(Stephen Marche)的《文學(xué)不是數(shù)據(jù):駁數(shù)字人文 》3 或亞當(dāng)·克思奇(Adam Kirsch)的《科技接管英文系: 數(shù)字人文的虛假承若》,4 近期的批評(píng)則來(lái)自于數(shù)字人文的參與者,是一種反思與自省式的批評(píng),有點(diǎn)恨鐵不成鋼的意味。弗朗科·莫瑞狄(Franco Moretti)可以算是這類批評(píng)的最好代表。莫瑞狄既是著名的傳統(tǒng)比較文學(xué)學(xué)者,也是公認(rèn)的數(shù)字人文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遠(yuǎn)距離閱讀” ( Distant Reading)的概念已成為數(shù)字人文的一個(gè)標(biāo)識(shí)。然而在最近一次有關(guān)數(shù)字人文的對(duì)談里,他對(duì)數(shù)字人文的學(xué)科現(xiàn)狀卻表露出相當(dāng)悲觀的情緒。面對(duì)采訪者對(duì)于數(shù)字人文的未來(lái)可為的提問(wèn),莫瑞狄首先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表示不滿,他說(shuō):
“‘數(shù)字人文已經(jīng)做了什么?’ 這個(gè)問(wèn)題我們根本沒(méi)有涉及。為什么不能先放下關(guān)于未來(lái)的問(wèn)題,問(wèn)問(wèn)現(xiàn)在數(shù)字人文做了什么?我覺(jué)得這本身就是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令人費(fèi)解的是,數(shù)字人文目前為自己造就了一種永久的嬰兒期,總是在寄希望于未來(lái)。這種作法是對(duì)理智判斷的曲解,因?yàn)槔碇桥袛鄳?yīng)該面向過(guò)去的存在,而不是對(duì)未來(lái)的承諾。”5
作為數(shù)字人文的大家,莫瑞狄對(duì)于學(xué)科的未來(lái)不可能沒(méi)有自己的設(shè)想。我猜測(cè)也許他對(duì)處于“炒作周期”中數(shù)字人文司空見(jiàn)慣的過(guò)度自我推銷與無(wú)邊許若或許有點(diǎn)厭煩,但這更有可能反映了他對(duì)數(shù)字人文研究現(xiàn)狀的失望,因?yàn)樗又卮鹆俗约旱脑O(shè)問(wèn):“[數(shù)字人文]已取得的成績(jī)并不令人滿意……數(shù)字人文自己號(hào)稱是了不起的新事物,然而至今為止我們拿不出什么證據(jù)證明如此。” 6
由于是對(duì)談的形式,我們不能對(duì)莫瑞狄的隨心恣意的語(yǔ)詞過(guò)于挑剔。比如在對(duì)談中他甚至發(fā)出“數(shù)字人文什么也不是”(digital humanities means nothing)的驚人之語(yǔ),提議要用” 電腦批評(píng)“(computational criticism)而取而代之。莫瑞狄想傳達(dá)的是對(duì)數(shù)字人文真切而又執(zhí)著的關(guān)懷,同時(shí)也是對(duì)數(shù)字人文目前處于“失望的低谷”的焦慮。焦慮的根源在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現(xiàn)狀與我們對(duì)它“過(guò)度期望”不相般配,這是莫瑞狄的個(gè)人意見(jiàn),但他很顯然綜合了眾多批評(píng)者的聲音。
數(shù)字人文孵育于 20 世紀(jì)六七十年代,成型于八九十年代,自 2004 年正式命名之后,進(jìn)入迅速發(fā)展的時(shí)期,相當(dāng)于前文所說(shuō)的“過(guò)度期望的高峰”。迄今為止,數(shù)字人文當(dāng)然不是一無(wú)所成;恰恰相反,它可以說(shuō)是從無(wú)到有,碩果累累。除了海量的制作(圖像、數(shù)據(jù)和編碼)、論文和專著——其鑒別和評(píng)估是下文要討論的問(wèn)題——以外,數(shù)字人文的成果主要表現(xiàn)在學(xué)科本身的制度化建設(shè),包括研究中心、專業(yè)協(xié)會(huì)與行業(yè)學(xué)術(shù)刊物。以各種方式命名的研究機(jī)構(gòu)如室(lab)、方案(initiative)和中心(center)在歐美大學(xué)如雨后春筍般生長(zhǎng),從著名學(xué)府倫敦大學(xué)、普林斯頓大學(xué)到一般高校堪薩斯大學(xué)、喬治梅森大學(xué),大家都想搭上數(shù)字人文的快車。有些高校甚至成立了單列的專業(yè)系所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般以數(shù)字人文加公共人文 (public humanities)或應(yīng)用人文(applied humanities)命名,如倫敦國(guó)王學(xué)院和亞利桑那大學(xué)。各種專業(yè)協(xié)會(huì)的數(shù)目有二十幾個(gè),其中有影響的包括“電腦與人文協(xié)會(huì)”(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歐洲數(shù)字人文協(xié)會(huì)”(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Digital Humanities)和“數(shù)字人文組織聯(lián)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7 學(xué)術(shù)刊物大多行數(shù)字人文之實(shí),只有網(wǎng)絡(luò)電子版,開(kāi)源,依循盲審制度,如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Digital Studies 和 Journal of the Text Encoding Initiative。8 數(shù)字人文的制度化建設(shè)的迅猛發(fā)展離不可充足的科研經(jīng)費(fèi)支持,這方面數(shù)字人文相比傳統(tǒng)人文有明顯的優(yōu)勢(shì),因?yàn)槠渑c電腦科技的交叉得以模仿現(xiàn)行科學(xué)體制的操作模式,從而取得公共資源與私立基金會(huì)的資助。當(dāng)然,數(shù)字人文的興盛也與美國(guó)人文學(xué)科國(guó)家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大力提倡和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言協(xié)會(huì)(Modern Languages Association)的學(xué)術(shù)認(rèn)定息息相關(guān)。
在西方學(xué)界,關(guān)于人文學(xué)科在數(shù)字化時(shí)代的危機(jī)的討論由來(lái)已久,數(shù)字人文一直被認(rèn)為破解這個(gè)危機(jī)的途徑之一,因?yàn)槠淇茖W(xué)內(nèi)涵和交叉特性而被寄予厚望。如果僅從其轟轟烈烈的制度化建設(shè)來(lái)看,數(shù)字人文對(duì)于提升人文學(xué)科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度與影響力是非常成功的。然而,制度化建設(shè)的成功并不是一個(gè)學(xué)科成熟的決定性標(biāo)志,有效研究成果及其影響才是。迄今為止,數(shù)字人文領(lǐng)域內(nèi)發(fā)表的專著、論文和圖像設(shè)計(jì)與數(shù)據(jù)庫(kù)制作數(shù)量雖然非常可觀,可是真正令人滿意的成果卻是鳳毛麟角。這正是莫瑞狄焦慮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他對(duì)數(shù)字人文下期的工作提出如下建議:“也許數(shù)字人文接下來(lái)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了解自已的研究成果的性質(zhì),也就是如何評(píng)估的問(wèn)題。同時(shí),我們必須反思為什么生產(chǎn)優(yōu)異的成果如此之難,盡管我們的精力、人才和工具一樣也不缺。”9
數(shù)字人文研究成果的評(píng)估困難恰恰來(lái)自這個(gè)學(xué)科的新穎之處:即把數(shù)據(jù)分析帶入文本分析,通過(guò)其產(chǎn)生的統(tǒng)計(jì)性的數(shù)量化結(jié)果而導(dǎo)出新的結(jié)論或產(chǎn)生新的知識(shí)。經(jīng)過(guò)幾十年的努力,數(shù)字人文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價(jià)值已經(jīng)得到了制度化的肯定,可是它的價(jià)值理性必須納入現(xiàn)有的科學(xué)評(píng)估體系,包括傳統(tǒng)人文的價(jià)值評(píng)估范式。很顯然,數(shù)字人文的數(shù)量化文本分析方法跟傳統(tǒng)人文的質(zhì)量化分析方法是不相融的,因此要想建立一個(g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是件困難的事。所以早期的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處于相對(duì)獨(dú)立的狀態(tài),在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邊緣地帶獨(dú)自辛勤耕耘。得益于標(biāo)準(zhǔn)化的電腦語(yǔ)言程序的建立和完善, 如“標(biāo)準(zhǔn)通用標(biāo)記語(yǔ)言”(Standard Generalized Markup Language)和文本編碼計(jì)劃(Text Encoding Initiative),他們制作的一系列普通或主題性的文本語(yǔ)庫(kù), 前者如谷歌書(shū)庫(kù),后者如有名的“書(shū)信共和國(guó)圖譜”(Mapping the Republic of Letters),為文本的“數(shù)字再現(xiàn)”提供了實(shí)驗(yàn)基礎(chǔ),從而拉近了電腦閱讀與讀者閱讀的距離。進(jìn)入二十一世紀(jì),數(shù)字人文的潛在學(xué)術(shù)價(jià)值不再令人懷疑,但是如何在現(xiàn)有的學(xué)術(shù)體系中評(píng)價(jià)數(shù)字人文研究成果引起了持久的爭(zhēng)議,這首先對(duì)于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的求職、升遷和獎(jiǎng)勵(lì)具有實(shí)際意義,特別是在數(shù)字人文學(xué)科建設(shè)蓬勃開(kāi)展的時(shí)候。有鑒于此,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言協(xié)會(huì)于 2000 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評(píng)價(jià)數(shù)字人文與數(shù)字媒介學(xué)術(shù)成果的指導(dǎo)性建議,并于 2012 年更新。因?yàn)楝F(xiàn)代語(yǔ)言協(xié)會(huì)是美國(guó)最大的人文學(xué)科專業(yè)組織,它的綱領(lǐng)、章程和建議有很高的權(quán)威性。這份建議首先肯定數(shù)字媒介對(duì)教授職能在讀寫(xiě)文化、學(xué)術(shù)研究、教學(xué)實(shí)踐及公共服務(wù)方面帶來(lái)的巨大變化,這是我們所處的數(shù)字化時(shí)代社會(huì)與文化變革的結(jié)果,而數(shù)字人文代表的方法和理念是對(duì)這一時(shí)代的理性認(rèn)可,是延續(xù)和張揚(yáng)人文精神的知識(shí)渠道。在這個(gè)認(rèn)知層面,建議強(qiáng)調(diào):“學(xué)術(shù)評(píng)價(jià)必須反映迅速變化之中的科技、制度與職業(yè)以及伴隨而來(lái)的對(duì)學(xué)術(shù)、教學(xué)和服務(wù)的重新定義。”10 由于數(shù)字人文學(xué)科本身的繁復(fù)和多樣,這份建議并沒(méi)有給出非常具體的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只是強(qiáng)調(diào)在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評(píng)價(jià)規(guī)則的框架之下包容更為廣泛的研究成果樣式,如電子出版物、開(kāi)源期刊及數(shù)字與圖像制作。
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言協(xié)會(huì)及其它專業(yè)組織對(duì)數(shù)字人文的認(rèn)可和倡導(dǎo)只是解決了一半的問(wèn)題,另一半則需要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共同努力一套衡量研究成果質(zhì)量的評(píng)估體系,既能滿足數(shù)字人文這頂“大帳篷” 11 的各種研究產(chǎn)出方式,又能回答數(shù)字人文的質(zhì)疑者,從現(xiàn)在常見(jiàn)的學(xué)科內(nèi)自我慶賀的喧嘩走向人文科學(xué)關(guān)于范式與規(guī)則的普識(shí)之路。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guó)現(xiàn)代語(yǔ)言協(xié)會(huì)對(duì)數(shù)字人文的熱情支持并非僅是部分領(lǐng)導(dǎo)者的先知先覺(jué),而是得益于美國(guó)高等教育界自上世紀(jì)九十年代以來(lái)對(duì)于高等教育的價(jià)值與目的的反思與討論,包括有關(guān)學(xué)術(shù)文化傳統(tǒng)的重新認(rèn)識(shí)。1990 年,著名教育學(xué)家歐內(nèi)斯特·博耶 (Ernest Boyer)受卡耐基基金會(huì)之約發(fā)表了影響深遠(yuǎn)的研究報(bào)告《重估學(xué)術(shù):教授職業(yè)的首要責(zé)任》,主張?jiān)诟叩仍盒H找嬖黾拥纳鐣?huì)責(zé)任和迅速發(fā)展的信息化科技的前景之下,我們要突破由來(lái)已久的研究即學(xué)術(shù)的傳統(tǒng)定義。他認(rèn)為教學(xué)與研究絕然對(duì)立的思維已經(jīng)過(guò)時(shí),提出了擴(kuò)展學(xué)術(shù)定義的四點(diǎn)意見(jiàn),即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scholarship of discovery),整合的學(xué)術(shù) (scholarship of integration),應(yīng)用的學(xué)術(shù)(scholarship of application)和教學(xué)的學(xué)術(shù)(scholarship of teaching)。12 這四點(diǎn)意見(jiàn)基本上規(guī)范了之后關(guān)于學(xué)術(shù)文化的變革方向,雖然其具體內(nèi)容仍是商榷和爭(zhēng)議的對(duì)象,還有待于充實(shí)與完善。
不可否認(rèn)的是,當(dāng)今的美國(guó)高等教育與學(xué)術(shù)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如大學(xué)財(cái)政與管理的企業(yè)化、學(xué)科交叉的制度化,在線與多媒體教育科技的普遍化等等,雖然這些變化帶來(lái)的效益與弊端還有待于歷史的評(píng)判。 數(shù)字人文在這個(gè)大壞境中迅速發(fā)展成型也是順乎自然的事情。至少在歐內(nèi)斯特·博耶所提倡的學(xué)術(shù)文化新定義的三個(gè)方面,即整合的學(xué)術(shù)、應(yīng)用的學(xué)術(shù)和教學(xué)的學(xué)術(shù),數(shù)字人文發(fā)揮其先天的優(yōu)勢(shì),數(shù)十年來(lái)取得了非凡的成績(jī)。然后,我們注意到歐內(nèi)斯特·博耶把“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列在第一位而突出其在新的學(xué)術(shù)文化中的重要性。發(fā)現(xiàn)意味著創(chuàng)造、發(fā)明,是產(chǎn)生和傳遞新知識(shí)的基礎(chǔ),也是貫穿一切科學(xué)話語(yǔ)(自然科學(xué)或人文科學(xué))之中的核心價(jià)值符號(hào)。在這方面,數(shù)字人文的表現(xiàn)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一如弗朗科·莫瑞狄的悲觀論調(diào),我認(rèn)為目前數(shù)字人文處于“失望的低谷” 的說(shuō)法并不過(guò)分。
那么數(shù)字人文目前面臨的挑戰(zhàn)是什么呢? 筆者認(rèn)為一是評(píng)估體系的自我指涉,二是闡釋理論的放棄。前者導(dǎo)致數(shù)字人文研究的自我封閉,大量的研究成果自?shī)首詷?lè),而得不到人文學(xué)界的認(rèn)可,更不能滿足“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的范式要求。后者傾向于過(guò)度相信數(shù)據(jù),視之為自在、自明的文本,把文本解讀簡(jiǎn)化于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和數(shù)字推理。兩者雖然在研究過(guò)程和成果呈現(xiàn)中表現(xiàn)不同,實(shí)質(zhì)上都源于方法的理性化,即以工具理性為目的的實(shí)驗(yàn)主義哲學(xué)。
數(shù)字人文的學(xué)科立足點(diǎn)是對(duì)源數(shù)據(jù)(對(duì)文本的某種切割或綜合)的量化分析,對(duì)于這種分析的有效性的驗(yàn)證來(lái)自于兩個(gè)方面,第一是采集源數(shù)據(jù)的工具是否運(yùn)行正常,第二是這個(gè)運(yùn)行正常的工具所得出的結(jié)論是否可靠。常見(jiàn)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多注重于第一而輕視第二,或者把兩者混而為一。這里的“工具”是指替代人眼閱讀的機(jī)器閱讀,包括研究者依據(jù)電腦編碼語(yǔ)言定制的各種處理文本的專用應(yīng)用程序,或由高科技公司及行業(yè)研究機(jī)構(gòu)開(kāi)發(fā)的智能數(shù)據(jù)庫(kù)與通用閱讀器,其中最有名的是由谷歌于 2010 年推出的“N 像閱讀器” (Ngram Viewer)。這個(gè)閱讀器可以瞬時(shí)“閱讀”谷歌書(shū)庫(kù)”(目前收集了四千萬(wàn)書(shū)目,約占世界總量的百分之三十)中的海量文本,所以自問(wèn)世以來(lái)成為數(shù)字人文研究者津津樂(lè)道的工具,尤其為歷史和文學(xué)學(xué)者所偏愛(ài)。因?yàn)槠渎曂陀绊懀P(guān)于數(shù)字人文的評(píng)估爭(zhēng)議也集中體現(xiàn)在 N 像閱讀器的功用和效率上面。
N 像閱讀器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計(jì)算機(jī)搜索引擎,它通過(guò)人為輸入的任意關(guān)鍵詞組合而給出詞語(yǔ)頻率和相聯(lián)關(guān)系的圖標(biāo)或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同時(shí)注明詳細(xì)的時(shí)間坐標(biāo)。13 這種閱讀完美體現(xiàn)了弗朗科·莫瑞狄先于 N 像閱讀器十年所猜想的“遠(yuǎn)距離閱讀”的內(nèi)涵,因?yàn)?“遠(yuǎn)距離閱讀”的實(shí)質(zhì)就是借助于數(shù)字化手段的泛讀,在海量的文本里通過(guò)“分析修辭、主題、借喻、風(fēng)格和系統(tǒng)性來(lái)尋找范式和模型”。14 顯而言之,完成這樣的閱讀非 N 像閱讀器莫屬。事實(shí)上,弗朗科·莫瑞狄身體力行,通過(guò) N 像閱讀器,較早地提供了一個(gè)關(guān)于“遠(yuǎn)距離閱讀”的研究案例,即對(duì)從 1740 年到 1850 年之間出版的七千部英國(guó)小說(shuō)中所體現(xiàn)的作家在小說(shuō)主題和遣詞造句中的性別意識(shí),這是數(shù)字人文早期研究一個(gè)典范性的成果。
然而,借助 N 像閱讀器的遠(yuǎn)距離閱讀功能而產(chǎn)生的結(jié)論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并非毫無(wú)爭(zhēng)議,最常見(jiàn)的批評(píng)是它們往往只是證實(shí)已知的常識(shí),而非創(chuàng)造了新的知識(shí)。關(guān)于弗朗科·莫瑞狄的研究成果的評(píng)價(jià)筆者另文已有介紹,15 這里不再贅述。美國(guó)學(xué)者艾拉茲·埃登(Erez Aiden)和讓-巴蒂斯特·米歇爾(Jean-Baptiste Michel)合著的《未知的疆域:大數(shù)據(jù)作為探究人類文化的棱鏡》16 是另外一個(gè)體現(xiàn)了數(shù)字人文的承諾與局限的例子。這兩位學(xué)者置身于信息化時(shí)代的宏觀視野,宣稱“大數(shù)據(jù)革命”不光會(huì)改變我們?nèi)绾握J(rèn)識(shí)自我,還會(huì)改變?nèi)宋暮蜕鐣?huì)科學(xué)的本質(zhì),并重新定位商業(yè)化社會(huì)與大學(xué)這個(gè)象牙之塔的關(guān)系。基于這個(gè)宏觀視野,他們關(guān)注點(diǎn)是大數(shù)據(jù)的歷史痕跡,比如說(shuō)它們?nèi)绾斡绊懮虡I(yè)活動(dòng)、政府決策、社會(huì)行為與個(gè)人生活。于此,他們依據(jù) N 像閱讀器所提供的抽象數(shù)據(jù)語(yǔ)言來(lái)解釋許多歷史和社會(huì)現(xiàn)象,其中一個(gè)的案例是此書(shū)第五章《沉默之聲》對(duì)納粹德國(guó)的藝術(shù)審查制度的研究。他們的檢索發(fā)現(xiàn)許多著名現(xiàn)代藝術(shù)畫(huà)家像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 保羅·克利(Paul Klee) 在德國(guó) 1933-1945 年間出版的書(shū)籍中幾乎不見(jiàn)蹤影,這說(shuō)明納粹德國(guó)已成功地根除了作為 “頹廢藝術(shù)”的現(xiàn)代派藝術(shù)。這個(gè)結(jié)論,正如亞當(dāng)·克思奇所言,毫無(wú)新意,至多提供了關(guān)于納粹德國(guó)焚書(shū)禁言體制的一個(gè)細(xì)節(jié)。更為重要的是,亞當(dāng)·克思奇指出了兩位作者在構(gòu)思這個(gè)研究案例時(shí)的致命缺陷,即為已知的問(wèn)題補(bǔ)充顯然的答案:“除非我們知道要找什么、為什么要找它,我們就不會(huì)去檢索那個(gè)時(shí)間段這些名字出現(xiàn)的頻率。”17
如此看來(lái),艾拉茲·埃登和讓-巴蒂斯特·米歇爾的成就只能說(shuō)是在整合的學(xué)術(shù)和應(yīng)用的學(xué)術(shù)方面有所貢獻(xiàn),而在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方面則無(wú)所建樹(shù)。更恰當(dāng)?shù)卣f(shuō),他們證明了數(shù)字人文的工具價(jià)值,即 N 像閱讀器的遠(yuǎn)距離閱讀的強(qiáng)大功能。身為 N 像閱讀器的發(fā)明者群體成員之一,他們對(duì)這個(gè)新穎的高科技“玩具”愛(ài)不釋手, 奉為至寶,因而不惜以近三百頁(yè)的篇幅而渲染其功能與價(jià)值,這里有一種“工具自戀”的姿態(tài)。也許我們不應(yīng)該求全責(zé)備,因?yàn)?N 像閱讀器確實(shí)是一項(xiàng)了不起的發(fā)明,但在數(shù)字人文界,這種工具自戀的確是一種常見(jiàn)的現(xiàn)象,尤其是在具有科技背景的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當(dāng)中。工具自戀的現(xiàn)象反映了數(shù)字人文對(duì)高科技產(chǎn)業(yè)炒作文化的追隨,對(duì)其軟件程序產(chǎn)品的商品特性的警醒不足,從而把學(xué)術(shù)性和市場(chǎng)化混為一談。更為重要的,工具自戀遮蔽了對(duì)工具本身應(yīng)有的批評(píng)維度,對(duì)軟件程序可能的偏見(jiàn)與局限視而不見(jiàn),從而忽略其潛在的結(jié)果與效用偏差。在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的算法研究話語(yǔ)中,“垃圾進(jìn),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是一句很有反省意味的流行語(yǔ),意指錯(cuò)誤的數(shù)據(jù)輸入會(huì)產(chǎn)生荒謬的數(shù)據(jù)輸出。這不僅強(qiáng)調(diào)人為數(shù)據(jù)選擇的前在性,也暗含算法程序的局限性。當(dāng)今的許多基于算法程序的數(shù)字化商業(yè)產(chǎn)品,如微軟的人工智能、臉書(shū)的信息算法等使用預(yù)測(cè)模型(predictive modeling)的數(shù)據(jù)采集系統(tǒng),在種族、性別與社會(huì)弱勢(shì)群體方面都表現(xiàn)出不同程度的偏見(jiàn)與歧視。谷歌的 N 像閱讀器及其伴侶谷歌書(shū)庫(kù)也不例外,它們眾多的缺陷如書(shū)目選擇的隨意性、科目類別的代表性以及光學(xué)掃描的文字誤差都可能引發(fā)遠(yuǎn)距離閱讀的失真。有鑒于此,一些有見(jiàn)識(shí)的學(xué)者如馬修·富勒(Matthew Fuller) 提出了“軟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的概念,18 把軟件系統(tǒng)的社會(huì)與文化效果的研究納入數(shù)字人文的學(xué)科領(lǐng)域。
毫無(wú)疑問(wèn),數(shù)字人文不能放棄對(duì)數(shù)字化工具的批評(píng),但這不意味著放棄數(shù)字化工具本身。數(shù)字人文,從根本上來(lái)說(shuō),就是用數(shù)字化工具來(lái)回答傳統(tǒng)人文的問(wèn)題。對(duì)于任何一項(xiàng)數(shù)字人文研究,工具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問(wèn)題則更為重要。“正確”的問(wèn)題應(yīng)該體現(xiàn)人文精神的精髓,即代表人類對(duì)經(jīng)驗(yàn)的超越和對(duì)未來(lái)的幻想,指向增進(jìn)理解和培育共情,其預(yù)想的答案一定含有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內(nèi)容,并經(jīng)得起現(xiàn)有學(xué)術(shù)評(píng)估體系的考驗(yàn)。 在研究過(guò)程中,這個(gè)“正確”的問(wèn)題與數(shù)字化工具碰撞、交融、磨合,有可能變成無(wú)意義的問(wèn)題,也有可能變形為其它的問(wèn)題,或引發(fā)出其它的衍生問(wèn)題,這也許是數(shù)字人文研究不同于傳統(tǒng)人文研究的地方。這種問(wèn)題為重、工具為輔的研究構(gòu)想已經(jīng)在一些成功的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那里體現(xiàn)出來(lái),比如英國(guó)學(xué)者梅爾芭· 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及其合作團(tuán)隊(duì)關(guān)于“現(xiàn)代主義的關(guān)鍵詞”的研究項(xiàng)目。19 這項(xiàng)研究首先從一個(gè)來(lái)自于個(gè)人近讀讀經(jīng)驗(yàn)的假設(shè)入手,即某些關(guān)鍵詞如廣告(advertising)、宣傳(propaganda)、國(guó)際化(international)在現(xiàn)代派文學(xué)藝術(shù)興起期間廣為流行,而另外一些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關(guān)鍵詞如宣言(manifesto)、先鋒(avant-garde) 則不是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的常用詞語(yǔ)。毋庸置疑,N 像閱讀器至少目前是驗(yàn)證這個(gè)假設(shè)的理想工具,驗(yàn)證的結(jié)果是假設(shè)成立。下一步,梅爾芭· 卡迪-基恩從這個(gè)成立的假設(shè)中引發(fā)新的問(wèn)題。在比較、考察英國(guó)文學(xué)史上的維多利亞文學(xué)和現(xiàn)代派文學(xué)的承繼與斷裂痕跡時(shí),她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有趣的 “戰(zhàn)爭(zhēng)駝峰曲線”,即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某些關(guān)鍵詞的出現(xiàn)頻率的升降類似于隆起的駝峰。“戰(zhàn)爭(zhēng)”這個(gè)詞的使用頻率符合駝峰曲線,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和平”“民族”“民主”這些詞語(yǔ)的歸類也合情合理,但“速度”、“新世界”這些詞語(yǔ)的駝峰頻率卻超乎我們的意料。受這些關(guān)鍵詞的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的啟示,梅爾芭· 卡迪-基恩進(jìn)而討論了幾個(gè)文學(xué)與社會(huì)關(guān)系重要課題:人類戰(zhàn)爭(zhēng)的重負(fù)如何改變了我們的烏托邦構(gòu)想,時(shí)間次序的再現(xiàn)方式,以及自我主體的描述與定義。20 這項(xiàng)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成功的數(shù)字人文研究的構(gòu)想與思路:預(yù)設(shè)的關(guān)鍵詞通過(guò)遠(yuǎn)距離閱讀得到證實(shí)或修正,新的關(guān)鍵詞形成數(shù)據(jù)鏈或圖標(biāo)、曲線,指向潛在的范式、模型,通過(guò)再次閱讀而連接傳統(tǒng)人文的課題,從而厘正已知的知識(shí)或創(chuàng)造新的知識(shí),最終體現(xiàn)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文化價(jià)值。
如果說(shuō)數(shù)字化的遠(yuǎn)距離閱讀過(guò)去是、現(xiàn)在仍然是數(shù)字人文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那么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重新考慮它的涵義的時(shí)候。首先,我們必須摒除弗朗科·莫瑞狄最初所設(shè)想的遠(yuǎn)距離閱讀與近讀(close reading,又譯“細(xì)讀”)完全對(duì)立的立場(chǎng),重新認(rèn)可近讀的闡釋功用,雖然數(shù)字人文的近讀并不完全等同于傳統(tǒng)人文學(xué)者的細(xì)讀。遠(yuǎn)距離閱讀是機(jī)器的閱讀,是初級(jí)閱讀,它提供了關(guān)鍵詞的譜系;近讀是人的閱讀,是再次閱讀,它為關(guān)鍵詞添加時(shí)間的坐標(biāo),然后為人類關(guān)注的現(xiàn)實(shí)性問(wèn)題或終極問(wèn)題給出可能的答案。遠(yuǎn)距離閱讀與近讀的糅合不應(yīng)視為對(duì)數(shù)字人文學(xué)科特性的消解,恰恰相反,它應(yīng)看作是電腦科技和傳統(tǒng)人文的交叉性的標(biāo)志。無(wú)論如何,數(shù)字人文的研究對(duì)象依然是文本,雖然這是數(shù)字化的文本,是數(shù)據(jù)通過(guò)“數(shù)字再現(xiàn)”而產(chǎn)生的文本,也可以說(shuō)是文本的文本,21 其文本性不言而喻,而文本性及其意義依然是闡釋學(xué)范疇。 數(shù)字人文的闡釋學(xué),在津德?tīng)柼?Joris J. van Zundert) 看來(lái),已從“文本解讀的理論轉(zhuǎn)變?yōu)橹R(shí)接受的本體理論”,著重于“把信息轉(zhuǎn)變?yōu)橹R(shí)的過(guò)程“。22 數(shù)字化工具為我們提供了逼近文本隱喻(allegory of textuality) 的新手段,而研究者用心的近讀和機(jī)器強(qiáng)大的遠(yuǎn)讀仍然是領(lǐng)悟文本隱喻的必然途徑。
綜而論之,偏重?cái)?shù)字工具還是重視學(xué)術(shù)發(fā)現(xiàn)是當(dāng)今的數(shù)字人文面臨的一個(gè)抉擇。如果我們只是繼續(xù)或重復(fù)早期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的研究思路,把編碼制圖作為首要任務(wù),止步于采集新的數(shù)據(jù)來(lái)證明已知的結(jié)論,那么數(shù)字人文將不會(huì)得到學(xué)界的尊重,永遠(yuǎn)處于失望的低谷之中。數(shù)字人文的突破之路在于把關(guān)注的重心從工具理性自我把玩轉(zhuǎn)移到外向性的、可傳達(dá)的發(fā)現(xiàn)性學(xué)術(shù)。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數(shù)據(jù)本身的價(jià)值及其對(duì)于人文研究的意義,相信數(shù)據(jù)的言說(shuō)意義,但不迷信數(shù)據(jù)是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絕對(duì)、唯一的再現(xiàn)。在當(dāng)今“數(shù)據(jù)崇拜”風(fēng)行一時(shí)的數(shù)字化時(shí)代,這當(dāng)然是一件很難的事情。然而,因?yàn)閿?shù)字人文占有數(shù)字工具技術(shù)與人文傳統(tǒng)精神的交叉優(yōu)勢(shì),數(shù)字人文學(xué)者對(duì)于破解這個(gè)難局負(fù)有義不容辭的責(zé)任。正因于此,我對(duì)數(shù)字人文的未來(lái)仍然抱有期待和希望。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