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20世紀80年代《西游記》兩大英語全譯本的發行,《西游記》譯介首次得以向英美國家展示整體的、全方位的西游知識。在全球化合作背景下,《西游記》非譯介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形象、敘事和精神為主線并以東方元素為點綴,重構英美世界的西游故事,進而推動《西游記》在英美世界進入譯介和非譯介本土化的深入期。譯介給《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提供了發生緣起,只有解決了緣起問題,才能深入探討譯介和非譯介在《西游記》英美本土化流變中經歷的過程、發揮的作用、做出的貢獻和揭示的規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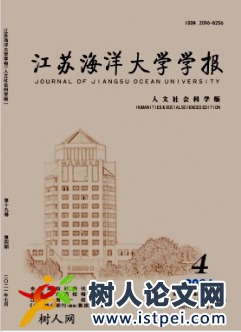
本文源自王鎮; 郭艷花; 楊娟, 江蘇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發表時間:2021-07-27
關鍵詞:《西游記》;本土化;譯介;非譯介
隨著20世紀80年代《西游記》兩大英語全譯本的發行,《西游記》譯介首次得以向英美國家展示整體的、全方位的西游知識,并全面闡釋和張揚《西游記》的文化多元價值。與此同時,基于《西游記》譯介和非譯介研究的專著、論文與文學創作在學術探索、理論建樹與社會互動等方面成果斐然,而在多媒體、信息化、網絡化等高科技技術的助力之下,《西游記》的非譯介形式,即改編的影視劇、動畫片、舞臺劇、音樂、網絡游戲等文藝作品得以策劃、醞釀、生產和上市。以重講西游歷險的美國電影《失落的帝國》(TheLostEmpire)為代表,《西游記》非譯介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都穩步提高,擁有的受眾人數呈幾何級暴漲,《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市場蓬勃發展,潛力驚人,尤其是在全球化合作的應景下,《西游記》非譯介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形象、敘事和精神為主線并以東方元素為點綴,重構英美世界的西游故事,進而推動《西游記》進入譯介和非譯介本土化的深入期,并預示著其在英美國家的發展前景令人欣喜。當然,這一切都得從《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轉向說起。
一、《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轉向
廣義地說,只要是攝入國依據自身的接受能力,對來自輸入國的物質或精神進行本地化的參與和改造行為,由此產生的一切變形結果等,都應歸入本土化的范疇。在此立場上看,無論是區區幾百字的改篡、“獵奇”或“借殼”,還是明顯的“排斥”或“沖突”,都不能被簡單排除出本土化的界定范圍,因為這些嘗試本身已經反映了本土化對象的接受價值、影響力以及本土化調適的可能性。
概言之,《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大致經歷了三個歷史時期:譯介本土化的啟蒙期(1895—1941年)、譯介本土化的普及期(1942—1976 年)和譯介與非譯介本土化的深入期(1977年至今)。1895年,以美籍在華傳教士吳板橋(SamuelI.Woodbridge,1856—1926年)出版的僅有16頁的西游故事TheGolden-HornedDragonKing;or,TheEmperor’sVisittotheSpiritWorld 為開端,《西游記》譯介主要以單篇選譯或故事簡譯的方式走進英美國家的高等學府或研究機構,并流傳于較少部分的漢學家等特殊群體中,雖然整體的社會影響力相對有限,但是畢竟在專業受眾層面潑撒了興趣的種子,為《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轉向集聚了一定的學術營養。
從1942年起,以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ArthurWaley)于1942年完成的英譯本 Monkey(《猴》)為標志,《西游記》隨之進入了英美本土化譯介的普及時期,更重要的是,在膾炙人口的西游取經故事的刺激下,《西游記》譯介迅速帶動了學術的轉向,致使譯介的形式、范疇、規模、程度等不斷突破,《西游記》進入了譯介的社會普及期。在這一時期,《猴》等一大批譯作走出學府,走進書店,走向不同階層的普通受眾,為《西游記》譯作提供了經典的英美本土化樣板,也為譯介的本土化變形鋪平了道路。《猴》于1961年順利躋身于象征英語世界文學經典的“企鵝叢書”之列,表明《西游記》譯作達到了英語文學認定的本土化標準。緊接著,《猴》被作為譯介底本轉譯成德語、西班牙語、法語、意大利語、波蘭語、匈牙利語、捷克語、羅馬尼亞語、瑞典語等歐洲多國語言,顯示出其超凡的語言性、輻射性和接受性,也更坐實了該譯本實為英語文學經典的論斷。同期,《西游記》的譯介與研究成果顯著,相得益彰,交相輝映,以英國漢學家杜德橋(GlenDudbridge,1938—2017年)的專著《十六世紀中國小說〈西游記〉前身 考》(TheHsi-yuchi:AStudyofAntecedentstotheSixteenth-CenturyChineseNovel)為代表,《西游記》的專著與論文分專題、成系列地見諸于印刷品,《西游記》進入尋常百姓家,扎根于普通受眾之中,廣泛傳播開來。
從1977年崛起于翻譯界的“文化轉向”開始到現在,在全球化的“向東看”文化大潮的席卷之下,《西游記》中的東方元素逐漸受到英美大眾的關注,更多的中國儒釋道思想被提煉出來,與英美世界的基督精神搭建生態關聯性并相向而行,于是《西游記》的譯介和非譯介活動都轉向順應著中西跨文化交融的主流順勢而作,并呈全面開花之勢,在英美世界的接受度和貼合度也得以明顯提升。
二、《西游記》的本土化譯介需求
歷史一再證明,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系統要避免退化和衰亡,就必須時刻保持開放性和多元性,必須經常與異質文化進行交流,必須對異域文化體進行譯介和接受,以滋養和更新本國文化。譯介是兩個不同文化共同體之間發生交換作用的主力軍,惟有它才能開啟信息再傳輸、文本傳播、文學交流、文化互通等功能。譯介給《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本土化提供了發生緣起。英美世界的語言文學和文化的開放性、多元性、包容性、人文性等特征促使其長期地、習慣性地選擇、過濾和吸納域外文本和文化,自然也包括譯介并接受中國的文化知識,特別是像《西游記》這樣知識容量大、文化兼容性強的文學佳作,這是英美世界對《西游記》譯介的天然需求。
無論是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譯介學文化轉向,還是接受美學等詩學理論,都迫使翻譯學界的“文學文化學派”和“多元體系派”關注國別、社會、傳統、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文化因素對翻譯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以及文學翻譯與目標語文化的相互關系,普遍相信“接收者必然根據自身文化背景和時代精神的要求,對外來因素進行重新改造與重新解讀和利用,一切外來文化都是被本土文化過濾后而發揮作用的”[1]96。這些新理念證實一個事實:如果沒有如同《西游記》這樣成功的譯介在域外文化體中的慣性影響,英語文化就不可能接受并發展成一個強大、包容的多元文化系統,就不可能吸收外族博大精深的知識,培育全面的文化素養,更不可能在全球確立今天的強勢地位。而在這一過程中,《西游記》譯介和英語文化之間的相互需求性和依賴性不斷得到強化,最終,在英美世界這個強勢的多元文化系統中,《西游記》譯介順理成章地走進英美社會,扮演著應有的角色,并展現出其強大的適應性與生命力。
《西游記》原著可謂是一部取之不盡的文學寶藏,它屬于中國俗文學范疇,體量巨大,內容龐雜,話題繁多,形象林立,語言簡樸,情節簡單,敘事流暢,表達靈活,便于其他藝術形式的借鑒、挪用和改造,再加上其主要背景、故事情節、主題思想、表述方式、敘事邏輯、情感精神等文學技法都是典型的中國文筆,一些膾炙人口的西游故事如“龍宮奪寶”“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智斗紅孩兒”“真假美猴王”等,故事通俗易懂,在民間廣為傳頌。這些文學和文化知識對英美讀者來說,幾乎契合每個時代的精神,符合每個人的審美需求和接受取向,是向來喜歡異國風情且頗具敏銳鑒賞力的英美讀者觀察和了解中國的一扇重要窗口,并促使讀者對譯作的主體產生認同的“一致性”,也保證了各譯本在故事梗概和基本精神上一貫統一的“忠實性”。《西游記》英譯的本質決定了原作與譯本的血緣關系,譯者以原著為淵源和依托,用全新的語言表達和思維方式選擇性地傳遞中國的主題敘事、文學意象、情感表達、藝術價值等,不管各譯本對原作的片段如何取舍,對人物如何加工,對情節如何調整,基本上都會收錄經典的西游故事,確保與原作的質的聯系,這是毫無異議的。
在流傳英美的百余年中,西方受眾一直懷著濃烈的興趣,熱衷于從不同角度追索《西游記》所展現的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似乎每個讀者都可以從中找到他們喜歡的情節、人物、話題、品質和精神等,所以《西游記》一直被列入英譯熱門書目,主要由英美人獨譯或主譯,且一系列的譯本都帶有時代性,形成一個豐富的譯本群,每一個新譯本并不是要向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讀者均講述同樣的內容,這說明英美人對它的譯介需求和接受能力不斷深入,同時為下一個譯本拓寬譯介空間,為更精進譯本的面世做好鋪墊。另外,《西游記》自成書以來的四百余年中始終熱銷,從未像很多其他名著一樣在中國國內出現極端文化迫害時遭到一時禁絕,這足以說明該文學產品的氣質切合中國文化的統一性,這種溫和的、易被接受的代表性品質顯然有利于《西游記》最有可能適應英美文化系統的需求。因此,盡管《西游記》譯介在英美文化系統中尚處于非原創的地位,但這種適應性需求見證了《西游記》在百余年間的譯果累累、銷量看漲、長盛不衰,也反過來證明《西游記》中富含英美人感興趣的重合點,為其實現英美本土化提供了可能。
當面對全然陌生的中國詞語時,英語譯者大都極力地采用自己熟悉的、喜歡的話語體系在意義轉換上做到英語優先式的文化兼容,力圖保證讀者首先能“看得懂”,發現喜歡的趣味。隨著中西方譯介學語言水平的提高、跨文化交流的頻繁深入和知識儲備的增強,信息再傳輸和意義轉換的忠實程度和異化程度愈發提高,譯介的可接受性和通順性逐步得到認可,其本土化的譯介需求也得到相應滿足,最終持續拓展了《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譯介空間。
《西游記》內容豐富,聲名遠播,早在16至17世紀就以非英語的形式流傳海外,這個隆盛的名聲足以使英美譯者慕名而來,欲端其詳,求窺一二。當譯者個體的需求上升到更大的讀者群體的需求時,個體的、偶然的行為就發展成了社會的、必然的結果。而令人感到神奇的是,不管譯介形式怎樣、結果如何,英美讀者總能從中找到喜聞樂見的話題和興趣,進而產生更加旺盛的譯介需求,以致《西游記》的譯介活動連綿不絕,佳作眾多,并屢屢被各版《大英百科全書》《美國百科全書》、谷歌搜索網、維基網絡百科全書等所提及、收錄和評價。英美民眾最早接觸到《西游記》,當然是從他們喜歡的譯文和譯本開始的,“我覺得要引起讀者的注意,對一些好的中國文學作品重新翻譯是有必要的”[2]。正是漢學譯者們的不懈努力,使《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西游記》的英譯是根據讀者需求和時代需要,對中文原本和其他非英文譯本的表達、內容、形式、意義等進行再加工,這些譯介作品構成的《西游記》呈現出有別于原著的特殊面貌,與英語世界的很多方面都產生了化學反應。時至今日,《西游記》儼然占據了英語原創文學的地位,但凡英美讀者一提起《西游記》,其自有之意就是指英文版《西游記》,而非其他文字版本的《西游記》,其中代表性的譯作有李提摩太的《天國之行》(AMissiontoHeaven)、海倫·海斯的《佛教徒的天路歷程:西游記》(TheBuddhistPilgrim’sProgress:theRecordoftheJourneytotheWesternParadise)、阿瑟·韋利的《猴》(Monkey)等簡譯本,阿瑟·韋利的《猴子歷險記》(TheAdventuresofMonkey)等兒童本,以及詹納爾的《西游記》(JourneytotheWest)和余國藩的《西游記》(TheJourneytotheWest)等全譯本。這些譯介作品圍繞原著的故事情節各取所需,改動各異,或長或短,或宗教化或世俗化,可謂前后相繼,應需而生,應時而現,深受英美讀者的好評,對《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站穩腳跟可謂意義重大,“而小說中,首先走出國門,真正能在西方主流媒體中露面的,能在西方公共圖書館上架的,只有《西游記》———這點我們 2006年曾委托《美國國家地理》高級記者紐曼做過詳細調查”[3]。21世紀以來,《西游記》的譯介需求有增無減,英譯事業后繼有人,蓬勃發展,例如,英國漢學家、倫敦大學伯克貝克學院教授藍詩玲(JuliaLovell,1975—)于2010年決定接受英國一家出版社的邀請,重新簡譯《西游記》;最近幾年一些中國和英美的主流出版社也一直在商討合作并醞釀推出新的簡本或全本。可見《西游記》的譯介需求是長期以來存在于英美文化體系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化事實,英美讀者似乎從來就沒有無視或遺忘《西游記》,反而對不斷涌現的譯本樂見其成并贊賞有加。由是觀之,英美受眾的社會需求也是促成一種《西游記》譯介發生的可能推力,是推動西游故事改寫或重寫的內在動力,是《西游記》英美本土化轉變模式的發生前提。
英美受眾的微觀思維和閱讀需求是喜歡將整個取經故事片段化、人物化、結構化和專題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西游記》譯介經歷了一個從片段譯文到簡譯本再到全譯本,從宗教性、故事性、敘事性再到文化性等的演變過程。可以說,每部譯作都是在一定時代下的閱讀需求的產物。出于早期的傳教需求,漢學家和譯者習慣性地把《西游記》選擇和改寫成宗教性故事,甚至將之轉換成基督教化故事,加劇了西游故事的英美味道。而在20世紀70年代末興盛的“向東看”文化浪潮中,《西游記》譯介重點轉向呼應英美社會的文化呼聲,在跨語言、跨時空、跨民族、跨文明的東西方語境中傳遞西游歷險中最具典型性的語言、人物、情節、歷史、風俗、思想、意識、心理等異域格調,為英美本土文學注入東方異質的文化營養和活力,這說明《西游記》譯介一直指向英美社會的時代性閱讀需求。針對讀者的興趣和喜好,不可避免地要歸化東方色彩,給它們烙上英美本土語言和文化的印記,以便于本土特定的讀者群體更易理解,這種譯介需求保證了譯者源源不斷地參與《西游記》的譯介活動中,從而在英美世界形成《西游記》譯介的本土化良性循環。從譯介學意義上講,只有原作的必然性“犧牲”才能成就譯作的合理性“涅槃”,任何成功的文學翻譯都必須緊貼時代脈搏和讀者需求,這種譯介彈性保障了《西游記》的本土化變形,譯者們不再照本宣科,反而堅定地以滿足讀者需求為首要目的,大膽地對目標語受眾無法接受和喜歡的內容進行取舍和改創,徹底顛覆了傳統譯界遵行的“精確”“忠實”“對等”“可信”“高雅”等字面準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走出需要什么→翻譯什么這樣應對性的現實路徑,造就一種既具有原著風采又適合本土接受的譯介作品,這符合辯證法的鐵律。
誠然,《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的主要傳播載體包括譯介作品(如譯本及其改寫本等)和非譯介作品(如影視劇、舞臺劇、動漫、音樂、網游等),其中每一部作品的面世都意味著一次意義重組,一種經驗變化,一個連續變形,一次微觀和宏觀層面上的本土化接力,這種服務于接受能力的本土化變形自始至終都要盡投英美受眾所好,饜足時代需求,其結果就是徹底重塑了《西游記》在英美國家的文化屬性和傳播前景。這種變形實際上都是時代性作品,都是為《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奠定基礎并擔當起至為重要的橋梁作用,導致語言、人物、內容、形式、敘事、題材、主題、思想、意義等多方面轉換,并始終貫穿于各個作品的廣泛傳播中,滿足受眾的需求,迎合受眾的評判。
就此而言,《西游記》在英美國家本土化的首要緣起就是《西游記》的譯介需求,對它的認知將有益于從源頭上扣住《西游記》譯介在英美世界的發生淵源,把握其本土化譯介的自然性,發掘《西游記》譯介如何在英語語境中重構本土化典型特質的必然性,理解英美世界自成一體的《西游記》文化品牌及其演變規律。
三、《西游記》的本土化文學場
毋庸置疑,任何完整的文學或文化行為要想在異國他鄉廣為傳播,就必須首先打下豐富可靠的物質基礎,必然會經歷信息再傳輸即狹義的傳播和本土化接受兩個環節,二者缺一不可,至于其成功與否,可以干脆用本土化接受的程度和效果來評判。《西游記》能在英美國家落地生根,歸根結底還是受眾廣泛參與和普遍認可的結果,而受眾參與的對象就是琳瑯滿目的譯介和非譯介作品,這些譯介成果在英美文學內部經過一系列的沖突和協商后,激起了受眾的興趣并廣為傳揚,最終發展成為擁有廣泛受眾的一種文學集合,即一種全新的、獨立的本土化產品,從而在整個英美文學體系中扮演從邊緣走向經典的角色,實現文學的域外承認和接受,完成文化身份的重新塑造,使中國文學與英美文化的關系呈現出立體感和復合感,推動《西游記》在英美世界發揮文化影響作用。
基于這種認識,有必要在此澄清一下,不能因為《西游記》原作具有源語國的文學和文化特征就武斷地認定《西游記》譯介具有雙面屬性,即它既屬于源語文學,也屬于目標語文學,這種兩面討好式的說法恐怕會混淆國別文學的概念,是不具有說服力的。因為《西游記》譯介由于在文化語境上的根本轉換限定了讀者和接受者,主要是為目標語國家的讀者和研究者服務,它的轉換過程自始至終都是在目標語的知識語境、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中開展并體現的,讀者和批評家對它的閱讀、賞析和評價等一系列后續的接受活動也是在目標語的話語體系中進行的。打個比方,譯介就好比移植手術,一部《西游記》譯作就像是將一個人體器官由一個中國人生命體移植入另一個英美人生命體,該器官必須發揮通用機能,適應新的生命環境,展現應有的生理功能,服務于新的生命體。故而,《西游記》譯介盡管出自中國文學,但在范疇和功能上當屬于英美文學,如果只是為了表示區分文學素材來源,可以特意將其劃歸為英語文學中次一級的翻譯文學或世界文學,以示非原創的純文學。
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的文學譯作都能像《西游記》譯介作品一樣被英美受眾長期接受,更多的譯作則是因為終歸難以被讀者接受而曇花一現。《西游記》譯介在英美國家的成功不能簡單地歸于某一個譯者或某一部作品,而是應歸結為不同譯介作品共同努力方才實現的完美結局,即《西游記》本土化譯介代表著一個由幾十種相關譯作組成的總集,一個特殊的本土化文學場,這是《西游記》在英美產生歷史生命的物質基礎,是《西游記》實現英美本土化的根本。
在英語世界參與翻譯和接受的漫長百余年間,這些品種繁多、版本各異的《西游記》譯介作品將英美文學傳統和東方文明特質有機結合,在英美文學領域開辟了一個內容豐富、別具一格的《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并構建了一個《西游記》的英美文學品牌,為越來越多的讀者、譯者和作者提供閱讀樂趣和文學滋養。譯者顯然也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他們的譯文也有相互借鑒、繼承的影子,存在很多相似或相通之處,這保證了《西游記》的很多譯本雖然在表情達意等不少層面看似不忠實,卻是譯家們為闡釋和接受《西游記》做出的聰明而無奈之舉,也是該文學品種躋身英美文學并擴大影響力的必由之路。假如沒有這個本土化文學場的物質基礎,西游知識和文化就肯定不可能在英美國家乃至西方世界產生良好的反響,更遑論其所孕育的五彩繽紛、各具風格的文學形態和文化精神。盡管《西游記》的譯介作品數量多達60種以上,體量對比鮮明,出發點、目的性、價值觀和審美觀等花樣百出,但是,只有從英美的文化立場上才可以衡量和欣賞它們的內容、特點、質量和效果等,隨著譯作在數量和質量上的不斷積累以及其本土化影響的不斷擴大,《西游記》作為一系列翻譯作品總集在英美世界彰顯出獨立存在的故事精神和文學價值并取得成功,這是《西游記》譯介作品在英美世界能屹立百年的發生緣起。
出于學術嚴謹性的考慮,用“最好”“高水平”“優秀”“佳作”等華麗而寬泛的字眼來描述《西游記》的譯介作品實在是過于簡單、模糊、主觀,甚至絕對了。為了杜絕此類爭議,不妨嘗試從接受美學和譯介學的視角對《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給出明確的界定,畢竟“翻譯就是用一種語言把用另一種語言在內容與形式不可分割的統一中所業已表達了出來的東西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4]9,此處的“準確而完全地表達出來”指出了譯介的接受旨歸。《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必須在目標語國家才有存在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受英美國家、譯者、讀者的文化意識形態、文化態度、文化心理、文化期待及文化開放度等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譯介本身就有接受的自有之義,如中國唐代賈公彥在《周禮義疏》中就一語中的地指出:“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這個“相解”就是從接受的角度道出了譯介的指向性和終端性,明確地指出譯介不僅是兩種語言間的轉換,更重要的是要被目標語受眾所接受,這和當前國際譯界流行的“異化”和“歸化”的概念不謀而合,因為無論是“異”還是“歸”,其實都是“易”的具體轉換手法的體現,而“化”才是根本上要實現的翻譯目標,即“相解”,倘若順著這個思路并套用這個說法,可以簡單地把《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理解為“換而解文學”甚至“接受文學”。
德國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Hans-GeorgGadamer,1900—2002年)認為,從語言學上講,一種語言代表著一個世界,翻譯即解釋,這就從語言形式上撇清了源語和譯語的界限,極大降低了二者的外在關聯性,說明《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可以理解為一個英美化的文學世界。而姚斯則結合結構語言學和俄國語言學家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1896—1982年)的理論,把一種文學視為一個特殊的語言系統,“文學也是一種語法或句法,自身具有相對穩定的關系,傳統的和非規范化的類型,以及表達方式,風格類型和修辭格的安排。相對于這種安排的是更加千變萬化的語義學領域:文學主題、基型、象征和隱喻等”[5]47,真是“一千個英美人就有一千個《西游記》”,此處的“千變萬化”道出了《西游記》源語文本和譯介文本在類型上的大異其趣和各行其道,指出了《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反映為一系列翻譯作品總集的合理性。同時,這些作品在類型上屬于新作品,而“文學作品的歷史性存在取決于讀者的理解,所以,讀者的理解是作品歷史性存在的關鍵”[6]287,這又從讀者終端區分了源語文本和譯介文本的存在范圍,對領會《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為何反映為一系列翻譯作品總集的必然性很有啟發性。由此,根據接受美學和譯介學,《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價值的實現離不開讀者接受,其一系列翻譯作品總集同樣為不同讀者而作,作為閱讀參與、接受互動的能動方和角色方,不同的《西游記》讀者必當會影響不同譯者的預判和生產,“因為譯者在多大程度上將詩意本土化,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作品的價值”[7]128,此處的“本土化”顯然是指接受美學和譯介學意義上的本土化,即譯介作品相較于原作變化越大越好,數量越多越好,理解越易越好,這條規則非常適用于闡釋《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
在此意義上看,《西游記》的中文原作具有人類通俗的譯介訴求,因而完全有資格走向英美世界,而它一經邁出國門,就超越了中國文學的范疇,進而演繹出英美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意義。作為善于吸納異質文學的精華并用詩學智慧去探索人類存在的一種藝術手段和一個開放平臺,英美文學與異質文學之間并沒有刻意營造出一條不可逾越、無法彌補的鴻溝,相反,它們很樂意將各自相諧的對話、情感、思想自由靈活地交織、體現在同一作品或同一文學品種中,這種積極、開放、包容的通俗特性給《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與英美的接受能力提供了重合點,開拓了它在英美世界的接受空間,并促使其悄然化為英美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而言之,完整的英美文學必然包括《西游記》的一系列譯作總集,而要研究完備的英美文學,就繞不開《西游記》譯介與英美文學之間的互動、影響和接受。換言之,英美文學的范疇要遠遠大于英美的原創文學,所以將《西游記》譯介納入英美文學是合乎情理、不可或缺,畢竟《西游記》在英美國家的本土化譯介中與生俱來的通俗性使其根基牢固,既為英美文學增添了新的文學品種,又在英美文學中深深打下了中國烙印,其眾多譯本各有特色,潛力巨大,不斷地釋放出新的、通俗的文學和文化因子,并促使這些因子在英美文學中生根發芽,在跨文化交流中發揮多元價值。
事實上,盡管《西游記》的原著世界與英美受眾的經驗世界天差地別,原作者、譯創者、英美受眾的“前知識”等大相徑庭,差異性、未知性和陌生性比比皆是,語言的差異更使得英譯無法傳達出原作中極為奧妙的意韻和雅致,如果在英譯中附以繁瑣的注釋,很容易被對中國古典知識一知半解的普通讀者視為畏途。既然這些內容連中外專業學者都語焉不詳,言之不清,就更沒必要將之變形以滿足英美讀者了,不如暫且忽略,因此早期的譯者大都刪繁就簡,盡可能避開繁文縟節般的術語、概念、格式等,采取簡單化、通俗化的譯述方式,先選擇比較契合讀者需要的興趣點,幫助讀者構建起一種整體性的知識輪廓,再以之為基礎,逐漸向能接受的陌生信息擴大,比如阿瑟·韋利把小說第15回的標題“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韁”就縮略為 “TheDragonHorse”。早期的譯本大都對《西游記》原作一再進行簡略和壓縮,導致李提摩太的《天國之行》只有362頁,海倫·海斯的《佛教徒的天路歷程:西游記》僅有105頁,而阿瑟· 韋利的《猴》不過351頁,但這種結構性的知識矛盾和這些尷尬的數字似乎并未束縛英美受眾的西游情結,反而驅動了他們的“視域融合”和“本土化改造”,《西游記》譯本呈愈來愈厚、越來越全之勢,同時不斷地拓寬讀者的接受程度。“譯作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形態,是它的新的存在形式;從譯作與譯入語的文學關系來說,譯作是譯入語文學系統中的一部新的文學作品,具有自己獨立的審美特性和文化內涵。”[8]可見,《西游記》的本土化譯介肯定無法完全拋棄中國文學的傳統因子,它的中國元素既承載著英美讀者的興趣,令他們難以割舍,又相對獨立于英美讀者的“前知識”,令他們難以捉摸,這個矛盾可以通過英語知識共同體的變形調適、文化交匯和歷史共識來化解,從而顯現出《西游記》本土化譯介中中國特質的鮮明價值,以及英美讀者對《西游記》的接受彈性和自主性。
在這個本土化的運動過程中,《西游記》是作為“為接受而再創”的譯介和非譯介作品而發揮作用,這些作品不是簡單對照的字面轉換行為,而是專業受眾基于自身和普通受眾的接受能力的權衡重構,是把中國式取經大義的集體活動濃縮成英美式的個體化歷險的“選擇性”接受活動,是將中國儒釋道教義對接成英美基督精神的“揚棄性”主觀反應,是在英美受眾的邏輯性分析思維和微觀思維操控下所開辟的一片本土化天地。比如,東方的《西游記》都推崇唐僧并尊奉他為靈魂,而英美的《西游記》則膜拜孫猴子并認定他是主人公,以致阿瑟·韋利的《猴》迅速流行英美并被歐洲其他多國語言轉譯,這又從一個世界性的維度提供了考察和思考《西游記》本土化譯介的必要性。因而,東方有東方的《西游記》,英美有英美的《西游記》,當《西游記》最初以譯介形式進入英美國家時,它實際上就已經實現了從純粹的中國文學到英美本土文學的華麗變形,不再是中國文化讀本,而是經漢學家們重新打造的英語文本,他們在英美語境下所接受的、一種具有鮮明英美文化氣質的文學品種即《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一個無比龐雜的《西游記》‘知識共同體’”[9]295。這種譯介憑借其廣泛的認可度成為英美文化共同體接受能力的結晶,不僅展現了英美國家的文化、精神、話題以及中國意象等,而且成為深度譯創甚至非英語譯創的生成性母體,在最大限度內施展了接受的輻射力和生產力,進而在文學、文藝、網絡等領域演繹出一個精彩的西游世界。
四、結語
總之,《西游記》譯介在英美國家的成長得益于其作為一個完整的本土化文學場的成功、其數量的積累和質量的突變,如果要把《西游記》譯介作品整體置于英美文學體系中,不妨從譯介范疇將之劃入翻譯文學之類,以方便對《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的研究。在《西游記》本土化文學場中,每一部作品都具有各自的文學價值,每個譯作與原作以及不同譯本之間往往顯示出時代需求、接受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和互補,每個譯作的價值都經譯者對原作進行不同程度的消解和變形后得到重新張揚。要理解《西游記》在英美世界形成一個完整的本土化文學場的這種特殊現象,就必然涉及到《西游記》文學翻譯的定位、特征、歸屬、變異、與英美本土原創文學的關系、翻譯文學的本土化傾向、譯介和非譯介形式之間直接或間接的復雜關系以及文學譯介向何處去等基本問題,也只有解決了緣起問題,才能深入探討譯介和非譯介在《西游記》的英美本土化流變中經歷的過程、發揮的作用、做出的貢獻和揭示的規律等,也為中英文學翻譯的交流和發展提供探索性的意見和建設性的觀點。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