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刑法典將合同詐騙從詐騙罪中分離出來后,合同詐騙罪的相關問題一直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探討的熱點,尤其是有關合同詐騙罪之合同與合同法之合同的界分在實踐中也是困擾不已。
關鍵詞:合同詐騙罪;合同法;合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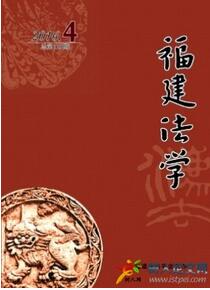
《福建法學》創刊于1982年,是由福建省法學會主辦的一部季刊,正文語種為簡體中文,出版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規定,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據此規定,我們無從得知此罪狀中的合同究竟是與《合同法》中的合同進行全面銜接,還是具有其獨特內涵。而學界對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應以何種標準進行界定,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當具有怎樣的性質,具體包括哪些形式的合同,也存在較大爭議。
一、合同詐騙罪之“合同”
合同詐騙罪是刑法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中的罪名,利用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行為不僅侵犯了對方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更重要的是利用合同詐騙的行為使人們對合同這種手段失去了信賴,擾亂了動態的財產流轉市場秩序,妨害了國家對合同的管理秩序。因此,在認定行為人是否利用的是合同詐騙罪之合同手段這個問題時,必須考慮合同詐騙罪復雜的客體性質,即合同詐騙罪中之合同,必須存在于合同詐騙罪復雜客體的領域內,其合同必須是能夠體現動態的財產流轉市場秩序之合同。凡與這種社會關系無關的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系的協議,不在合同詐騙罪的合同之列,而應適用其他法律的規定,因為嚴格地講,此類合同不具有動態的市場經濟特征,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交易合同,而更類似于一般民事合同。
《合同法》的起草幾乎與現行《刑法》的修訂同期進行,刑事立法者不會不關注我國合同制度的調整。雖然《合同法》修改在后,但它是一個基本法,況且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范圍已經不僅僅限于經濟合同,更多的存在于市場活動主體間的以民事合同為手段的詐騙犯罪開始涌現。并且,將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局限于經濟合同將合同詐騙罪很難發揮刑法打擊此種犯罪的威力,不符合刑法的保護目的。雖然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在立法淵源上以兩個司法解釋為基礎,但立法淵源不應影響刑法的目解釋,也就是當行為人利用除了經濟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進行詐騙,只要是能夠體現市場秩序的合同類型,符合合同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就可以認定構成合同詐騙罪。
二、合同法之“合同”
關于合同法之合同的概念,民法學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理解合同是指確立權利、義務內容的協議,包含經濟合同、行政合同、勞動合同等;狹義的合同是指確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的合同,包括物權合同、身份合同等。從《合同法》第10條的規定,我們可以看出合同的形式包括:①書面形式,即指以文字等有形的表現形式訂立合同的形式。依《合同法》第11條規定,書面形式也包括合同書、信件、數據電文等三種形式。②口頭形式,即當事人之間運用語言對話的方式訂立的合同。③其他形式,即指當事人采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以外的其他方法訂立的合同,如推定形式。上述三種合同形式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形式,但應當強調的是采用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進行合同詐騙的行為需要有證據證明合同本身的存在,否則會因證據不足而無法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因此,從內容上看,《合同法》之合同與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并不完全相同,《合同法》之合同范圍要廣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 合同詐騙罪之合同只占《合同法》之合同的一部分,只有那些能體現合同詐騙罪客體特征的合同才能成為合同詐騙罪所指的合同。對于不屬于合同詐騙罪之合同詐騙內容的行為,雖然行為人利用的是《合同法》之內容的合同,看似采用了合同的手段,卻不能以合同詐騙罪定罪量刑。如果符合普通詐騙罪的犯罪構成, 只能以普通詐騙罪論處,即應當將口頭合同排除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范圍之外。
三、司法解釋確認可成立合同詐騙罪之合同種類
考慮到經濟合同與其他民事合同的區別不明顯,同時技術合同、涉外合同等沒有包括在《經濟合同法》規定的“經濟合同”中,以及制定統一合同法立法的趨勢,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解釋均采用了合同詐騙罪這一罪名,表明刑法第 224 條合同詐騙罪之合同不限于《經濟合同法》之合同,還應包括《技術合同法》及《涉外經濟合同法》之合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的規定,涉外合同有 17 種。這些涉外經濟合同除利用涉外信貸合同進行詐騙構成貸款詐騙罪、利用涉外保險合同進行詐騙構成保險詐騙罪之外,其他 15 種涉外經濟合同均可成為合同詐騙罪的合同種類。在涉外經濟領域已經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大趨勢的要求,《涉外經濟合同法》已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客觀基礎。所以合同法中已取消了“涉外經濟合同”的提法。但是涉外合同畢竟是客觀存在的合同,并且也確實有著與國內合同不同的特殊性,即主體、客體、內容等法律關系的涉外性,以及由此決定的糾紛解決、法律適用等方面的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民事合同中除了上述《合同法》、《擔保法》和司法解釋確認的合同之外,實踐中還有聯營合同、旅游合同、合伙合同、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合同、商標轉讓和許可使用合同、演出合同、出版合同等,這些合同也完全符合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內涵要件,因此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中的合同。
就本文所闡述的問題而言,我們在理解合同詐騙罪中有關“合同”的相關問題時,不可能不基于民事法律特別是合同法中對合同相關法律規定及基本理論來理解,否則,對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理解或闡述就失去了其理論基點。總之,我們認為對于合同詐騙罪中“合同”的理解應建立在民事法律尤其是合同法相關理論基礎之上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更好地對之進行理解,進而有助于在司法實踐中準確處理相關問題。
參考文獻:
[1]蔡剛毅.析合同詐騙之合同[J].刑法問題與爭鳴,2001.
[2]趙秉志.合同詐騙罪專題整理[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