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大釗作為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人民觀極具代表性。他的人民觀內(nèi)涵極其豐富,體現(xiàn)在四個(gè)方面:一是反對(duì)剝削制度,認(rèn)為只有社會(huì)主義制度才能保證人民“智德”與幸福;二是加強(qiáng)對(duì)長(zhǎng)期處于社會(huì)底層勞動(dòng)人民的教育;三是將分散的個(gè)人組織起來(lái),加強(qiáng)團(tuán)結(jié)力和戰(zhàn)斗力;四是對(duì)青年積極社會(huì)變革提出了殷切期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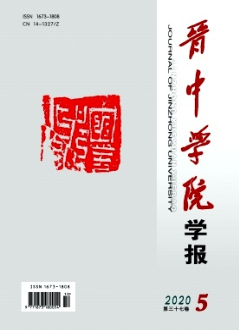
本文源自晉中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20,37(05):23-27.《晉中學(xué)院學(xué)報(bào)》雜志,雙月刊,于1982年經(jīng)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zhǔn)正式創(chuàng)刊,由晉中學(xué)院主管主辦的學(xué)術(shù)性刊物,本刊在國(guó)內(nèi)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shí)效性強(qiáng)的特點(diǎn),其中主要欄目有:政治研究、哲學(xué)研究、文化生態(tài)研究、經(jīng)濟(jì)研究等。
習(xí)近平同志曾鮮明地指出:“人民既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歷史的見(jiàn)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1]314近些年來(lái),學(xué)者關(guān)于群眾史觀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對(duì)人民歷史主體地位也具有共識(shí),但研究客體主要集中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和黨的領(lǐng)導(dǎo)人,鮮有研究早期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人的人民觀。李大釗作為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人民觀內(nèi)涵極其豐富。許全興教授曾指出:“李大釗是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最重視群眾、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觀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和啟蒙思想家。他的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的歷史觀和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解放觀,至今仍閃耀著真理的光輝。”[2]他在求學(xué)生涯及長(zhǎng)期探索中國(guó)革命道路的實(shí)踐中形成了內(nèi)容極其豐富的人民觀,這對(duì)今天我們堅(jiān)定初心、牢記使命,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dǎo)意義。
一、李大釗人民觀的三重演進(jìn)理路
杜鴻林教授在研究李大釗人民群眾觀時(shí)曾論述到:“人民群眾觀是關(guān)于人民群眾是誰(shuí)、如何看待人民群眾、怎樣處理與人民群眾關(guān)系等一系列重大問(wèn)題思想認(rèn)識(shí)的理論形態(tài)。”[3]李大釗的人民觀遵循著“事實(shí)—認(rèn)識(shí)—實(shí)踐”的邏輯,基于事實(shí),逐步深化對(duì)人民群眾的認(rèn)識(shí),最終應(yīng)用于救國(guó)救民的實(shí)踐中。他對(duì)人民群眾的認(rèn)識(shí)前后發(fā)生了三次轉(zhuǎn)變。首先,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他開(kāi)始批判剝削階級(jí),心系人民群眾;其次,受中國(guó)立憲政治西方文化的影響,他萌發(fā)英雄人物在國(guó)家救亡圖存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逐步認(rèn)識(shí)到資產(chǎn)階級(jí)剝削的本質(zhì),從而確立了馬克主義群眾觀,認(rèn)識(shí)到人民群眾是社會(huì)變革的根本力量。
(一)“此少數(shù)豪暴狡獪者外,得其所者,有幾人哉?”
青年李大釗受傳統(tǒng)民本主義思想的影響,開(kāi)始心系群眾,批判剝削制度,既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對(duì)人民的壓迫,也反對(duì)軍閥都督制度。他在《大哀篇———(一)哀吾民之所失也》一文中首先指出:“然自滿清之季,仁人義士,痛吾民之憔悴于異族專制之下”[4]7,“則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專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數(shù)十專制都督”[4]8。當(dāng)時(shí)的李大釗看到了幾人幸福而數(shù)萬(wàn)萬(wàn)人痛苦的現(xiàn)狀。因而,他寫道:“然則所謂民政者,少數(shù)豪暴狡獪者之專政,非吾民自主之專政;民權(quán)者,少數(shù)豪暴狡獪者之竊權(quán),非吾民自得之權(quán)也;幸福者,少數(shù)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數(shù)豪暴狡獪者外,得其所者,有幾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4]9
李大釗雖然看到了社會(huì)的剝削,但他沒(méi)有找到徹底根除專制制度的方法,他對(duì)人民的同情和對(duì)剝削制度的憎恨仍基于道義的譴責(zé)。因而,在《原殺》一文中他寫道:“為今之計(jì),吾人當(dāng)發(fā)揮正義,維護(hù)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則,回復(fù)人類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愛(ài)平和,則平和自現(xiàn),人人良心上皆惡暴力,則暴力自隱,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惡,則罪惡自除。”[4]81當(dāng)時(shí)的李大釗還沒(méi)有樹(shù)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他將人心看作一種可以摧毀現(xiàn)存制度的力量。他論述到:“人心向道義,則風(fēng)俗日躋于純,人心向勢(shì)力,則風(fēng)俗日趨于敝”[4]157。此外,李大釗還從風(fēng)俗、暗殺、“闡明政理”等角度探討人民追求幸福的路徑,但終究不可為。盡管如此,這些樸素的同情對(duì)李大釗日后逐漸走向社會(huì)革命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
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zhàn),人民生活極其痛苦。此時(shí)的李大釗開(kāi)始批判中國(guó)的立憲政治,積極地探索解決中國(guó)問(wèn)題之“道”。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李大釗曾一度認(rèn)可英雄史觀,他認(rèn)為解決中國(guó)問(wèn)題要發(fā)揮少數(shù)人的作用。他在《文豪》一文中指出:“嗟嗟!世之衰也!怨氣郁結(jié),人懷厭世之悲觀,文人于此,當(dāng)以全副血淚,傾注墨池,啟發(fā)眾生之天良,覺(jué)醒眾生之懺悔,昭示人心來(lái)復(fù)之機(jī),方能救人救世。”[4]121隨后又指出:“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樞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樞。風(fēng)之以義者,眾與之赴義。”[4]157他在《立憲國(guó)民之修養(yǎng)》一文中指出:“是皆專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習(xí)染而今猶未能湔除者。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階級(jí),以身作則,而急急以立憲國(guó)民之修養(yǎng)相勸勉。”[4]520本國(guó)立憲政治的失敗、都督混戰(zhàn)和西方文化對(duì)李大釗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其促使了李大釗人民觀的轉(zhuǎn)變,但由于他還沒(méi)有樹(shù)立起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還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人民的主體地位,對(duì)人民的范疇也缺乏完整的認(rèn)識(shí)。
統(tǒng)治日益腐朽,中國(guó)出路何在?李大釗在東渡日本留學(xué)期間接觸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書(shū)籍,他開(kāi)始認(rèn)識(shí)到人民群眾在社會(huì)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開(kāi)始樹(shù)立樸素的群眾史觀。1914年的李大釗就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群眾勢(shì)力是一種新勢(shì)力。他指出:“今有存者,惟此新勢(shì)力耳。新勢(shì)力維何?即群眾勢(shì)力。”[4]188當(dāng)然,由于中國(guó)人民長(zhǎng)期受封建制度的壓迫,人民思想腐朽,一時(shí)還難以開(kāi)化,因此李大釗發(fā)出“吾人生當(dāng)群眾之時(shí)代,身為群眾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覺(jué)其權(quán)威”[4]188的號(hào)召;在《警告全國(guó)父老書(shū)》一文中也指出:“吾國(guó)民今日救國(guó)之責(zé)維何?曰:首須認(rèn)定中國(guó)者為吾四萬(wàn)萬(wàn)國(guó)民之中國(guó),茍吾四萬(wàn)萬(wàn)國(guó)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強(qiáng)敵,亦不能亡吾中國(guó)于吾四萬(wàn)萬(wàn)國(guó)民未死以前”[4]219。此時(shí)的李大釗對(duì)人民的認(rèn)識(shí)還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過(guò)程中,這也是由于他在樹(shù)立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前接觸了大量的外來(lái)學(xué)說(shuō)因素的影響。
(三)“歷史的純正的主位,是這些群眾,決不是幾個(gè)偉人”
留日學(xué)習(xí)的李大釗,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這種理論積淀與俄國(guó)十月革命的爆發(fā),讓李大釗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他開(kāi)始將目光轉(zhuǎn)向勞工主義,他認(rèn)為勞工主義必勝。他在《庶民的勝利》一文中指出:“聯(lián)合國(guó)的勞工社會(huì),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guó)的同胞取同一行動(dòng)的趨勢(shì)。這亙古未有的大戰(zhàn),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jì)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kāi)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zhàn)勝。”[5]358他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論述德國(guó)失敗與俄國(guó)的勝利時(shí)也指出:“不該為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yīng)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huì)主義把軍國(guó)主義打倒而慶祝。”[5]363他開(kāi)始批判西方的政治哲學(xué)與資本家,他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最多數(shù)勞工與最少數(shù)資本家斗爭(zhēng)勝利的不可避免性,他認(rèn)為勞工的勝利是新世界的潮流,但也指出這新命的誕生,必經(jīng)一番痛苦。
李大釗的人民觀與其歷史觀的轉(zhuǎn)變有著根本的聯(lián)系,他摒棄了英雄史觀,從而樹(shù)立起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他曾在《史學(xué)與哲學(xué)》一文中指出:“自馬克思經(jīng)濟(jì)的歷史觀把古時(shí)崇拜英雄圣賢的觀念打破了不少,他給了我們一種新的人生(歷史)觀,使我們知道社會(huì)的進(jìn)步不是靠少數(shù)的圣賢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過(guò)是時(shí)代的產(chǎn)物。”[6]204他隨后又指出:“神權(quán)的、精神的、個(gè)人的歷史觀,多帶退落的或循環(huán)的歷史觀的傾向,而人生的、物質(zhì)的、社會(huì)的歷史觀,則多帶進(jìn)步的歷史觀的傾向。神權(quán)的、精神的、個(gè)人的、退落的或循環(huán)的歷史觀可稱為舊史觀,而人生的、物質(zhì)的、社會(huì)的、進(jìn)步的歷史觀則可稱為新史觀。”[6]321在《孔道西的歷史觀》一文中更是指明:“人類的真實(shí)歷史,不是少數(shù)人的歷史。人類種族,是由些全靠他們自己工作的果實(shí)生存的家族的群眾成立的。歷史的純正的主位,是這些群眾,決不是幾個(gè)偉人。”[6]401
1919年五四運(yùn)動(dòng)爆發(fā),李大釗徹底轉(zhuǎn)向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已然發(fā)現(xiàn)人民群眾是社會(huì)變革的根本力量。他將人民的社會(huì)地位與生產(chǎn)力結(jié)合起來(lái),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指出:“生產(chǎn)力一有變動(dòng),這社會(huì)關(guān)系也跟著變動(dòng)。可是社會(huì)關(guān)系的變動(dòng),就有賴于當(dāng)時(shí)在經(jīng)濟(jì)上占不利地位的階級(jí)的活動(dòng)”[7]19。但當(dāng)時(shí)的李大釗由于受到各種虛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影響,還沒(méi)有完全掌握群眾史觀的科學(xué)性,因此,他曾說(shuō)“有人說(shuō),歷史的唯物論者以經(jīng)濟(jì)行程的進(jìn)路為必然的、不能免的,給他加上了一種定命的彩色,后來(lái)馬克思派的社會(huì)黨,因?yàn)樾帕诉@個(gè)定命說(shuō),除去等著集產(chǎn)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議也沒(méi)有,什么活動(dòng)也沒(méi)有,以致現(xiàn)代各國(guó)社會(huì)黨都遇見(jiàn)很大的危機(jī)。這固然可以說(shuō)是馬氏唯物史觀的流弊”[7]19。
此時(shí)的李大釗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人民,尤其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既是大工業(yè)的產(chǎn)物,又是摧毀建立在大工業(yè)基礎(chǔ)上的資本主義的根本力量。因此他指出:“資本主義是這樣發(fā)長(zhǎng)的,也是這樣滅亡的。他的腳下伏下了很多的敵兵,有加無(wú)已,就是那無(wú)產(chǎn)階級(jí)。這無(wú)產(chǎn)階級(jí)本來(lái)就是資本主義下的產(chǎn)物,到后來(lái)滅資本主義的也就是他。”[7]39在《要自由集合的國(guó)民大會(huì)》一文中也指出:“什么宗教咧,皇統(tǒng)咧,軍閥咧,政閥咧,不遇民眾的勢(shì)力則已,遇則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則已,犯則必遭其殄滅。民眾的勢(shì)力,是現(xiàn)代社會(huì)上一切構(gòu)造的惟一的基礎(chǔ)。”[7]262
二、李大釗人民觀的四維內(nèi)涵意蘊(yùn)
在國(guó)運(yùn)凋零、內(nèi)憂外患、民生苦楚的時(shí)代,李大釗盡管受諸多思潮的影響,他對(duì)人民的認(rèn)識(shí)也時(shí)有偏差,卻始終沒(méi)有偏離人民主體地位的中心軸。他的人民觀內(nèi)涵極其豐富,主要包含四點(diǎn)內(nèi)容:一是對(duì)剝削制度的批判,揭示了剝削制度對(duì)人民幸福遮蔽的本來(lái)面目;二是加強(qiáng)對(duì)長(zhǎng)期處于社會(huì)底層勞動(dòng)人民的教育;三是將分散的個(gè)人組織起來(lái),加強(qiáng)團(tuán)結(jié)力和戰(zhàn)斗力;四是對(duì)青年積極社會(huì)變革中提出了殷切期盼。
(一)“社會(huì)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李大釗認(rèn)為政治是人民“智德”和幸福的保障。他指出:“斯凡一政治所具之長(zhǎng),即在增進(jìn)人民之智德。”[4]272隨著時(shí)局的變化和自身認(rèn)識(shí)的進(jìn)步,他逐漸發(fā)現(xiàn)立憲政治等主張并不能使人民幸福,而是各為其利益所謀。因此,他曾哀嘆道:“唉!社會(huì)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7]120在長(zhǎng)期的革命實(shí)踐中,他逐漸揭示了各種虛假民主政治制度對(duì)人民幸福的遮蔽,并最終發(fā)現(xiàn)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智德與幸福。
李大釗對(duì)國(guó)內(nèi)剝削、壓迫政治的憎恨是一貫的。1919年4月他在《宰豬場(chǎng)式的政治》一文中就曾明確指出:“我說(shuō)我們的政治,是宰豬場(chǎng)式的政治,把我們?nèi)嗣癞?dāng)作豬宰,拿我們的血肉骨頭,喂飽了那些文武豺狼。”[5]450俄國(guó)十月革命后,李大釗一方面繼續(xù)抨擊當(dāng)時(shí)“惡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也開(kāi)始闡述他對(duì)民主主義的認(rèn)識(shí),他認(rèn)為現(xiàn)代民主主義精神是對(duì)人性發(fā)展的有效保障。他指出:“現(xiàn)代民主主義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個(gè)共同生活組織中的人,無(wú)論他是什么種族、什么屬性、什么階級(jí)、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會(huì)上、經(jīng)濟(jì)上、教育上得一個(gè)均等的機(jī)會(huì),去發(fā)展他們的個(gè)性,享有他們的權(quán)利。”[5]410此時(shí)的李大釗已經(jīng)摒棄了抽象的政治學(xué)說(shuō),轉(zhuǎn)而研究政治與人的關(guān)系、制度對(duì)人各種具體發(fā)展的保障。
大機(jī)器工業(yè)下,人民對(duì)資本家、無(wú)產(chǎn)階級(jí)對(duì)資產(chǎn)階級(jí)已經(jīng)是實(shí)質(zhì)上的依賴。李大釗學(xué)習(xí)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后,立即將這一學(xué)說(shuō)應(yīng)用于中國(guó)革命,他發(fā)現(xiàn)“工銀制下的工人,純是一種機(jī)械”[7]26,對(duì)資本家貪婪的揭示與對(duì)工人的同情促使李大釗開(kāi)始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他認(rèn)為批判資本家的貪婪都是源于資本主義制度,而對(duì)工人的壓迫也是資本主義制度,只有摧毀這種剝削制度,才能真正實(shí)現(xiàn)人民的幸福。
李大釗在對(duì)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中逐漸認(rèn)識(shí)到只有社會(huì)主義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個(gè)性的發(fā)展。早期的李大釗也沒(méi)有使用“社會(huì)主義”一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平民政治”“德謨克拉西的制度”等詞語(yǔ)。直到1922年他在評(píng)論工人政治實(shí)現(xiàn)的根本保障時(shí)才具體指出:“在社會(huì)主義制度之下,實(shí)行社會(huì)主義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產(chǎn)階級(jí)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廢止,失去了復(fù)活的可能的時(shí)候,隨著無(wú)產(chǎn)者專政狀態(tài)的經(jīng)過(guò),隨著階級(jí)制度的消滅,Ergatocracy的內(nèi)容將發(fā)生一大變化。他的統(tǒng)治的意義,將漸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統(tǒng)治。此時(shí)的工人政治就是為工人,屬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務(wù)管理。”[6]105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由于各種反馬克思主義、西方資產(chǎn)階級(jí)政治學(xué)說(shuō)等理論的宣傳和影響,很多學(xué)者對(duì)社會(huì)主義提出懷疑,他們認(rèn)為社會(huì)主義制度成立之后,社會(huì)就要發(fā)生怠工現(xiàn)象,從而反對(duì)社會(huì)主義制度。為此李大釗曾指出:“他不知道在社會(huì)主義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現(xiàn)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勞苦,同那牛馬一樣,得不到一點(diǎn)人生的樂(lè)趣。”[6]458社會(huì)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社會(huì)主義首先是一個(gè)經(jīng)濟(jì)的概念,它有一定的物質(zhì)基礎(chǔ),這需要所有人的辛勤勞動(dòng)才能實(shí)現(xiàn),而并非建立社會(huì)主義制度就能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主義。
(二)“人類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須知識(shí)”
中國(guó)曾長(zhǎng)期處于封建社會(huì),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思想精神也極其貧瘠。當(dāng)時(shí)處于底層的中國(guó)人民看不到出路,更不能解決中國(guó)的問(wèn)題。李大釗在長(zhǎng)期革命實(shí)踐中看到了人民對(duì)國(guó)家的重要作用,社會(huì)變革非依賴人的“意志”與“實(shí)力”不可。他在文中曾論述道:“光明緝熙之運(yùn),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賴吾民之實(shí)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邁往直前,以應(yīng)方來(lái)之世變,成敗利鈍,非所逆計(jì)。吾信吾國(guó)命未必即此終斬,種性未必由此長(zhǎng)淪也。”[4]244這里他將人民的個(gè)人命運(yùn)與國(guó)家的前途命運(yùn)聯(lián)系起來(lái)。
如何培育人民的“意志”,李大釗認(rèn)為教育至關(guān)重要。早在1913年,他在《論民權(quán)之旁落》一文就曾指出:“所望仁人君子,奮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爭(zhēng)奪政權(quán)之魄力,以從事于國(guó)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觀”,“若夫國(guó)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圖,所關(guān)至鉅,余當(dāng)更端論之”[4]76。“實(shí)力”是人民自身的力,是與生俱來(lái)的力;而“意志”可以通過(guò)教育后天培育。李大釗認(rèn)為人首先要解決衣食住行,而后才能有“靈”的需求,在物質(zhì)滿足的基礎(chǔ)上,尚需知識(shí)的陶冶。這恰恰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人民所欠缺,他們終日勞作,生活卻極其困苦。因而李大釗曾指出:“不但這個(gè),人類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須知識(shí);物的欲望而外,尚有靈的要求。一個(gè)人汗血滴滴地終日勞作,靡有工夫去浚發(fā)他的知識(shí),陶養(yǎng)他的靈性,他就同機(jī)械一樣、牛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沒(méi)有甚么區(qū)別。”[5]407可見(jiàn)教育人民群眾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此外,李大釗認(rèn)為教育的內(nèi)容也應(yīng)該寬泛和更具操作性,他認(rèn)為這才是democracy的精神,這種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選舉,在經(jīng)濟(jì)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學(xué)上也要求一個(gè)人人均等的機(jī)會(huì),去應(yīng)一般人知識(shí)的要求”[5]408。
今天,我們正在為中華民族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而奮斗。習(xí)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我們所建設(shè)的是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首先是社會(huì)主義。改革開(kāi)始四十多年來(lái),我們物質(zhì)生活極大發(fā)展,人民精神境界也穩(wěn)步提升。在新時(shí)代,加強(qiáng)人民的“意志”教育,錘煉黨性,“首要的就是堅(jiān)定共產(chǎn)主義遠(yuǎn)大理想和中國(guó)特色社會(huì)主義共同理想”[1]4。在實(shí)踐中,有部分黨員和群眾由于自身認(rèn)識(shí)的不足,理想信念不堅(jiān)定,認(rèn)為實(shí)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遙遙無(wú)期,從而產(chǎn)生了悲觀主義情緒,有的甚至不作為、亂作為。因此,他也多次教育黨員和群眾“如果大家都覺(jué)得這是看不見(jiàn)摸不著的東西,沒(méi)有必要為之奮斗和犧牲,那共產(chǎn)主義就真的永遠(yuǎn)實(shí)現(xiàn)不了了”[1]143。
(三)“組織民眾,以為達(dá)到大革命之工具”
民眾的實(shí)力是社會(huì)變革的根本力,如何將這變革“力”發(fā)揮極致,李大釗認(rèn)為只有將四億同胞組織起來(lái)。他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就認(rèn)為:“茍吾四億同胞之心力,稍有活潑之機(jī),創(chuàng)造改造之業(yè),姑且莫論,但能順應(yīng)此環(huán)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視五洲威震歐亞矣。”[4]286也正如習(xí)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深深知道,每個(gè)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們?nèi)f眾一心、眾志成城,就沒(méi)有克服不了的困難。”[8]5
首先,李大釗認(rèn)為人要有犧牲和協(xié)力互助的精神。他在論述達(dá)爾文進(jìn)化論解釋人和動(dòng)物的幾種本能時(shí)曾指出:“第一就是(為)社會(huì)全體而舍棄自己的犧牲心。若是群居的動(dòng)物沒(méi)有這種本能,各自顧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會(huì)全體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會(huì)必受環(huán)周的自然力與外敵的壓迫而歸于滅亡。”[7]131在新時(shí)代,這就要求我們要注意協(xié)調(diào)個(gè)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guān)系,要弘揚(yáng)先公后私的奉獻(xiàn)精神。
其次,李大釗認(rèn)為全世界無(wú)產(chǎn)階級(jí)要聯(lián)合起來(lái)。機(jī)器大工業(yè)的發(fā)展,不僅生產(chǎn)出強(qiáng)大的資產(chǎn)階級(jí),也生產(chǎn)出數(shù)量龐大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他認(rèn)為隨著這種生產(chǎn)制度的變化,無(wú)產(chǎn)階級(jí)非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不可。他在《新紀(jì)元》一文中寫道:“從今以后,生產(chǎn)制度起一種絕大的變動(dòng),勞工階級(jí)要聯(lián)合他們?nèi)澜绲耐饕粋€(gè)合理的生產(chǎn)者的結(jié)合,去打破國(guó)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jí)”[5]377;只有聯(lián)合起來(lái)的無(wú)產(chǎn)階級(jí),才有戰(zhàn)勝資本階級(jí)的希望。他認(rèn)為:“現(xiàn)在那些資本家對(duì)于勞動(dòng)者有些畏懼心,完全是為了勞動(dòng)者還有一些團(tuán)結(jié)力罷了。勞動(dòng)者合了幾千個(gè)或是幾萬(wàn)個(gè)去和一個(gè)資本家爭(zhēng),那也可得到好的結(jié)果”[6]471。隨著資本在全世界的集中,李大釗逐漸認(rèn)識(shí)到全世界無(wú)產(chǎn)階級(jí)聯(lián)合起來(lái)的必要性,因而他指出:“工人們———就是無(wú)產(chǎn)階級(jí)———為對(duì)付中產(chǎn)階級(jí)的聯(lián)合,必須組織一個(gè)工人的國(guó)際聯(lián)合”[6]212,而聯(lián)合的目的就是要“組織民眾,以為達(dá)到大革命之工具”[6]219。
最后,李大釗提出多方面的團(tuán)結(jié)。他認(rèn)為團(tuán)結(jié)不是抽象的團(tuán)結(jié),而是要實(shí)現(xiàn)不同層次人的團(tuán)結(jié),主要有四點(diǎn)內(nèi)容:一是青年人有朝氣,老年人有經(jīng)驗(yàn),要實(shí)現(xiàn)“老人與青年”的協(xié)力團(tuán)結(jié);二是實(shí)現(xiàn)“農(nóng)村與青年”的結(jié)合,讓青年去改進(jìn)農(nóng)村生活;三是實(shí)現(xiàn)“知識(shí)階級(jí)與勞工階級(jí)”的團(tuán)結(jié),把知識(shí)文明輸入到社會(huì);四是實(shí)現(xiàn)“知識(shí)階級(jí)和民眾”的團(tuán)結(jié),民眾做知識(shí)階級(jí)的后盾,而知識(shí)階級(jí)做民眾的先驅(qū),且知識(shí)階級(jí)本身也是民眾的一部分。
(四)“國(guó)家不可一日無(wú)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wú)覺(jué)醒”
李大釗在其諸多講話和文章中,對(duì)青年都表達(dá)了殷切期盼,特別期待青年的“覺(jué)醒”,他認(rèn)為青年應(yīng)該在社會(huì)變革中揮發(fā)中堅(jiān)作用。1916年,他在《青春》一文中已然指出:“青年銳進(jìn)之子,塵塵剎剎,立于旋轉(zhuǎn)簸揚(yáng)循環(huán)無(wú)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轉(zhuǎn)之精神,屹然獨(dú)立之氣魄,沖蕩其潮流,抵拒其勢(shì)力。”[4]309他主張將青年的個(gè)人命運(yùn)與國(guó)家的命運(yùn)結(jié)合起來(lái)。他說(shuō):“國(guó)家不可一日無(wú)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wú)覺(jué)醒,青春中華之克創(chuàng)造與否,當(dāng)于青年之覺(jué)醒與否卜之”[4]329。青年代表著現(xiàn)在和未來(lái),李大釗認(rèn)為過(guò)去的中華是老輩的中華,而未來(lái)的中華是青年人的中華,社會(huì)的根本變革不得不依賴青年的覺(jué)醒。
青年也是人民中的一份子,李大釗青年“覺(jué)醒”的觀念對(duì)新時(shí)代我國(guó)青年大學(xué)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他曾在《學(xué)生問(wèn)題》一文中對(duì)學(xué)生提出要求:“寧為受人敬畏之學(xué)生,不為仰人憐惜之學(xué)生;寧為獨(dú)往獨(dú)來(lái)之學(xué)生,不為寄人籬下之學(xué)生;寧為自強(qiáng)之學(xué)生,不為被動(dòng)之學(xué)生;寧為位置人之學(xué)生,不為被位置之學(xué)生。”[5]127當(dāng)時(shí)很多學(xué)生對(duì)中國(guó)的前途具有悲觀主義情緒,部分學(xué)生不積極參加社會(huì)革新運(yùn)動(dòng),他寫道:“因此我很盼望我們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會(huì)、文學(xué)、思想種種方面開(kāi)辟一條新徑路,創(chuàng)造一種新生活”[5]291。大學(xué)生是一種“新勢(shì)力”,今天我們正處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huì)的關(guān)鍵時(shí)期,這需要更多的大學(xué)生提高覺(jué)悟參與其中;我們也正處于大有可為的時(shí)代,當(dāng)代大學(xué)生要緊跟時(shí)代發(fā)展的步伐,牢固樹(shù)立共產(chǎn)主義必勝的信念,為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貢獻(xiàn)更多的知識(shí)文化。
三、結(jié)語(yǔ)
李大釗的人民觀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群眾路線的最早淵源,他對(duì)人民認(rèn)識(shí)的變化也極具代表性。實(shí)際上他的人民觀不僅僅局限于國(guó)內(nèi),而是樹(shù)立起大人民觀,他曾說(shuō)“然則吾儕今日,不愿為某一特定之國(guó)民希望勝利,而為世界各國(guó)之平民希望勝利,不愿為某一特定之國(guó)民祝禱自由,而為世界各國(guó)之平民祝禱自由”[5]212。今天我們正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guó)夢(mèng)而奮斗,在世界上也積極倡導(dǎo)“一帶一路”,共同發(fā)展,這都是在踐行李大釗的人民觀。國(guó)家的強(qiáng)盛就是人民的幸福;全世界和平,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幸福的實(shí)現(xiàn)都是源于人民的奮斗,正如習(xí)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國(guó)夢(mèng)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mèng),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lái)實(shí)現(xiàn),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8]40。
參考文獻(xiàn):
[1]習(xí)近平談治國(guó)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許全興.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李大釗群眾觀略述[J].唐山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9,32(5):1-12.
[3]杜鴻林.李大釗人民群眾觀述論[J].南開(kāi)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2):106-117.
[4]中國(guó)李大釗研究會(huì).李大釗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中國(guó)李大釗研究會(huì).李大釗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中國(guó)李大釗研究會(huì).李大釗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中國(guó)李大釗研究會(huì).李大釗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習(xí)近平談治國(guó)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論文指導(dǎo)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jiàn)問(wèn)題 >
SCI常見(jiàn)問(wèn)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