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位于河南省方城縣的黃褐土田間定位試驗為平臺,監測生物質炭和秸稈連續施用 4 a 后小麥拔節期和成熟期土壤性質變化及其與成熟期籽粒產量的關系,明確影響小麥產量的主要土壤生化因子。試驗包含 6 個處理,即分別在不施用生物質炭(-B)和施用生物質炭(+B)條件下各設置 3 個處理:①對照(CK),②單施化肥(NPK),③秸稈還田配施化肥(NPK+S)。結果表明:生物質炭和秸稈施用對土壤生化性質和籽粒產量的影響基本上不存在交互作用。連續 4 a 施用生物質炭后,小麥產量平均降低了 17.4%。盡管 NPK+S 與 NPK 處理間平均產量沒有顯著差異,但它們比 CK 處理產量分別增加了 33.8% 和 37.4%。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路徑模型(PLS–PM)分別分析了拔節期和成熟期的土壤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和酶活性對產量的影響,發現小麥拔節期的土壤速效養分含量,特別是氮素的供應是直接影響產量的最為重要因子;而成熟期土壤生化性質對作物產量的影響比較小。因此,為防止黃褐土上施用生物質炭和秸稈后小麥產量降低,需要特別注意小麥拔節期土壤氮素的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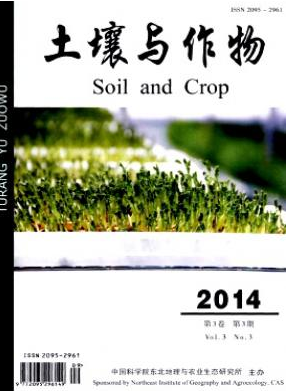
本文源自邱麗麗; 李增強; 徐基勝; 李慧; 趙炳梓; 張佳寶, 土壤 發表時間:2021-05-06《土壤》雜志,于1958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32-1118/P,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專論與綜述、研究報告、研究簡報等。
關鍵詞:生物質炭;秸稈還田;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酶活性;小麥產量
生物質炭是生物質原料在無氧或限氧條件下經高溫熱解的產物,因其在碳封存、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高土壤質量和作物生產力等方面的潛力而被廣泛用于改良農田土壤[1]。施用生物質炭可改善土壤結構、降低土壤養分浸出、增強土壤酶活性、增加土壤中作物生長所必需的營養供應、刺激作物根系生長,從而促進作物產量提升[1-2]。全球 371 個獨立試驗結果表明,施用生物質炭后作物地上生物量和產量平均提高 26% 和 17%[3]。少數研究表明生物質炭可導致作物產量降低 4% ~ 24% [4]。然而,施用生物質炭對土壤生化性質的影響隨作物生育期而異。竇露等[5]發現,生物質炭處理與化肥處理相比,其脲酶活性僅在拔節期增加,過氧化氫酶活性僅在返青期降低,而堿性磷酸酶活性卻在拔節至揚花期升高。劉露等[6]報道,塿土上施用高量生物質炭提高了小麥拔節期和成熟期的土壤 NO3 - -N 和有機碳含量。
秸稈還田是提升土壤質量的常用措施,其不僅可平衡作物營養,顯著改善土壤結構和水熱條件,而且可提升土壤有機碳和養分,促進作物穩產和增產[7]。相對于單施化肥,秸稈還田配施化肥明顯提高了作物產量[8],增加了土壤總有機碳及其組分[9]以及速效養分含量,對土壤酶活性也有明顯的活躍作用[10]。秸稈施用不當也會對土壤環境和作物生產力產生負面影響。王曉娟等[11]曾發現高比例的秸稈還田會降低玉米產量。秸稈還田對土壤的改良同樣受到作物生育期的影響。研究表明,秸稈還田降低了冬小麥返青期土壤 NO3 - -N 含量,但卻有利于成熟期 NO3 - -N 的積累[12]。李秀等[13]發現秸稈還田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氮在小麥整個生育期呈現先增加再降低的趨勢,在拔節期達到最大值。
雖然學者針對生物質炭和秸稈還田導致的作物產量升高或降低及其影響因子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并從土壤性質變化角度做出解釋,但絕大多數結果都是基于成熟期或收獲后土壤性質變化與產量的關聯[2,7-10],而涉及生物質炭和秸稈施用后土壤性質隨作物生育期的動態變化及其對產量的作用研究仍較少。不同生育期內土壤性質的變化會顯著影響該時期作物生長進而影響最終產量。因此,明確不同生育期土壤性質對作物產量的作用,對在最佳時期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當季作物生產力至關重要。
黃褐土是黃淮海平原重要的耕作土壤之一,其土質黏重,耕性和通透性差,是該地區主要的障礙土壤。本研究以田間定位試驗為平臺,監測生物質炭和秸稈連續施用 4 a 后的土壤生化性質和小麥產量。研究目的包括: ①明確生物質炭及秸稈連續施用對小麥拔節期和成熟期黃褐土生化性質的影響;②評估不同生育期土壤生化性質對小麥產量的影響。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田間定位試驗位于河南省方城縣趙河鎮現代農業示范園區(33°08′ N,112°58′ E),始建于 2012 年 10 月的小麥季。該區域氣候屬亞熱帶大陸性氣候,年平均氣溫 15 ℃,年均降水量 800 ~ 1 200 mm。供試土壤為黃褐土,質地為黏壤土。試驗開始前耕層(0 ~ 20 cm)土壤理化性質為:容重 1.5 g/cm3,pH 5.9,有機質 22.8 g/kg,堿解氮 191.0 mg/kg,有效磷 46.6 mg/kg,速效鉀 99.0 mg/kg。
1.2 試驗設計
試驗包括不施用生物質炭(-B)和施用生物質炭(+B)兩種方式,每種方式均設置對照(CK)、單施化肥(NPK)和秸稈還田配施化肥(NPK+S)3 個施肥措施,共計 6 個處理。每個處理均設 3 個重復小區,小區采用隨機區組排列,每個小區面積為 40 m 2。生物質炭購自河南商丘三利新能源有限公司,為小麥秸稈于約 400 ℃ 限氧熱解制備所得,其含碳量 489.6 g/kg,含氮量 18.4 g/kg,含磷量 2.5 g/kg,含鉀量 34.7 g/kg。供試秸稈為玉米秸稈,來自試驗小區周邊肥力均勻的田塊,其含碳量 429.7 g/kg,含氮量 7.0 g/kg,含磷量 1.09 g/kg,含鉀量 14.7 g/kg。供試化肥為尿素、過磷酸鈣和氯化鉀。
試驗地種植方式為冬小麥-夏玉米輪作。在小麥季,當季所用磷肥、鉀肥、玉米秸稈(長 3 ~ 5 cm)和生物質炭均一次基施,50% 的氮肥作為基肥,剩余 50% 氮肥在小麥拔節期開溝追施。小麥季具體化肥施用量見表 1,確保各施肥處理間總施氮量相同。在玉米季,各施肥處理僅施用化肥,施用量均為 N 210 kg/hm 2、P2O575 kg/hm 2 和 K2O 90 kg/hm 2,其中 50% 氮肥、全部磷肥和鉀肥在玉米五葉期溝施,剩余 50% 氮肥于抽雄期穴施。小麥和玉米收獲后其秸稈全部移出小區,其他田間管理方式與當地常規管理方式相同。
1.3 樣品采集與測定
在小麥拔節期(追肥前,2016 年 3 月 6 日)和成熟期(2016 年 6 月 2 日)采集耕層(0 ~ 15 cm)土樣。每個小區均用多點混合法采集土樣,置于冰盒中運回實驗室。在實驗室內將樣品中石礫及動植物殘體等挑出,一部分土樣過 2 mm 篩,然后保存在 -20 ℃ 冰箱中,用于測定土壤中 NH4 + -N,NO3 - -N,水溶性有機碳、氮(DOC、DON),熱水提取態有機碳、氮(HWC、HWN),微生物生物量碳、氮 (MBC、MBN)以及土壤酶活性。另一部分土樣風干后研磨過 2 mm 篩用于測定土壤中有效磷(AP)和速效鉀(AK)含量。
NH4 + -N、NO3 - -N、有效磷和速效鉀含量分別采用靛酚藍比色法、雙波長比色法、鉬銻抗比色法和火焰光度法測定[14]。DOC 和 DON 含量采用 Jones 和 Willett[15]的方法測定。HWC 和 HWN 含量采用 Ghani 等[16]的方法測定。MBC 和 MBN 含量采用氯仿熏蒸–硫酸鉀浸提法測定[17]。采用 3, 5-二硝基水楊酸比色法測定土壤淀粉酶(AMY)和轉化酶(INV)活性;苯酚鈉–次氯酸鈉比色法和三苯基四唑氯化物比色法分別測定脲酶(URE)和脫氫酶(DEH)活性;磷酸苯二鈉比色法測定酸性磷酸酶(ACP)活性[18]。在小麥收獲期,每個小區隨機取 3 個 1 m 2 樣方的麥穗,待風干后脫粒測定小麥籽粒重并用來表征產量。
1.4 數據處理
對數據進行雙因素方差分析并采用 LSD 方法進行多重比較。采用偏最小二乘路徑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path modeling,PLS-PM)分析土壤生化性質之間的作用及其對產量的影響。統計分析采用軟件 SPSS 24.0 和 R4.0.1 中的 PLSPM 程序包完成。
2 結果與分析
2.1 成熟期小麥籽粒產量與不同生育期土壤速效養分
表 2 表明,除了拔節期的速效鉀,生物質炭與秸稈配施化肥對成熟期小麥籽粒產量和生育期內速效養分均沒有交互作用。連續 4 a 施用生物質炭顯著降低了小麥籽粒產量,平均產量降幅達 17.4%。相反,生物質炭施用顯著提升了拔節期有效磷和速效鉀含量及成熟期速效鉀含量,其平均含量增幅分別達 9.0%、19.5% 和 12.4%,但對 NH4 + -N 和 NO3 - -N 沒有顯著影響(表 2)。
秸稈配施化肥處理顯著影響籽粒產量及生育期內速效養分含量。NPK+S 與 NPK 處理間籽粒平均產量沒有顯著差異,但它們比 CK 處理的平均產量增加了 33.8% 和 37.4%(表 2)。拔節期的 NO3 - -N 和有效磷的平均含量在 NPK+S 和 NPK 處理間沒有顯著差異,但它們比 CK 處理的平均含量分別高 195.7%、187.0% 和 37.4%、 32.2%;速效鉀平均含量按秸稈配施化肥處理間的排列順序為 NPK+S>NPK>CK(表 2)。成熟期的 NO3 - -N 平均含量在 NPK 處理中最高,NPK+S 處理次之,CK 處理最低;有效磷和速效鉀平均含量在 NPK+S 和 NPK 處理間沒有顯著差異,但它們比 CK 處理中其平均含量分別高 32.4%、27.6% 和 21.8%、18.1%(表 2)。
2.2 不同生育期土壤活性有機質含量
生物質炭與秸稈配施化肥對不同生育期活性有機質含量基本上沒有交互作用(表 3)。施用生物質炭顯著增加拔節期的 DON 和 HWN(平均含量增幅分別為 19.0% 和 11.4%)和成熟期的 HWN(平均含量增幅為 11.6%)。
秸稈配施化肥處理顯著影響拔節期的DON、HWC、HWN、MBN,它們的平均含量在NPK+S和NPK處理間沒有顯著差異(表3),但分別比CK處理的平均含量增加46.9%、66.7%,7.8%、5.7%,9.7%、20.3% 和50.4%、 63.3%。秸稈配施化肥處理顯著影響成熟期的DOC、DON、MBN,其中DOC含量在處理間的顯著差異主要表現在NPK處理的DOC平均含量比CK處理高11.4%;NPK+S處理的DON平均含量比NPK處理低31.8%,而比CK處理高65.5%;NPK+S與CK處理的MBN平均含量沒有顯著性差異,但它們比NPK處理低28.4% ~ 41.6%(表3)。
2.3 不同生育期土壤酶活性
與上述結果類似,生物質炭與秸稈配施化肥對不同生育期酶活性沒有交互作用(表 4)。施用生物質炭顯著增加拔節期和成熟期的脲酶和脫氫酶活性,其平均活性的增幅分別為 10.4%、8.6% 和 8.7%、6.7%。秸稈配施化肥顯著影響拔節期和成熟期的所有測定的酶活性,NPK+S 處理的酶活性平均比 CK 高 12.1% ~ 40.9%,而 NPK 與 CK 處理間酶活性基本沒有顯著差異(表 4)。
2.4 土壤生化性質對作物產量的影響
利用 PLS-PM 分析了小麥產量與兩個生育期土壤生化性質的關系(圖 1)。圖 1A 表明,本研究測定的拔節期土壤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酶活性總共解釋產量變異的 33%,其中土壤速效養分(直接路徑系數=0.94)的直接影響顯著高于活性有機質和酶活性(直接路徑系數分別是 -0.27 和 -0.23)。在土壤養分變量中,NH4 + -N、 NO3 - -N、有效磷、速效鉀的解釋方差均大于 0.70(圖 1B)。
然而在成熟期,土壤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酶活性總共解釋產量變異的 16%,并且決定小麥產量的直接路徑系數都小于 0.20(圖 1C),表明成熟期土壤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酶活性對產量的影響不如拔節期顯著,盡管其中脲酶、淀粉酶活性與速效鉀含量具有較高的解釋方差(圖 1D)。
3 討論
3.1 生物質炭和秸稈施用對土壤生化性質的影響
3.1.1 速效養分
表 2 表明連續 4 a 施用生物質炭顯著提升了拔節期和成熟期土壤速效鉀含量和拔節期有效磷含量。這與陳心想等[19]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發現施用生物質炭提高了新積土有效磷和速效鉀含量。其原因可能與生物質炭中所含的磷、鉀元素釋放到土壤有關。此外,施用生物質炭可減少土壤中氮、磷、鎂等養分淋失 [20],從而利于土壤有效磷含量的增加。然而,活性磷在土壤中極易發生固定作用,這可能導致了小麥成熟期生物質炭對土壤有效磷含量無顯著影響。
NPK+S 比 NPK 處理的拔節期速效鉀含量高,成熟期 NO3 - -N 含量低(表 2),表明秸稈還田有助于提升拔節期的速效鉀含量,降低成熟期的 NO3 - -N 含量。馮愛青等[21]在棕壤上進行的盆栽試驗結果表明,秸稈配施氮肥比單施氮肥提高了小麥整個生育期 NO3 - -N 含量,但生育期內兩個處理間速效鉀含量沒有顯著差異。可見,該研究結果與馮愛青等的結果不一致,這可能與試驗條件和土壤類型不同有關。秸稈中的鉀元素主要以離子狀態存在,秸稈進入土壤后鉀離子能夠快速釋放到土壤中,從而提高了拔節期速效鉀含量。鉀離子的淋溶損失可能是導致秸稈還田配施化肥與單施化肥處理間土壤速效鉀在成熟期無顯著差異的原因。成熟期小麥對 NO3 - -N 的吸收利用程度降低,但有研究表明,秸稈還田配施氮肥比單純施氮肥更能提高作物的氮素利用效率[22],因此,作物對土壤中 NO3 - -N 的吸收消耗差異可能是造成成熟期 NPK+S 處理 NO3 - -N 含量相對于 NPK 處理降低的原因。
3.1.2 活性有機質
活性有機碳、氮是土壤有機碳、氮中最活躍和最易變化的部分,對土壤管理措施響應敏感。表 3 表明施用生物質炭顯著提高了小麥拔節期土壤 DON、HWN 含量及成熟期 HWN 含量。Gundale 和 DeLuca[23]也曾發現,施入生物質炭的土壤中氮循環加快,可溶性氮含量提高。土壤活性有機碳、氮主要來自于外源有機物料、根系及其分泌物和土壤自身有機質的分解過程。生物質炭對活性有機氮含量的影響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生物質炭自身所含有的有機氮組分通過淋溶作用直接進入土壤所造成的。另一方面,生物質炭進入土壤后會導致微生物將更多的無機氮轉化為有機氮維持自身的生長和代謝活動[24],微生物死亡后這些有機氮釋放到土壤中,從而提高了土壤活性有機氮含量。
在拔節期,NPK+S 與 NPK 處理間的活性有機質含量沒有顯著差異,但在成熟期則是 NPK+S 處理的 DON 和 MBN 含量顯著低于 NPK 處理(表 3);表明秸稈施用對活性有機氮的影響隨著作物生育期不同而異。秸稈還田后其自身含有的部分含氮物質先溶出,但很快會被土壤微生物吸收同化[25]。土壤中可溶性氮或因微生物的吸收同化而消耗;或因土壤中有機質和秸稈的分解而增加。在小麥成熟期,秸稈腐解的養分釋放緩慢,當土壤中礦質氮含量較低時,微生物則以可溶性有機氮作為氮源,其同化作用可能造成了成熟期土壤可溶性有機氮的降低。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秸稈還田在冬小麥生育前期對土壤溫度表現出明顯的增溫效應,在生育后期卻表現為降溫效應[13]。而在一定范圍內,溫度與微生物活性與數量呈正相關關系[26]。因此,秸稈還田的降溫效應可能導致了成熟期秸稈還田配施化肥處理較單施化肥處理的微生物生物量氮的下降。李秀等[13]研究也發現,秸稈還田較無秸稈還田處理能增加冬小麥生育前期的 MBC、MBN 含量,之后緩緩降低,在灌漿期甚至降低土壤 MBC、 MBN 的含量。
3.1.3 酶活性
土壤酶大部分是由微生物釋放,并推動著土壤生物化學轉化過程。連續施用生物質炭顯著提高了兩個生育期的脲酶、脫氫酶活性和成熟期淀粉酶活性(表 4)。這與王智慧等[2]的研究結果一致。土壤中酶活性主要受酶促反應底物濃度以及環境條件的影響[18]。生物質炭對土壤酶活性的提高主要是因為[24]:生物質炭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積,能夠吸附胞外酶分子和底物,提高酶與底物的表面親和力;生物質炭通過改變土壤理化性質而提高酶活性;生物質炭可能釋放一些小分子物質作為一些特定酶的調節劑(比如乙烯可導致 β-N-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活性上調)。
連續施用秸稈顯著提高了拔節期和成熟期土壤轉化酶、脲酶、酸性磷酸酶和脫氫酶活性(表 4),表明秸稈還田是增加與碳氮磷轉化相關酶活性的重要因素。李臘梅等[27]也發現,長期秸稈還田能夠顯著增加土壤中脲酶、酸性磷酸酶和脫氫酶活性。這可能是由于秸稈中含有較高的碳水化合物及豐富的有機態氮磷等物質,為相關酶提供了充足的反應底物,從而有效地提高了酶活性[18]。
3.2 不同生育期土壤性質與作物產量
施用生物質炭后,當季小麥產量顯著降低(表 2)。Kishimoto 和 Sugiura[28]曾報道在火山灰土上施用 5 t/hm2和 15.25 t/hm2 生物質炭導致大豆產量分別降低了 37% 和 71%,究其原因是生物質炭添加提高了土壤 pH,導致土壤中微量元素缺乏。另一項研究報道,在酸性土壤上單施 4、8 和 16 t/hm2生物質炭(未配施氮肥)后,水稻籽粒產量分別降低了 23%、10% 和 26%,而配施氮肥后其產量沒有顯著性變化[29]。本研究中 PLS-PM 分析表明小麥拔節期的土壤速效養分含量是直接影響黃褐土上當季小麥產量的重要因素(圖 1A)。其中 NH4 + -N、NO3 - -N、有效磷、速效鉀的解釋方差均大于 0.70(圖 1B),表明這 4 個參數是影響小麥產量的重要參數。施用生物質炭顯著提升了拔節期的有效磷和速效鉀含量,而對 NH4 + -N 和 NO3 - -N 沒有顯著影響,進一步表明 NH4 + -N 和 NO3 - -N 可能是影響小麥產量降低的最為重要因子。NH4 + -N 和 NO3 - -N 在土壤中的凈變化量取決于多個微生物過程的綜合作用。以尿素等 NH4 + -N 形式施入的氮肥一般在 2 ~ 3 周內即可通過硝化作用迅速轉變為移動性較強的 NO3 - -N,而生物質炭的氧化表面也可以催化一定數量的 NH4 + -N 氧化[30]。生物質炭添加到農田土壤中,NH4 + -N 濃度的降低可能是揮發或被生物質炭強化固定的結果。由于微生物利用 NO3 - -N 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因此其優先選擇 NH4 + -N 作為氮源,但當 NH4 + -N 含量不足以滿足微生物需求時,NO3 - -N 的微生物同化作用就有可能發生[31]。 Dail 等[32]研究表明,當 NO3 - -N 施入土壤之后,在 15 min 之內其無機氮庫便減少了 30% ~ 60%,這其中只有不到 5% 轉化為難溶性有機氮,而其余絕大多數轉化為可溶性有機氮。而土壤中有效態碳的數量亦是限制微生物對氮源利用的關鍵因子,當土壤中加入足夠數量的碳源后完全可以刺激 NO3 - -N 同化[33]。生物質炭含碳量高,施入土壤后一方面刺激了微生物的數量和活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土壤有效碳源,提高土壤 C/N,會激發異氧微生物吸收更多的外源氮來滿足自身生長對氮的需求;但這同時也降低了土壤氮素的有效性。本研究中拔節期生物質炭施用后,土壤中 NH4 + -N 和 NO3 - -N 含量有降低趨勢(表 2),微生物將無機氮轉化為 DON 和 HWN 等有機氮(表 3),不利于小麥對無機氮的吸收,造成作物產量下降。已有的研究也表明施用生物質炭容易導致土壤氮素被固定,不利于作物產量的提高[34]。因此,在黃褐土上施用生物質炭,可考慮適當增加作物拔節期氮肥施用比例,以緩解微生物與作物競爭氮素現象,滿足作物生長氮素的需要。
圖1C表明本研究測定的小麥成熟期的土壤速效養分、活性有機質和酶活性對作物產量的直接影響都很小。小麥從播種到返青期,根系生長量很小,對養分需求少;返青期到拔節期根系迅速生長,對養分需求也迅速增加;開花以后,對養分的吸收率逐漸下降[35]。劉興海等[36]認為,拔節期是冬小麥的“N 素最大效益期”,也稱 “N 素不足敏感期”,在拔節期重施氮肥,不僅不會引起貪青、倒伏,而且能大大提高小麥后期的光合生產率,達到成穗率高、提高粒重的明顯效果。因此,相對于拔節期,成熟期的土壤生化性質對產量的調節效應可能較弱。
NPK+S 與 NPK 處理間的小麥籽粒平均產量沒有顯著差異(表 2),表明連續 4 a 施用秸稈對小麥產量無顯著性影響。秸稈中的氮磷等養分元素主要以有機形態存在,進入土壤后短時間內并未完全被微生物分解釋放,從而造成拔節期土壤中速效氮和有效磷含量并沒有顯著提高。在拔節期,NPK+S 與 NPK 的處理間礦質態氮和活性有機氮均沒有顯著差異(表 3),這一方面說明了秸稈還田配施化肥避免了微生物與作物爭氮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施用秸稈處理小麥產量沒有顯著變化的原因。李曉等[12]連續 3 a 的研究曾表明,秸稈還田增產或減產與施氮量有關,秸稈還田處理施氮量較低時小麥減產,施氮量較高時小麥增產。因此,今后仍需要評估秸稈與化肥的不同配比對不同生育期土壤養分的影響及生產效應,為農業生產實踐提供最合理的秸稈施用方案。
4 結論
1)黃褐土上連續 4 a 施用生物質炭提高了小麥拔節期有效磷、速效鉀、DON、HWN 含量以及脲酶和脫氫酶活性;提高了成熟期速效鉀、HWN 含量以及淀粉酶、脲酶和脫氫酶活性。連續施用秸稈提高了拔節期速效鉀含量和兩個生育期的轉化酶、脲酶、酸性磷酸酶和脫氫酶活性,降低了成熟期 NO3 - -N、DON 和 MBN 含量。
2)黃褐土上連續 4 a 施用生物質炭后,當季小麥減產;而連續秸稈還田對產量卻沒有顯著影響。小麥拔節期的土壤速效養分含量,特別是氮素的供應是直接影響當季作物產量的最重要因子。因此在黃褐土施用生物質炭和秸稈,應考慮適當增加作物拔節期氮肥施用比例,從而提高作物生產力。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