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和阻礙很多,除了自身關鍵領域的創新與經營能力落后外,外部的打壓也十分激烈,但同時我們要看到國家和社會的堅定決心,國內市場的繁榮穩定,將為制造業升級提供持久推動力。鑒于零售是銜接產研和營銷的關鍵環節,且我國的網絡零售業在全球具有領先優勢,本文就網絡零售對我國制造業升級的影響效應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網絡零售對我國制造業升級具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但同樣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制造業升級要充分利用網絡零售帶來的發展動力,加快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在新的全球貿易網絡格局定型前,在全球制造業價值鏈的中高端占據主導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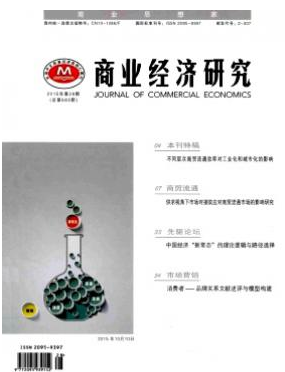
本文源自商業經濟研究,2020(18):176-179.基金:2018年度河南科技智庫調研課題“河南智能制造產業發展影響因素與趨勢研究”(HNKJZK-2018-15);2018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決策咨詢項目“新時代河南高端裝備制造業發展現狀及對策研究”(2018JC14);2018年度第九批河南省重點學科建設項目“區域經濟學”(教高[2018]119號)《商業經濟研究》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旬刊),創刊于1982年,曾用刊名:商業時代;1982年創刊,是專業理論刊物。研究社會主義商業經濟理論,介紹企業改革和營銷經驗。主要讀者對象為商業、供銷系統管理和工作人員、經濟理論工作者及經濟院校師生等。主要刊發經濟類稿件,尤以研究流通理論而獨樹一幟。
制造業升級本質就是要將我國制造業重心,從微笑曲線的中間組裝環節,轉移到兩頭的研發設計和品牌。零售業是鏈接供需兩端的樞紐,在網絡零售環境下,將傳統串行產業鏈條轉變為高度融合的一體化網絡。網絡零售對競爭迭代、技術外溢、規模化、品牌運營、研發牽引、需求挖掘等的能力都是傳統零售無法比擬的,在網絡零售的帶動下,生產制造流程、制造企業管理運營模式、生態合作、價值鏈、全球格局等都會發生革命性變化。面對高端突破阻力和低端“流失”,研究如何充分借助網絡零售推動我國制造業升級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相關文獻綜述
與傳統零售的最大區別在于,網絡零售是基于互聯網及網絡信息技術,真正實現了制造業以需求為導向、充分信息互換及產業鏈各環節的協同整合等革命性變化,因此研究網絡零售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必須清晰認識其對制造業產業鏈端到端的影響。
宏觀視角下,嚴北戰(2019)基于產業價值鏈的視角,分析了電商業-制造業雙重集聚的形成機理,雙向融合發展的動機、模式,并基于電商業-制造業雙重集聚與雙向融合互動,研究了制造業價值鏈升級效應,認為雙向集聚與雙向融合具有互動與強化作用,兩者互動形成合力具有產業價值鏈重構效應、協同效應與創新效應,推動制造業升級;胡俊(2019)運用2004~2016年省級面板數據對地區互聯網發展水平對制造業升級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研究表明地區互聯網發展水平對制造業升級呈現出顯著的正向影響,但中部及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制度改革等領域相對滯后,正向效應有所降低。同時,互聯網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我國制造業在GVC(國際價值鏈)的低端鎖定效應。
中觀視角下,潘晨濤等(2019)以阿里與福特合作為例,研究數字經濟促進傳統汽車產業轉型升級,認為數字經濟帶動汽車產業構建新型產業生態圈的途徑包括進行數字化生產、推廣“新零售”模式和優化內部資源配置三個方面;許紅妹等(2018)以無錫出口貿易為對象,研究跨境電商對無錫外貿轉型升級的影響,結果表明跨境電商促進了無錫外貿結構的調優、交易對象多樣化、外貿服務部門和出口制造商服務升級及進口消費結構升級。
微觀視角下,卞亞斌等(2019)研究認為“互聯網+”對制造業升級的促進效應包括知識外溢引發企業的開放并快速迭代的創新、基于信息化的生產要素全流程整合創新以及采購效率的提升三個方面;胡少東等(2018)基于粵東481家制造業企業的調查數據分析“互聯網+”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結果表明企業領導者和員工的教育程度、企業規模、盈利能力、研發投入與企業采用“互聯網+”行動之間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已采用“互聯網+”的企業與未采用“互聯網+”的企業相比,其領導者、員工的教育程度相對較高,企業規模比較大,有較強的盈利能力和研發投入,能夠更好地享受政策優惠,能獲得更多的財政扶持資金。
我國制造業升級發展現狀
(一)制造業結構、品牌化顯著改善
按行業分,制造業中機械、電氣、交通運輸及其他設備等制造比重逐年上升,自2005年起已超過以原材料、資源和勞動為主要投入的制造行業(見圖1)。
表12009~2018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額比重
圖11999~2018年我國制造業大類歸集出口額比重
圖22018~2019年度全球創新百強企業與機構
同時,中國制造品牌隨跨境電商“出海”,成為制造業“微笑曲線”改善的重要契機。《2019年BrandZ中國出海品牌50強》顯示,2019年中國品牌的品牌力指數同比增長15%,2018年增幅僅為5%,榜單涵蓋12個產品類別,反映出中國出海品牌涉獵商業領域廣泛,同時在日本、法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增幅明顯,說明品牌影響力明顯提升。
(二)關鍵領域亟待實現快速突破
盡管目前在網絡零售等因素推動下,我國制造業信息化水平及結構優化持續提升,而堅實的工業基礎能力、重點領域突破發展能力則亟待突破。從我國制造業產品出口結構看,自2005前后起,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主要包括服裝鞋帽、橡膠塑料制品、玩具等)出口比重被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機器、通信設備、電子產品、車船運輸設備等)出口比重超越,但實際上并不意味著我國已是技術領先和創新驅動的制造強國,而僅僅是從最初級的依賴原材料和勞動力的加工業,調整為以技術、資本和自動化生產為核心要素的中高端制造業。
如表1所示,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9-2018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中,出口額比重基本穩定在22%左右,而進口金額卻略有上升。科睿唯安(ClarivateAnalytics,前湯森路透)評選出2018-2019年度全球創新百強企業與機構(圖2)中,美日兩國占比超過三分之二,其他國家最高為法國有7家企業入選,而我國僅有3家(分別為比亞迪、華為和小米)。日本自2014年超越美國以來一直處于全球第一位置,目前早就拋棄已經淪為低端制造業的家電之類產業,轉變為全力投入BtoB、新材料、人工智能、醫療、生物、新能源、物聯網、機器人、高科技硬件、環境保護、資源再利用等新興領域,日本核心科技專利占世界80%以上。
制約我國制造業升級發展的主要瓶頸在于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特別是對未來發展具有關鍵顛覆性影響的重大技術創新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如核心零部件、關鍵設備等基礎能力不強,芯片、高檔數控系統、高檔電壓件、高端發動機、高端軸承、精密對接螺栓等都要依靠進口。在全球制造業格局重構的關鍵時期,發達國家極易扼住我國制造業的“咽喉”,如2018年11月,美國BIS列出了美國政府考慮進行管制的14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技術”清單,涵蓋5G、人工智能、微處理器、先進計算技術、機器人、3D打印、量子信息、先進材料和生物技術等領域。
(三)制造業升級的宏觀政策體系
國家圍繞“中國制造2025”戰略,發布了《中國制造2025》(“1+X”)規劃體系和《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年)》,先后啟動了三批智能制造試點示范項目,加快推進了“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智能制造、工業強基、綠色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為制造業整體轉型升級奠定了堅實基礎。
網絡零售對我國制造業升級的影響效應
(一)提升創新精準度以加速產品迭代
制造業升級的核心在于自主創新,而自主創新的核心在于創新效率。創新效率是指創新活動具有明確的指向性和變現效果。以往我國在很多領域的自主創新普遍存在“閉門造車”現象,缺乏對市場需求、競爭對手信息等進行充分調查和及時更新,最終導致研發成果質量低或已過時。自2009年前后起,我國企業專利申請數和擁有量持續快速增長(見圖3),2018年我國專利申請數占全球46.4%,連續8年全球第一。但根據WTO貿易數據統計分類中2009~2018年全球知識產權使用費顯示,我國知識產權使用費出口位列全球第18位,僅有第一名美國的1.4%。可見,我國的企業創新量大,但費用投入較低且創新使用價值不高。
圖32000~2018年我國規模以上及大中型企業發明專利擁有量及申請數
圖4主要國家2018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
圖5跨境電商平臺助力制造企業走出去的賦能體系
在網絡零售環境下,消費者需求和行為特征、競爭對手產品及服務等信息呈現出多樣性及豐富性,而創新活動在充分的市場信息支撐下,更能夠有的放矢。同時,市場信息的公開,提升了所有競爭者的研發和上市速度,小幅高頻創新變現成為產品競爭的核心策略。網絡零售的知識外溢,極大縮短了新產品和新模式的生命周期,終端消費品制造企業必須不斷尋求新的創新點,并快速通過全渠道零售和柔性生產實現快速規模變現。
(二)加速創新系統性積累
對比我國與美、日、德等強國的制造業發展水平,工業化起步時間差異,是我國的技術積累薄弱存在客觀原因。經過三十多年的貿易交換,我國已經在非核心技術領域實現了不斷的積累,但在各領域的核心技術中,由于擁有國的封鎖以及持續的研發投入(見圖4),我國期望在短時間內實現趕超,需要另辟蹊徑。
表2中、美、日三國企業平均壽命對比
在傳統市場環境下,技術、工藝、渠道等的外溢及開放度受限,企業一旦建立技術和品牌優勢,能夠在較長的時間內獲得良好的經營效益,進而支撐技術的持續提升和沉淀,因此技術強國的企業平均壽命明顯高于我國企業,如表2所示。
在網絡零售環境下,一方面基礎或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夠依靠互聯網+實現“小進步”的快速市場化,即通過網絡零售拓展市場空間,為自主創新及時“供氧”;另一方面在網絡零售的充分競爭下,倒逼制造業相關企業、研發機構等在自主創新上四處出擊,“各顯神通”。相比美、日、德等國制造業技術創新主要依靠科研機構、企業聚焦和持久的縱向深挖,目前我國的制造業自主創新走的橫向積少成多的道路。對于我國制造業整體創新系統而言,每一家企業、每個科研機構和高校,在各自的方向上邁進一小步,那么整體上就是邁進一大步,而實現眾多一小步到一大步的整合有賴于網絡零售,有賴于“互聯網+”制造。無論是產學研效率的提升還是產業鏈、產業生態的調整,網絡零售無疑是動力強勁的火車頭之一。
(三)提升我國制造業企業全球化經營能力
在國家和企業大力投入新型產業和技術創新的同時,更多制造業企業實現跨國家、跨地區的業務布局,但能否快速建立與之匹配的全球經營能力是絕大多數制造業企業面臨的最大挑戰,而跨境電商的發展為我國制造業增長及升級注入了新的動力(見圖5)。
主要表現在:跨境電商的F2C模式,減少渠道銷售環節,提升了制造商直銷的把控度,進而提高產品利潤率;第二,跨境電商平臺能夠為制造企業提供成熟的品牌運營方案,包括品牌設計、推廣策劃等;第三,跨境電商平臺聯合海外眾多線上、線下渠道,為制造企業構建一張互聯互通的渠道網絡;第四,跨境電商平臺通過參與各國、地區相關電商立法、梳理管理制度等,能夠幫助制造企業規避合規風險,消除隱患;第五,跨境電商平臺能夠直接為制造企業提供線上零售運營管理、專業咨詢等服務,減少制造企業自身電商團隊的投入;第六,圍繞跨境電商平臺生成的生態規模化發展,能夠推動跨境電商往來國家、地區加大相應的倉儲、物流園區建設,以及售后服務體系本地化合作,進而解決我國制造企業“出海”的后顧之憂。
(四)國產替代型制造企業在短期內會受到一定沖擊
我國大力發展跨境網絡零售,必須在行業準入、稅收等方面實施更加開放和公平的政策,因此跨境網絡零售同樣能夠為國外制造企業帶來流通成本降低、擴大渠道等利益。在中高端制造領域,我國在很多關鍵技術和部件上實現了進口替代,但并沒有實質意義上的達到國外先進水平或者實現引領,而僅僅是關鍵技術指標達到了實用要求,經濟性上具有明顯優勢。跨境網絡零售能夠明顯降低這部分制造商的出口成本,即我國進口的完稅價格下降,從而對進口替代制造商帶來直接的沖擊,如根據艾媒咨詢調查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30.7%海淘用戶因海外商品質量好而選擇海淘。
同樣地,在國際市場上掌握核心技術和工藝的跨國企業,能夠通過網絡零售平臺和智能零售工具,實現渠道和市場的規模化擴張,并覆蓋到更多的細分市場,同時又不需要在自身組織中投入過多的人力。因此,不僅僅是我國國內市場將受到沖擊,在我國制造業企業走出去的道路上也會面臨發達國家新的競爭。2018年全球跨境網購普及率達已51.2%,其中馬其頓、葡萄牙、澳大利亞的跨境電商市場份額已超過80%(數據來源:艾媒咨詢)。加上語言文化同源、政治和經濟同盟等關系,發達國家基于網絡零售開展新的全球化競爭,面對的阻力比我國制造企業要小很多。
對策建議
第一,加強自主研發知識產權保護和經濟性回報。
距離2025年實現智能制造的目標時間已經十分緊迫,因此我國的自主創新必須充分發揮“人多力量大”的優勢。一方面對關鍵領域進行重點投入,實現對核心領域、關鍵技術的突破;另一方面激發知識產權市場的市場效應,利用技術授權、轉讓等市場手段,不斷地碎片化、創新性進行收集疊加,以實現從量變到質變。上述策略的核心在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對于創新個人、創新企業而言,其發明創造不能被盜竊、不能被無償收割。具體而言,及時對知識產權加強法律保護,對發明創造要給予充分的經濟性回報,如華為公司對8位高端應屆生人才制定了百萬年薪就是具體的典范,應當有更多的制造業企業和政府政策,對創造性人才提供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經濟回報。
第二,加速制造業價值鏈中高端環節的全球布局。
伴隨著跨境電商以及各國本土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在排除貿易保護主義重新起勢的前提下,全球市場開放一體化的程度將大幅提升,各國家將會有更多企業通過網絡實現全球化經營。隨著我國人口紅利優勢逐漸衰弱越發明顯,我國制造業增速放緩將會給制造企業經營和國內就業帶來嚴重危害。因此,我國制造業升級在加速自主創新的同時,就是要借助跨境電商“出海”,利用我國雄厚的制造業體系和供應鏈生態能力,快速在海外國家制造業價值鏈中占據更多的高價值環節,如開發設計、營銷、供應鏈管理等等。對于具體的制造業企業而言,就是要實現業務增長點和利潤來源的轉換,由原先依靠廉價勞動力和低價走低端加工制造的增長模式,轉換為以品牌運營、研發設計、股權投資等為核心業務的增長模式。
第三,提升制造業企業經營管理軟實力。
我國絕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的經營管理軟實力,與歐美、日韓等的跨國制造業企業的差距很大,從企業組織結構、品牌形象、管理者形象素質、社會責任等方面,即使在本土的經營表現都差距明顯,更不論在語言文化、政治法律迥異的海外。我國目前已經走出去的制造業企業不少,但真正能夠深入當地經濟社會甚至政治環境的卻寥寥無幾,僅有華為、聯想等幾家屈指可數。在很多場景下,海外客戶由于語言、文化等原因,會對我國企業產生偏見,如澳大利亞的海淘客戶基本上只購買歐美國家的產品,加上現實中我國個別企業在海外經營存在不合規的行為,更是加深了海外客戶的負面印象。
近年來,國家從各個方面努力地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讓全球更加了解中國。作為在全球網絡經濟前線的制造業企業,應當在職業化、合規化、品牌化上向華為等國內優秀企業以及發達國家跨國企業取經學習。
參考文獻:
[1]王亮.網絡零售提高了制造業集聚嗎?——基于動態SDM的時空效應分析[J].中國經濟問題,2019(7)
[2]丁長峰.互聯網經濟下我國電商網絡零售演進及競爭發展態勢[J].商業經濟研究,2019(1)
[3]楊帥.網絡零售?電商生態與產業升級[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5(12)
[4]張拯華等.“互聯網+”背景下傳統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發展路徑與機理選擇[J].中國市場,2019(10)
[5]劉彬斌.“互聯網+”與制造業融合創新動力與機理研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19(9)
[6]余東華,李捷.人力資本積累?有效勞動供給與制造業轉型升級——基于信息網絡技術擴散的視角[J].經濟科學,2019(4)
[7]吳良德.商貿流通業集聚對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影響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17(3)
論文指導 >
SCI期刊推薦 >
論文常見問題 >
SCI常見問題 >